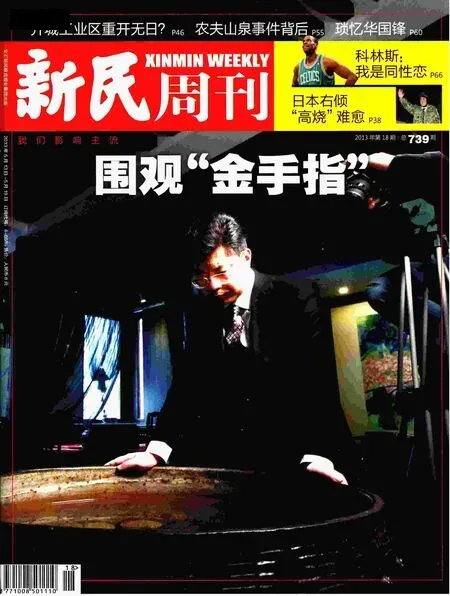正視民營快遞“新煩惱”
馬紅漫
民營快遞公司最近“比較煩”。據悉 ,國家郵政局近日向國內快遞企業發文,明確凡是在我國境內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都應當繳納郵政普遍服務基金。雖然具體征收時間尚未敲定,且相關負責人強調基金的征收是定向用于“村郵站”的建設、運營和補貼,但這一消息仍在業界引起不小的波瀾。
依照有關部門的觀點,國家郵政一方面要兼顧普遍服務、另一方面又要在高端市場迎戰異軍突起的民營快遞同行,著實力不從心。既然“嫌貧愛富”的民營快遞公司擠占了傳統郵政的優質客源,那么就有“義務”從其利潤中提取部分郵政普遍服務基金。但這一思路頗具行政色彩,混淆了商業與公益的邊界,以政令強行干預自由市場的意圖明顯。而國外已有實踐表明,財政資金支撐下的專項基金才與郵政普遍服務的公共屬性更加匹配。
郵政普遍服務、尤其是偏遠山區通信服務是政府為保障公民基本通信權利而提供的服務, 在各個國家都體現出業務多、任務重、利潤低的特征,是天然的公共產品。為了抵補這部分郵政基礎服務的虧損,我國從90年代就開始嘗試過“以電養郵”、“以儲養郵”、財政直接補貼等補償機制,但由于郵電分家等體制變革因素以及郵政普遍服務成本收益核算機制不完善等現實原因,相關補貼渠道不穩定、數額隨意性較大等問題較為突出。通過基金補貼的方式更加專業與有效,但問題是,該由誰為這項基金“注水”。
據業內人士測算,目前民營快遞價格競爭十分激烈,每件利潤僅為0.3-0.6元。如果按“國內同城快遞0.1元/件、國內異地0.2元/件、港澳臺1元/件、國際2元/件”的標準征收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就相當于要求它們承擔利潤1/4-1/3的額外負擔,這讓民營快遞企業感到有些“吃不消”,成本轉嫁將成為必然,但這一結果又顯然于內需擴容無益。需要指出的是,快遞市場并不應被視為國家郵政系統的專屬領域,大量民營資本介入體現了電商時代對物流業的需求。即便民營快遞公司在商業趨利訴求下對市場進行了“撇脂”性選擇,其在正常納稅后也沒有再為郵政普遍業務進行補貼的必然義務。客觀而言,民營快遞所激起的“鯰魚效應”明顯提升了客戶體驗,倒逼一直“朝南坐”的郵政快遞在發貨速度、送貨服務等方面做出了明顯改進,是為市場競爭的魅力所在。但是,新興網購催生的民營快遞業總體還處于“幼稚期”, 在當前油費水平高企、過路收費頻繁的環境下,多數民營快遞企業的合理盈利空間尚未打開。倘若將公益性郵政普遍服務的運營成本強加于民營快遞業,只會削弱其市場活力,緩滯快遞行業自我修正與完善的進程。值得一提的是,競爭壓力也在促使民營快遞業嘗試進入較為偏遠的地區。在每一條新路線開辟之初,快遞企業都要為前期人員、車輛配備以及貨源準備投入大量資金成本,但卻不可能像國家郵政那樣獲得社會資源的慷慨投入。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它們大多將郵政普遍服務明確定位為政府的社會責任,并在財政支持下對郵政普遍服務基金進行規范管理。德國《郵政法》規定:當經營者證明由于長期提供普遍服務,成本超過收入時,可向政府郵政主管部門要求補貼;美國財政部為郵政建立了一項沒有年度限制的“郵政基金”,用于支付郵政普遍服務等費用。這些案例均是國家稅收資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良好體現。事實上,我國郵政部門也因其提供了公益性服務而享受到許多民營企業無法企及的政策福利,諸如“中國郵政”的運郵車輛免收路橋費、對信件和國家機關公文的寄遞享有專營權等等。
財稅制度本就是為統籌使用稅收資金、提高公共產品供給公平與效率而設,要求市場主體在履行納稅義務之后再為公益服務買單,有違市場機理。民營快遞業的“新煩惱”理應得到正視,相關決策當再做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