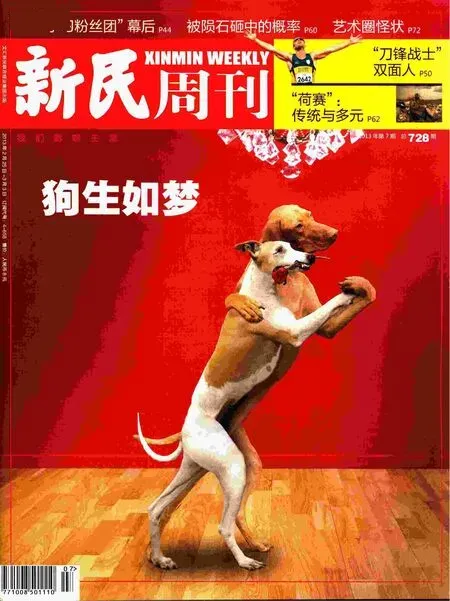風(fēng)自海上來
王悅陽



自近代起,上海的繪畫藝術(shù)就高舉起“海派”藝術(shù)大旗,曾經(jīng)占據(jù)過半壁江山,更是涌現(xiàn)了一大批諸如任伯年、吳昌碩、張大千、吳湖帆、林風(fēng)眠、謝稚柳、唐云、程十發(fā)等幾代藝術(shù)大家,獨領(lǐng)風(fēng)騷。直至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上海依舊是全國美術(shù)的重鎮(zhèn),各地的畫家以來到上海辦畫展為榮。同樣地,“海派”藝術(shù)家群體一旦有了新作,往往借著上海這方寶地,一舉打響全國的牌子。毋庸置疑,無論是中國畫、油畫還是普及性極高的連環(huán)畫、版畫,上海無疑是出作品、出大家的福地。
隨著時間的推移,前輩大師陸續(xù)凋零,文化產(chǎn)業(yè)的轉(zhuǎn)型發(fā)展,以及市場經(jīng)濟的流動變化,海派繪畫藝術(shù),輝煌不再,亟待全新的提高與發(fā)展,不僅要在藝術(shù)上承接起大師們傳下的衣缽,更要在全國的市場上打開局面,擴大影響。而近年來,無論是中華藝術(shù)宮的改造落成,還是海派畫家陸續(xù)晉京辦展取得成功,乃至在梳理城市美術(shù)文脈方面,上海的美術(shù)界,都做出了許多努力與探索。
這其中,由上海書畫院主辦的“海上風(fēng)”系列展覽,無疑是較為奪人眼球的一項,盡管舉辦至今只有兩屆,然而在學(xué)術(shù)性、前瞻性與藝術(shù)性上,上海書畫院都大膽地進行著自己的嘗試與努力。
包容性辦展
主持人:今天的研討,我們主要是圍繞第二屆“海上風(fēng)”展覽來進行一些探討和研究。我想無外乎這樣幾個主題,一個就是從“海上風(fēng)”這個展覽來看上海書畫院未來的架構(gòu)與定位,第二個就是對于當(dāng)代海派繪畫藝術(shù)的一些現(xiàn)狀的評析、梳理,第三點則是對于青年藝術(shù)家的群體性研究,從藝術(shù)院校的教學(xué)、創(chuàng)作到參與展覽,甚至走向市場的一些體會。
樂震文:這個“海上風(fēng)”的畫展,其實是在文聯(lián)的要求下,作為我們上海書畫院的一項品牌活動舉辦的。我們書畫院經(jīng)過這兩三年的實踐和探討,覺得其實海派藝術(shù)在中國有很重要的地位。海派藝術(shù)這個概念如果說得狹隘一點,就是上海畫家的作品,說得廣義一點,其實海派真的是一個包容性的畫派,它沒有具體的固定的風(fēng)格。因此我們書畫院就一直在考慮能不能把這個包容性體現(xiàn)在我們的展覽作品當(dāng)中。
這次舉辦的是第二屆,從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初,我們故意把它安排成一個跨年度的展覽。回想我們辦第一屆“海上風(fēng)”展覽,那個時候我剛來書畫院沒多久,辦展覽的經(jīng)驗也比較缺乏,就動員了一批力量,參展的作者大概有三百名左右,可是結(jié)果展示出來卻不是我希望的、要求的東西。因此我們把第二屆“海上風(fēng)”展覽做得比較細(xì)致,比較用心。首先我們不讓人家來提名,我覺得我們書畫院應(yīng)該要有這樣的能力去對上海的一些畫家進行提名,其實這個“海上風(fēng)”展是一個提名展,整個展覽從操辦開始就是基于這樣一個包容和寬泛的心態(tài)。我們上海書畫院院長是陳佩秋先生,她很主張繪畫的經(jīng)典性和繪畫邏輯思維的表達(dá),以及繪畫的藝術(shù)性表達(dá)。她一直告訴我們說,畫跟藝術(shù)是兩回事情,并不是每張畫都能稱作藝術(shù)。因此,經(jīng)典性我們是一定要傳承下來的。
其次是我剛剛說的包容性。上海的包容性,內(nèi)里輻射全國,外面輻射海外,并不是狹隘意義上的幾個人的關(guān)系,其實是風(fēng)格流派的關(guān)系。所以我提出幾種想法,一個就是東西南北風(fēng)都要包容,我最怕一個城市的展覽只是一個流派的展覽,這不能展現(xiàn)我們城市的風(fēng)貌。那么我們就故意找一些在當(dāng)今上海,甚至在全國有影響的藝術(shù)家。另外還關(guān)注美術(shù)學(xué)院那一塊,我稱它是藝術(shù)學(xué)院吹來的新風(fēng),讓這些學(xué)院的碩士生參與我們的展覽,目的就是想讓我們的“海上風(fēng)”能夠后繼有人。我在藝術(shù)院校工作過,深知學(xué)校和社會其實是脫節(jié)的,學(xué)校老師的教育和社會是兩回事情,那么我們這個平臺就是讓學(xué)校的、學(xué)院的碩士研究生能夠在沒有畢業(yè)前知道社會上整個藝術(shù)界是怎么回事情,要讓他們也能參與這個畫展。這也就是這次展覽的整體構(gòu)想和布局。
具體到選擇畫家上,我們上海書畫院的很多畫師給我們提意見,“我是上海書畫院的畫師,為什么不能參加‘海上風(fēng)的畫展?”我就告訴他,我們有一個團隊在上海精選一些有藝術(shù)造詣和有影響力的人員參加,目的就是通過上海書畫院把上海的整體實力打造出來。我們就是用我們的力量把上海畫得非常好的優(yōu)秀畫家集中推出,讓他們有一個參與的平臺。因為很多畫家跟我說,“你們上海畫展,如果要打造品牌,就要杜絕不是太好的作品進入,堅決不能因為人情而讓缺乏藝術(shù)水準(zhǔn)的作品參加,這樣才能把品牌打造得好”。
吳林田:我要說說這次展覽的背景,我們?yōu)槭裁锤氵@個展覽,它的學(xué)術(shù)背景,它的土壤產(chǎn)生的原因在哪里,我們要分析一下。
“海派”在民國的時候不是半壁江山,是“大壁江山”,90%的江山。以前的老先生就曾經(jīng)說過:“上海是個大碼頭,哪怕北京再牛的畫家也要在上海這個大碼頭走一走。”實際這個“大碼頭”是個通俗的說法,說明了什么呢,說明海派繪畫的影響力幾乎能夠在民國前后代表整個中國的中國畫創(chuàng)作的最高水平。
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這個三十年,當(dāng)代藝術(shù)因為有資本的介入,做了一些非常有質(zhì)量的展覽,所以現(xiàn)在我們聽到的所謂天價畫家,基本都是當(dāng)代繪畫范疇產(chǎn)生的。我們不要說海派繪畫,就是這個中國畫的現(xiàn)狀,實際也是令人擔(dān)憂的。大學(xué)院校出來的人對筆墨根本就不懂,樂院長在大學(xué)里本來是學(xué)院派的,他最清楚,70后、80后、90后基本上對筆墨的感情已經(jīng)沒有了,對中國畫的責(zé)任感也完全迷失了。實際上這是很不容樂觀的現(xiàn)象。
具體到這次“海上風(fēng)”的展覽,“海上風(fēng)”是什么呢?是近十多年來,比較強調(diào)海派概念的一個對當(dāng)代海派實力派畫家的集中展示。它的可貴的地方就是剛剛樂院長說的非常多元,確實有那種包容的氣度在里面。包容性,這個和海派藝術(shù)的內(nèi)在精髓是一致的。
全國性的“海派藝術(shù)”
主持人:陳九老師是朱屺瞻藝術(shù)館的藝術(shù)總監(jiān),多年來不僅自己實踐新水墨,畫得一手精彩的戲曲人物,同時也積極推動多次當(dāng)代水墨藝術(shù)的聯(lián)展,更是跨地域、跨領(lǐng)域,在全國范圍內(nèi)選擇精彩的水墨畫藝術(shù)家,不分南北,無論老幼,舉辦了多次具有影響力的展覽。這與本次“海上風(fēng)”包容性的藝術(shù)追求,無疑有異曲同工之處。
陳九:我覺得“海上風(fēng)”這個名字起得好,它其實是海上畫派、海上畫家的藝術(shù)特點。其實大家對海派有很多評價,各不相同,包括現(xiàn)在很多京派的畫家質(zhì)疑我們現(xiàn)在的海派。
吳林田:對對,上次謝春彥畫展研討會,好多人都在,來自北京的崔如琢當(dāng)場就不客氣地說上海現(xiàn)在的藝術(shù)是“垃圾”,我馬上就提出反對意見:“崔先生你對上海文化了解多少?”崔如琢聽了很不高興,但之后上海藝術(shù)家發(fā)言,居然都繞開了這個話題,都不說句公道話。我覺得,在任何場合都要維護上海畫壇的形象。
陳九:正如吳林田說的那樣,我們始終希望上海有能夠牽頭的、具有學(xué)術(shù)機構(gòu)權(quán)威性的組織來召集大家,或者把大家團結(jié)在它的周圍,扎扎實實把學(xué)術(shù)的東西做好,否則的話難免還是要被別人質(zhì)疑的。確實來說,一個藝術(shù)團體如果沒有一批很好的藝術(shù)家聚集在那里,那你對于一個地區(qū)的文化也起不了很大作用。所以我看了這次的“海上風(fēng)”,覺得從它的操作上來看,有可取之處,它也不是一下子做得很大,或者表面文章做得很多,它是慢慢地先操作起來,漸入佳境。我希望它是一個當(dāng)代海派藝術(shù)梳理的開始,或者說上海一個重要的品牌性美術(shù)展覽的開端。
從參展藝術(shù)家來看,的確它的容量似乎包容了各種年齡段、各種風(fēng)格。這也體現(xiàn)了海派的精神,特別是一批年輕人的作品參與其中。很少有人把眼光注重在年輕人身上,特別是古老的中國畫,論資排輩,甚至年輕人有些創(chuàng)新的作品還會遭遇質(zhì)疑。
另外我有一些建議,從我們整個上海地區(qū)來講,上海書畫院作為文聯(lián)下屬的一個重要平臺,如何團結(jié)上海的一批藝術(shù)家,而不是圈子藝術(shù)家,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因為在這個時代,其實形勢是不等人的,藝術(shù)家的發(fā)展,由于資本的介入以后,發(fā)展很快,又越來越多元,但是它同時又有很多被資本操作以后的異化。你如何保持藝術(shù)的純潔性,我講的就是指學(xué)術(shù)性、原創(chuàng)性,關(guān)鍵是能代表我們這個民族藝術(shù)的國際性,對于這一點,也就是精神上的堅守是比較難的。所以我希望我們以文聯(lián)為背景的這樣一個藝術(shù)機構(gòu)能夠通過它的學(xué)術(shù)品牌展覽,團結(jié)一批優(yōu)秀藝術(shù)家,而且和這個時代是同步的,它能隨時展示最新的藝術(shù)成果。我希望它是每年大家都期盼展示自己藝術(shù)的一個節(jié)日,也是一次水平的檢閱,更是成果的展示。
就以藝術(shù)作品本身的質(zhì)量來衡定。現(xiàn)在的藝術(shù)圈沒有公平性可言,來一個有錢的,他馬上把你很拙劣的畫包裝得很厲害,氣勢很大,壓過一切。這樣很可怕,我希望“海上風(fēng)”為海派繪畫帶來清新的東西,學(xué)術(shù)的東西。能夠像春雨一樣,潤物細(xì)無聲。
另外,就是希望在這么一個學(xué)術(shù)高地里,能把上海的體制外的一些有意義的小型展覽品牌,或者有一些藝術(shù)民間團體團結(jié)在書畫院的周圍。因為我覺得它完全有這個能耐,也有這個責(zé)任。
樂震文:我去年去過一次山東,其實山東對上海也蠻關(guān)注的,山東的一些美術(shù)館,包括山東電視臺等新聞媒體,還有一些畫廊的老板,都很期望我們上海美術(shù)界能去辦展覽。我一到山東,他們就跟我說,為什么上海人都不出來?因為歷史的原因,山東只知道上海有謝稚柳、陳佩秋,因為謝稚柳、陳佩秋在山東有很要好的朋友,以前他們經(jīng)常去,包括謝稚柳的很多圖章都是山東的一個篆刻家?guī)退痰模麄円惶岬街x稚柳、陳佩秋都知道,但上海其他畫家他們都不知道。所以他們跟我提出上海書畫院2013年能不能赴山東辦一個展覽,甚至他們建議說選人不要多,十幾個人就夠,每個人作品最好選四五件,這樣的話你就能展示上海國畫界的整體實力,山東方面就慢慢會知道海派是怎么回事情了。我想就從山東做起,因為山東在全國輻射力很大,全國畫家到山東去辦展的很多,山東畫家到北京去發(fā)展的也很多。那么我倒蠻有信心,就是書畫院以后“海上風(fēng)”到山東也去吹一下,這倒蠻有意思的。
第一,就是要走出去,第二要加強學(xué)術(shù)性,搞懂真正的學(xué)術(shù)是什么,第三就是要保持藝術(shù)的純潔性,這是我一直在想的幾件事情。當(dāng)然,這三點其實很難很難,要所有的畫家、藝術(shù)家的共同支持,如果大家不支持,我們也很難做到。什么叫支持?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作品拿給我們展覽,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關(guān)注青年群體
主持人:在本次“海上風(fēng)”展覽中,來自各大藝術(shù)院校的青年學(xué)生都有不少作品參展,而在匿名選拔的過程中,華東師范大學(xué)陳心懋教授的學(xué)生,錄取的比例最大,作品最多。這看似巧合,實際與陳教授多年來在藝術(shù)院校推廣當(dāng)代水墨的工作密不可分。
陳心懋:這次“海上風(fēng)”非常有新意的是有很多高校的學(xué)生作品入選,這是樂院長一個蠻新的思路。這些作品經(jīng)過選擇,經(jīng)過認(rèn)真的籌備,我覺得是有質(zhì)量的。
至于我的期望,跟剛才陳九先生講的有相似之處。我們長期在上海,水墨畫界也好,高校里任教也好,就覺得上海畫派的雄風(fēng)不再。現(xiàn)在的不少中青年畫家,或者丟棄了傳統(tǒng),或者對中國畫的理解恐怕還深入得不夠。因此導(dǎo)致全國美術(shù)界對上海的看法恐怕是非常參差不齊的,所以崔如琢當(dāng)面說上海的不好。在很多人眼里,上海的藝術(shù)家在上海本地是條龍,到外地就變條蟲。不能怪外地藝術(shù)家,他們罵上海美術(shù)界是不全面的,是不了解實情。
所以樂院長關(guān)于走出去的觀點,我覺得非常好,很及時,就上海目前美術(shù)界比較散漫的這個情況,我們怎么把它團結(jié)起來,做精,做大,做到全國去。這個工作陳九做了這么多年,我覺得很好,通過他的平臺,上海的很多優(yōu)秀的水墨畫家和全國的水墨畫家都聚到了一起。但是就像陳九所講的,他們是虹口一個地方,非常希望能有市級的一個平臺。那么這種情況也是我們上海很多藝術(shù)類高校所面臨的。就上海來說,一個上海中國畫院,一個上海書畫院,是市一級的專業(yè)性的機構(gòu)和平臺,應(yīng)該團結(jié)起高校、區(qū)級美術(shù)館等一起,來把上海的水墨畫做大做強做精,而且要做到全國去。
主持人:本次展覽所推出的青年藝術(shù)家群體的作品,是如何選擇的,兩位院長各自有著怎樣的印象與看法?
樂震文:當(dāng)初我想弄點學(xué)生作品進來,希望展覽有點意想不到的效果出來。結(jié)果學(xué)生作品陸續(xù)來了,有幾張我看了很掃興,當(dāng)然也看到一些我很振奮的作品,隨后就在這些作品中挑選出優(yōu)秀的,獨特的,風(fēng)格多樣的參展。沒想到這個事情引起幾個學(xué)校的很大的反響,有的老師就覺得哎呀你們挑選的畫不行,怎么可以挑選這樣的畫?后來我不得不改成三大藝術(shù)院校推薦,這樣一來畫院的責(zé)任好輕一點。但這也說明教學(xué)里面發(fā)生一個什么事情呢,就是老師的觀點可能會影響到學(xué)生。我覺得完全不應(yīng)該這樣,因為他們考上研究生本來就具有一定的藝術(shù)水準(zhǔn),導(dǎo)師只是在筆墨上引導(dǎo)一下然后在理念上引導(dǎo)一下。我不會把我的畫風(fēng)我的想法要求學(xué)生也這樣做。所以我很崇尚江寒汀,他教出來的學(xué)生,一人一個樣,喬木、錢行健、蕉雨、陳世中……每個人畫的都不一樣的。
基于這樣的考慮,那么其實這一屆里面的學(xué)生作品中有很多我還不是很想看到的,今天我說老實話。所以我希望第三屆“海上風(fēng)”畫展時展出的學(xué)生作品,像劉海粟一樣做做“藝術(shù)叛徒”沒什么不好。
丁一鳴:我覺得三大藝術(shù)院校各自的學(xué)生作品已經(jīng)形成一種現(xiàn)象了,而且,這一現(xiàn)象過了若干年很有可能就會影響到整個上海畫壇,所以現(xiàn)在對于這群年輕人的關(guān)注,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就叫先鋒性,就是你在很早以前就強調(diào)一種人家未知的理念,由于你敏銳,你發(fā)現(xiàn)了,它可能以后就是一個蔚為風(fēng)尚的一個藝術(shù)。
樂震文:而且我覺得藝術(shù)是表現(xiàn)給后代看的,不是表現(xiàn)給我們父輩看的,如果用這種觀點去想我們的藝術(shù)發(fā)展就對了。就像我們陳佩秋老師說的,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問題在里面,都有它的欣賞習(xí)慣在里面。
丁一鳴:我們要研究的,不僅僅是青年藝術(shù)群體,不僅是給他們展示自我藝術(shù)的平臺,更是對于群體性的推動、研究,以此來了解他們的成長環(huán)境,心理活動,了解他們創(chuàng)作的背景,以及這群人的精神風(fēng)貌。從現(xiàn)在開始,如果說能夠一直延續(xù)下去的話,絕對有好處。
海派繪畫的未來
主持人:年輕藝術(shù)家的培養(yǎng)與引導(dǎo),是每一個藝術(shù)門類所共同面臨的問題。盡管時代發(fā)展變得越來越多元,物質(zhì)條件也越來越豐富,年輕人的視野、思想與角度,都與前輩有著巨大的差異,但這并不妨礙海派繪畫藝術(shù)的傳承與發(fā)展。在日趨個性化的今天,每一條不同的道路,最終走出的,都可能是明天的希望。
鄭中榮:作為學(xué)生我感覺到,這樣一個新的時代的藝術(shù)氛圍,對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是有一個比較積極的推動作用的。
在這個展覽里,既有古典的也有一些中西融合的元素,我覺得也是當(dāng)下我們學(xué)術(shù)界想要看到的一個局面。我覺得海派繪畫不僅僅是民國時期這樣一個占全國很大部分比例的書畫派別。同時,在上海這個國際性都市背景下,當(dāng)代海派更多體現(xiàn)都市文化的特征,甚至成為一種都市文化現(xiàn)象。所以我就在想一個問題,怎么樣去把上海這個國際性跟中國畫的傳統(tǒng)性兩者更好地融合。另外,海派書畫作為都市文化的產(chǎn)物,它應(yīng)該怎樣在更大眾的層面上讓人接受并喜愛。
徐旭峰:其實,對于青年藝術(shù)家來說,現(xiàn)在會碰到這樣的現(xiàn)象,就是近期網(wǎng)絡(luò)會有一些網(wǎng)上征集藝術(shù)院校學(xué)生的作品然后進行拍賣。這其實最考驗一個學(xué)生的心態(tài)。我畫畫是為了賺錢還是為了其他的,據(jù)我了解,他們都把自己的作品傳到網(wǎng)上以很便宜的價格賣出去。借助于網(wǎng)絡(luò),現(xiàn)在成為一個主流,以打造學(xué)院青年藝術(shù)家為旗號做這樣一件事情,其實是純商業(yè)性質(zhì),非常可怕。有很多學(xué)生他沒拿捏好的話就會產(chǎn)生迷茫,尤其像現(xiàn)在的杭州、北京、四川這種現(xiàn)象特別多,上海還好。特別嚴(yán)重的像四川美院油畫系、國畫系,他們學(xué)生對整個藝術(shù)品市場非常非常了解,而對于自身藝術(shù)的發(fā)展,他們很茫然。就是說,他們會覺得我創(chuàng)作這張畫要賣多少錢,完全是以這種心態(tài)來畫畫。市場上什么風(fēng)格的畫好賣他們就畫怎樣的畫,這樣一來還怎么可能畫好?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是說我們院校學(xué)生以及我們年輕人怎么去平衡好這個藝術(shù)與市場的關(guān)系。
主持人:雖然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中文化藝術(shù)變得越來越豐富,然而,理論的高度,決定了將來能夠走得多遠(yuǎn),走得多好。對此,胡曉軍老師身為文聯(lián)研究室主任,必定有更深的體會。
胡曉軍:我是美術(shù)的門外漢,但是聽了大家一些意見,我非常有感觸。今天主要是通過“海上風(fēng)”這個展覽,探討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海派,第二個是青年藝術(shù)家群體。說起海派,大家談到的就是包羅萬象,兼容并蓄,中西嫁接,古今交匯,像這樣的內(nèi)容固然是非常重要,是它的核心。但同時,無論是老海派還是我們今后要形成的新海派,它還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它無論是“海”也好,是“風(fēng)”也好,它都有一個中心,它有一個涌動和流動的趨向。中西交融、兼容并蓄和涌動、流動,兩者是并在一起的。我們可以看到老海派領(lǐng)軍人物帶動了一種涌動和流動是如此的厲害,成就全國性的影響力,甚至影響到了海外,現(xiàn)在我們還沒有形成這樣的格局。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文化網(wǎng)絡(luò)化、信息共享化和人才流動化等等,全國不要說大城市了,就是中小型城市也呈現(xiàn)出當(dāng)時上世紀(jì)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化繁榮的景象,也就是說全國都在“海”了。我們上海已經(jīng)沒有這個優(yōu)勢了,新海派有更深層的改變就要靠當(dāng)今的藝術(shù)家群體了。
另外,我還有一個觀點,任何藝術(shù)如果我們承認(rèn)是不斷發(fā)展的話,就都有過去時、現(xiàn)在進行時和未來時,那么我們現(xiàn)在在上海,顯然對于舊海派的過去時傳承比較多一些,其實這三者是互相包容的,不過是在呈現(xiàn)上面有所側(cè)重而已,但是就現(xiàn)在“海上風(fēng)”這個表現(xiàn)來看,我感覺樂院長其實是非常想在后兩塊,也就是現(xiàn)在進行時和未來時方面更有突破。
所以說,發(fā)現(xiàn)、提攜、培養(yǎng)、推介更多的中青年藝術(shù)家的研討和交流,多聽聽他們的意見,及時總結(jié)他們的藝術(shù)思維,研討他們的作品,這個可以起到引導(dǎo)創(chuàng)作潮流、積聚藝術(shù)新的能量、催生藝術(shù)名家、營造文化新的海派氛圍的作用。而且這個作用比團結(jié)老藝術(shù)家更好做,因為他們更需要平臺。我認(rèn)為丁院長說得非常對,就是通過鼓勵年輕人的創(chuàng)新,強調(diào)他們的個性,讓他們拿出作品來,主要的目的是研究他們的心態(tài)、思維,從中加以引導(dǎo)、扶持,從中再發(fā)現(xiàn)傳承和創(chuàng)作之間的最佳點,然后再形成新的海派風(fēng)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