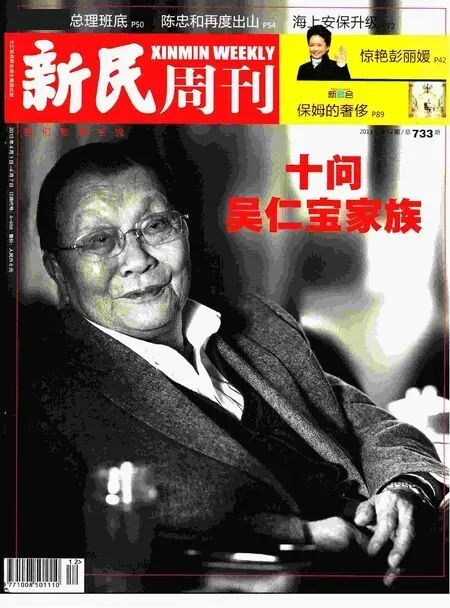飲食味外味
顧文豪
通過探尋食物背后的歷史,梁文道為我們揭示出飲食料理的文化衍變史。他無意關心食物的制作工序,而是琢磨究竟是何種力量在何種情境下使得食物成為今天的模樣。
那個向來有些自命風雅的袁枚,每回在別人家飽餐之后,都興沖沖地去人家后廚看看,向大廚執(zhí)弟子禮一一請教每道菜的食材和做法,筆錄成書,遂成《隨園食單》一冊。所謂“一世長者知居處,三世長者知服食”,穿衣吃飯,大有講究。向來有“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的中國知識分子亦不顧君子遠庖廚的訓教,津津樂道地研探這饕餮之學。不過就以這《食單》而言,袁枚熱衷的還是一事一物的原始承續(xù),刀功火候的尺度拿捏,食材調料的搭配分寸,外加飲食前后的禮儀規(guī)矩,用今天的話說,基本是用餐指南和名菜譜錄的雙核裝。
而比袁枚小了近四十歲的法國人薩瓦蘭——薩瓦蘭乳酪、薩瓦蘭蛋糕的冠名者,也寫了一冊食經:《廚房里的哲學家》。不過他滔滔不絕的問題和袁枚截然不同,論味覺、論食欲、論口渴、論消化、論節(jié)食對休息、睡眠和做夢的影響,薩瓦蘭仿若飲食界的蒙田,津液四濺地談論美食的哲學論,至于吃什么已然不重要了。
這兩種飲食書寫的路數,梁文道不用說更傾向后者。一氣推出的《味道》三冊,其實就是一回關于美食的文化史巡禮。在序言中,他特別提及歷史上第一位美食評論的作者葛立莫·德·拉·黑尼葉和他編寫的史上第一部餐廳指南《老饕年鑒》。與中國文人偏向抒情化的散淡書寫不同,黑尼葉的美食評論,實打實地以街區(qū)為分類,逐一評介各區(qū)卓越食肆,專業(yè)性不容小覷。梁文道提醒我們,這種頗為專精的食評原來其來有自,與黑尼葉所身處的法國大革命時代關涉甚深,淵源于“整個經濟環(huán)境和歷史脈絡的變動”。
因此,梁文道更關切飲食這件事背后的深閎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換句話說,食評,是否只有 “閑趣性散文和食經”這兩種寫法?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寫食評,是否也能越過食物的界限而照見更多的文化本相?
揚州炒飯,這道當年混搭淮揚菜粵菜的合成料理,勾惹梁文道興趣的并非它的口感賣相,而是日后揚州市烹飪協(xié)會企圖推出的“揚州炒飯制作標準法”,似乎完全有違這道菜最初的來歷出身,所謂獨家菜式倒是迎合了這個“知識產權無限擴大的年代”的需要?
香港一陣風似地流行吃奶酪,而三十多年前,當布爾迪厄等法國社會學家在做品味調查時,發(fā)現奶酪其實是一群中產階級的口味,多半由中學教師、中下級文化機構白領構成的這個群體,不愿在飲食上花費太多,于是選擇了奶酪,而其列名今日香港富人美食榜單,或許說明了“決定品味高下的不是品味本身,而是擁有這些品味的群體的能耐”,通過打一場品味爭奪戰(zhàn),競奪品味主導權。
20世紀中葉,牧場主通過給牛喂食混合了荷爾蒙添加劑、黃豆、魚粉的飼料,并通宵開足燈光讓牛群誤以為是白天,二十四小時吃個不停,如是四個月大就能長到四百磅,這種速肥法的推廣才使得牛肉一舉成為此后美國人的肉食之王。
通過探尋食物背后的歷史,梁文道為我們揭示出飲食料理的文化衍變史。他無意關心食物的制作工序,而是琢磨究竟是何種力量在何種情境下使得食物成為今天的模樣。換言之,或許從來沒有一道菜從誕生起到現在就是一成不變的,而任何些微改變,或許都是各種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力量的共同作用造成的。
然而飲食和社會的關系也非純然單向,不僅是社會趣尚塑造了飲食,反過來飲食也會改變我們的文化。譬如人類的同桌共食現象,古希臘的公民觀念和宰牛分吃牛肉頗有關系,讓每一個準公民分得同等分量的牛肉,吃完這頓牛肉大餐,就成了人人平等的公民,原來搞革命果真要請客吃飯。而基督教傳統(tǒng)里的圣餐儀式,不僅是最終極的同桌共食,更令全球信徒在那一剎那吃到同一具身體,達到真正精神上的“一體”。
梁文道以食物生產到被消費的過程,作為思考社會文化議題的切入口。一如其所言:“思考國家、社會不是只有時評一條路子最正宗。它們唯一的不同只是被我利用的題材不同了。”《中庸》所謂,“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梁文道將最日常可感的鮮活飲食與最玄虛的文化變遷勾連起來,則讓人體認了新一種飲食味外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