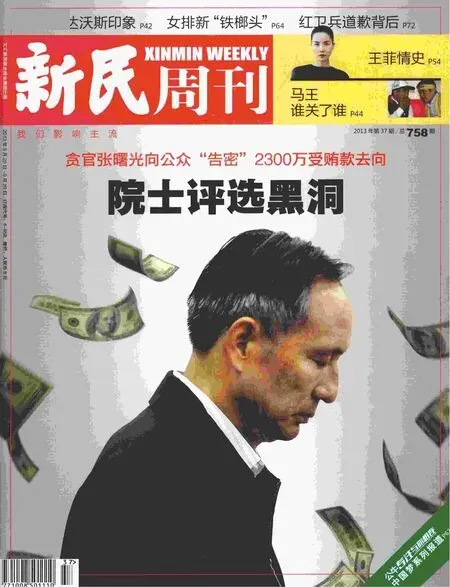亞洲的藝術思維
涂宜
在藝術品收藏領域,很長時間內中國收藏家似乎只對本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感興趣,并因此享受獲利數十倍的狂喜,而對鄰國藝術家則漠不關心。朝鮮藝術家的油畫近來成為交頭接耳的話題,那也是因為歐洲人發現了某種意識形態之外的秘密,國人趕快跟進。
日前,龍美術館推出了“亞洲線索——龍美術館亞洲當代藝術館藏展”,這是開館以來的首次國際性藝術館藏展。此次展覽由獨立策展人、批評家黃篤主持策劃,聚焦來自日本、韓國、印尼、馬來西亞和中國臺灣的30余位藝術家,展出其包括繪畫、雕塑、攝影、影像、裝置藝術在內的約40件作品。黃篤宣稱:“亞洲線索”展旨在思考和再現亞洲在迅速發展的現代化過程中當代藝術的趨勢和特征,反映和展現該地緣范疇的藝術家各自不同的視點、想象和創造,揭示其視覺圖像背后孕育的與其社會、傳統、習俗、現實、日常、語境相關的議題,探索多樣共存的、正在進行時的亞洲藝術狀態。
與收藏家的趣味相似的是,回顧中國與國際間的藝術交流,中國的美術評論家們更重視以歐美為中心的藝術,較少考慮亞洲區域的藝術問題,更缺少對亞洲內部的藝術現象進行比較和研究。因此,倘若要認清亞洲當代藝術在國際上的獨特性,就需要將亞洲當代藝術置于歷史語境與現實發展的聯系中加以考察。在這個意義上,龍美術館國際性收藏展選擇以亞洲作為起點,既是出于亞洲當代藝術的基因,又反映了亞洲文化的自覺。尋找龍美術館亞洲當代藝術收藏所揭示的內在“線索”,從而開啟中國研究亞洲當代藝術的契機和維度,是此次展覽的重要目的。
另一方面,長期來中國美術機構缺少國際性的藝術作品,這使得中國藝術評論家在國際平臺上說話不響,腰板不挺,特別是在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前提下,與國際藝術家的交流,我們總缺少一點底氣。龍美術館著手收藏亞洲藝術家的作品,是走在官方美術機構前面的,是邁出了可貴的第一步。收藏,往往是研究的基礎。
從這次展覽的形態來看,“亞洲線索”基本上是對亞洲當代藝術資源的視覺追述,且以較為年輕的藝術家的作品居多,展示了亞洲當代藝術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及其各自文化特點和鮮明個人風格,展現了亞洲當代藝術的創造活力。
來自日本的藝術家方面,除了児島善三郎和白發一雄之外,這次展覽的主要代表性的藝術家有:草間彌生、奈良美智、七戶優、北川宏人、鴻池朋子、小澤剛等。這些新一代的藝術家摒棄了歷史文化的影響,直面與流行的動漫文化的聯系,尤其將高度消費社會下的日本流行文化和動漫美學發揮得淋漓盡致。
韓國當代藝術作品,則反映了韓國藝術所始終保持的與其自身傳統文化的密切關系——浸透寺院文化和傳統色彩的美學。藝術家們將這些美學要素進行了轉譯,提升出一種新的藝術語言,強調富有詩意的境界。
策展人對中國臺灣當代藝術和以印尼、馬來西亞為代表的東南亞當代藝術的動向也給予了足夠的關注和重視。臺灣藝術經由歷史上多元時空的文化交錯,演變出獨具特色的新形態文化現象,極具生命力與鮮活的魅力。而東南亞當代藝術的發展與現狀,無論是在思想的豐富性、材質的運用、技術和形式方面,還是在語言和觀念的表現方面,都呈現出本土性、全球化和多樣化的文化特征,表現了別具一格的獨特性和多樣性。由此可見,“亞洲線索”展基本上是對亞洲當代藝術資源的視覺追述,通過對藝術家作品的觀念、語言與形式的解讀,揭示了與社會、日常、現實、傳統和語境相關的美學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