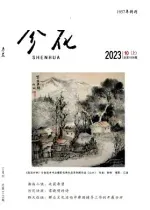由繁體字與簡體字之爭所想到的
摘要:簡述繁簡之爭的緣由,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看待繁簡之爭,剖析繁簡之爭的深層次文化原因,并應該引起我們教育界的重視。提出我們應該以開放的心態來保持中華文化的多樣性,正確堅持傳統主流文化,引導新興非主流文化。保持和發揚我們中華文化的靈動和活力,讓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煥發青春和生機
關鍵詞:繁簡之爭;教育學中的實用主義;文化教育政策;文字演變及文化的承載;國家實力在文字之爭中的體現;文化的多樣性
[中圖分類號]:H021 [文獻標識碼]:A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提出“廢除簡化字”,提議花10年時間逐步恢復使用繁體字,再次引起繁簡之爭。在呼吁“廢簡復繁”上,潘慶林并不是第一個站出來的公眾人物。
由于聯合國決定自2008年起所有中文文件一律使用中文簡體字,不再使用繁體和簡體并用的雙版本,引發了兩岸新一輪爭議。2008年全國兩會期間,郁鈞劍、宋祖英、黃宏、關牧村等21位文藝界的政協委員就曾聯名遞交了一份《小學增設繁體字的提案》,建議在小學開始設置繁體字必修課。這與近年來社會上日益升溫的重估和反省傳統文化及文化政策的整體性思潮有密切關系,正反兩方激情有余卻欠缺根本性的東西。像恢復繁體字“有利于提升現代中國在東南亞及全球的文化親和力”;或者,“恢復繁體字的社會成本太大,是一種折騰”之類,都將文字僅僅當作了工具,其他政治、經濟、社會的目標才是其目的。漢字的簡繁之爭,實際上也就被轉換成了對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不同立場和見解之辯。
作為一位一線語文老師,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繁簡之爭也引起了我的深思。追本溯源,我們現今的語言文字怎么了?追憶歷史,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三省淪陷。在敵占區,日本推行的文化政策中就有一項:從小學階段開始推行日語教育。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一商業巨頭指示,日本的商品廣告的針對對象要瞄準中國的兒童,要讓他們從小就培養對于日本商品的美好情感,培養他們要熱愛日本的產品。而我們在這里還進行繁簡之爭,什么廢繁復簡,什么廢簡復繁,難道繁體字和簡體字不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字么?
以美國實用主義教學理論為首的美國文化曾經風行一時,不能說它一點積極意義都沒有,但是同時思考一下上世紀90年代它的對華出國人員留學政策。其中一項首先要考托福,必須滿六百分才能考慮,第一類,學業優異,免試并贈送獎學金;第二類,學業不夠,拿錢來湊。不僅擄掠我國學業上的精英,更是吸取我國的經濟源泉。所以美國才成為繼英國之后又一世界霸主,其政治經濟科技等綜合國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尤其是它的先進科學技術方面更是世界矚目的方向。但是我們的頭腦不能成為外來文化的跑馬場。反觀我們中國的基礎教育,是世界所公認的扎實和穩固。我們國家是下了大力氣的。從小學、中學、大學,到下一步加大九年義務制教育,國家花費了大批人力、財力、物力來開展基礎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現在世界恰逢金融危機,各國也都使出渾身解數來應對,減少危機對本國經濟的壓力。日本近期就出臺了一項對華旅日的要求限定:年收入25萬元(人民幣)以下的人士拒游。年收入25萬元,也就是月薪20000元以上的人士,那是中國社會階層中的中產階級,是我國國民經濟活動中的中流砥柱,產業中的精英。這些人對國家的經濟活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項政策的出發點就是要進行經濟大移民。
文化教育是一項長期工程,是一項紛繁復雜的工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基辛格博士說:“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閱讀主席的全集。”毛澤東主席說:“我的那些東西沒什么。我寫的東西里面沒什么教育意義。”尼克松總統:“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國家,改變了這個世界。”所以文化教育政策不能過于簡單粗暴,因為你的教育對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生硬的產品。任何一項簡單粗暴的政策都會在一定時期后顯現出它的負面影響。所以在我們中國哈日哈韓現象從出現到成為非主流,令人心驚,應引起重視。
反思繁簡之爭,可以看出實用主義對我國歷史文化的割裂和沖擊。我們一個泱泱古國擁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文明傳承,漢字的作用功不可沒。中國文字的演變,大體經歷了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楷書——行書等幾個階段。這是符合文字的發展由繁到簡,由不規范到規范的規律的。簡體字的歷史是短,不足百年,但是就是因為它的簡便才使得知識的普及政策得以實施。正是由于簡體字的快捷和簡便,便于識記,才使文化知識普及成為可能,科技知識的推廣應用于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提高,才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得以高速發展。說“簡體字是垃圾”之說,可以讓人看到某些人的偏激和片面,還有對外開放后的一絲絲的民族自卑感。讓人感到有知識沒文化的可怕,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割裂歷史就意味著無知。
持恢復繁體字的觀點,說簡體字扼殺了繁體字的結構美,和形態表意功能,使一些漢字變得“奇丑無比”,而且切斷了文化關聯,讓人不能“望文生義”,破壞了文化的含義,且不利于中華文化的傳承,這樣的論斷未免失之偏頗。
文字具有獨立的生命、價值和邏輯,更重要的是其承載的文化基因延續使命。出于各種各樣的政治或其他目的,借助行政力量人為地阻斷或扭轉語言文字的自然演進軌跡,將導致難以預估的后果。歷史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像韓國、越南、土耳其這類使用“人造文字”的民族,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嚴重的文化危機,因而這些民族和國家近來也頗多反思。
這里的“人造文字”,指少數文字是在某一時刻,由某一群知識分子依據某種規范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在古代,日本、朝鮮、越南的語言與文字是分離的,它們使用漢字書寫;土耳其也有自己的突厥民族語言,但借用了阿拉伯字母及大量阿拉伯語詞匯。這些國家在近現代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過程中先后“發明”了自己的書寫符號,取代了原來的“帝國文字”,土耳其和越南還在很短時間內完成了文字拉丁化。
事實上,在上世紀50年代那次漢字簡化之前,也曾發生過兩次重大的語言文字“革命”。一次是2000多年前秦統一之后的“書同文”,另一次就是“五四”時期以白話代替文言的“新文化運動”。前一次基本上出于政治統治的需要,后一次則既源于政治等其他因素,又受到語言文字本身內在演進動力的有力推動。今天我們無論站在何種立場上去評價這兩次“革命”的功過得失,都不能否認它們對中國文化造成的深遠影響。
我希望漢字的“簡繁之爭”,能幫助我們加深對文化問題的理解,以為日后公共文化政策的形成提供一種比半個世紀前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視野。只有這樣,才能不流于表面的所謂進步。文化遵循著與政治、經濟不同的運行邏輯,還經常反過來對后二者施以強大的約束和影響。不妨思索一下:從“五四”到現在,從大陸到港臺,從來沒有一個法律和政策規定過書面語言必須使用白話,但為什么海內外很少有人呼吁恢復文言?相反,大陸明文規定且強制推行簡體字,為什么卻反而有那么多人贊成恢復繁體字?
但是由于繁體漢字承載了中華文化5000年的負載,加之兩岸當前政治紛爭的現狀,這場文字上的繁簡之爭難免牽涉到錯綜復雜的政治糾葛和中華傳統文化的棄收漩渦中。
簡體字與繁體字各有千秋,在這個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下,繁體字的應用之廣和簡體字的應用之便捷都不能偏執一方,繁簡之爭的背后包含著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矛盾。現在流行的周杰倫、林俊杰等人的歌曲得到部分80后90后的追捧,有繁體字的文化底蘊的功勞,在主流和非主流的文化氛圍下,網絡語言中的火星文也是一種存在。所以我們不要有什么繁簡之爭,或者廢簡復繁的提議。對待我們自己人的文化為什么不能有海納百川的胸懷呢?
廢簡立繁或者廢繁立簡皆不可取,倒可以繁簡共存。胡錦濤總書記不是講,要不折騰,這也是適用于文化教育界的科學發展觀。
那些本應該親自用毛筆寫的東西,全都用打印的方式印了出來,而在臺灣的一些新聞里,經常可以看到政府的文書,大廈的logo字,還有毛筆字,至少是毛筆字體形式的字。在大陸幾乎很難看到了。這才是漢字真正的遺憾。
繁體漢字是毛筆書寫體系下的字。事物似乎都有他自己的規律,由簡到繁,再由繁到簡。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的發展是有普遍規律的,以文字為載體的文化也不能例外。
客觀而言,簡體字的國際化已成無可阻擋的世界潮流,其簡單易學的特點更有利于向全世界推廣中華文化。別忘了,英語也曾經有過英國英語和美國英語的較量。現在,美國英語已經戰勝傳統的英國英語確立了其強勢地位。何也?語言和文字同樣受制于國家實力的消長。所以我們必須保持文化的多樣性。想當初,二戰期間,美軍的軍事情報總是被德軍截獲破譯,使得美方在戰場上非常被動。無奈之下,美軍請來了語言文字專家。專家從美國五十多個民族中挑選出少數民族印第安族,再從印第安民族中挑出極少數人口和地域的印第安民族。用這個少數民族的語言來編寫軍事密碼,再未被德方截獲和破譯,這就是美國科曼奇族軍人查爾斯·奇比蒂的故事。他帶領一小隊本族人使用一種極難破譯的密碼在戰場上傳送機密情報,使德軍無計可施。至今為止,奇比蒂使用的這種密碼仍然是軍事歷史上唯一尚未被破譯的通訊密碼。所以李大釗說,“凡一種學問,必于實際有用處,文學、史學都是如此。”史學和文學“一樣可以幫助我們為人生修養,所以也可以說是殊途同歸”,“文學是可以發揚民族和社會的感情的”。而史學對于人生,既可以像文學那樣激勵民族情感,還“可以得到一種觀察世務的方法,并可以增加認知事實和判斷事實的力量”。因此,“二者幫助人生的修養,不但殊途同歸,抑且是相輔為用,史學教我們踏實審慎,文學教我們發揚蹈歷”。那就是以民族的語言文字所構成的文學藝術和文化,是一個民族靈魂的精神家園,是一個民族凝聚力的定海神針。總之,請寶貝我們的文化吧,不要忘了我們的心靈的根在哪里。讓我們都來守護和建設我們的心靈家園,保持和發揚漢語言文學的靈動和活力。
這個爭論沒有直接的勝王敗寇的定論,因為每個人都會找到很有力量的支持自己觀點的理由,這恰恰說明了它們都有一樣生機勃勃的生命力。誰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對方,那何不讓它們并存呢?
我們可以繁簡并存,官方政府要以繁體字和簡體字并舉為要。既要重視文字的文化傳承作用,因為中華文化的古籍均為繁體字書寫;更要注重文字的傳播功用,教育措施可以考慮中小學書法課增加繁體字辨認教育,不能以使用人數的多少簡單言廢。在這樣的世界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局勢下,請保持我們中華語言文字的特色和多彩吧。
作者簡介:劉愛玉,女(1972.9.16-),中級講師,研究方向:課程與教學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