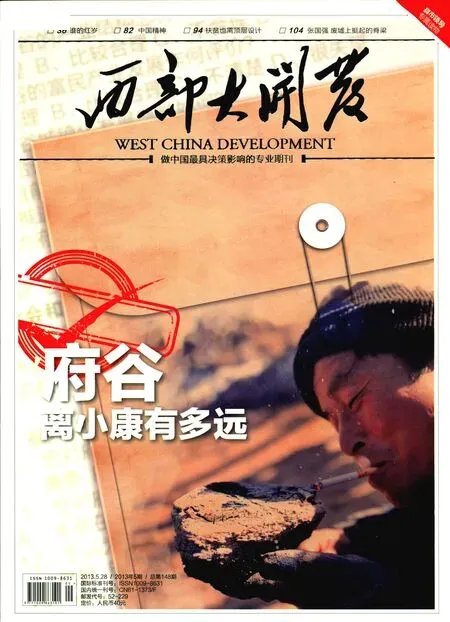“撤縣設市”大潮來臨?
□ 文/張墨寧
隨著吉林扶余、云南彌勒“縣改市”和江蘇南京完成全部“縣改區”,民政部在短期內連續批準兩個名單,被看作是“縣改市”全面解禁的信號。而僅廣東、貴州、云南、陜西四個省份,就已經有60多個縣提出了撤縣設市(區)的申請,到處是躍躍欲“市”的期盼。

“撤鎮設市”的想法也在一些東部省份醞釀。去年年底,浙江宣布在首批入選的27個實力強、人口多、城區面積大的中心鎮開展小城市培育試點,并爭取國家在浙江率先開展撤鎮設市試點,將條件具備的鎮升格為小城市。此外,江蘇、山東、湖北、安徽等省份已經或計劃開展鎮級市或強鎮擴權。
國家發改委《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初稿編制完成,各方就已經開始摩拳擦掌,準備迎接“新型城鎮化”的10年機遇。據報道,目前,全國醞釀撤縣設市(區)的縣已經有百余個,新一輪的“縣改市”、“鎮改市”大潮即將來臨。
被壓抑的“縣改市”
借著“新政城鎮化”的契機,各地重提“縣改市”,讓這一已經凍結15年的行政區劃調整再次回歸。
1997年3月12日,國務院批準了最后一個撤縣改市的行政區湖北漢川市,為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縣改市”熱暫時畫上了一個句號。中國行政區劃與地名學會副會長浦善新指出,上一輪的“縣改市”熱潮滿足了1980年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整縣改市模式基本克服了傳統切塊設市模式的弊端,解決了切塊設市模式造成的市縣并存、同駐一地、重復建設的問題,精簡了機構,減少了行政編制,有利于縣級政區的穩定。
但從長遠看,整縣改市模式違背了設置城市型行政區的基本宗旨,失去了設市的意義;市區農村人口比重過大,城郊比例嚴重失調,城鄉概念模糊,不利于城鄉分類統計及與其他國家的橫向比較,“假性城市化”造成城市化水平的混亂;市縣在地域上趨于一致,市政府在管理對象上與縣沒有區別,無法突出城市這個中心,集中精力強化對城市的規劃、管理、建設,甚至會造成城鄉兩方面管理的顧此失彼。
在“建制城市化”、“假性城市化”的發展模式下,為“縣改市”而走后門、拉關系、上報假材料等情況時有發生,并在上個世紀90年代達到頂峰。建設用地擴張進而占用耕地的現象也初步顯現,中央政府這才于1994年緊急叫停“縣改市”,1997年下半年正式凍結。
此后10年,中國的城市化進入到了飛躍性的發展期,被壓抑的“縣改市”也隨之積聚了更強烈的沖動。浦善新說,地方政府要求解凍的呼聲時起時落,有的地方甚至準備了相關的上報材料,只待中央政府一聲令下。
在此背景下,禁令開始逐漸松動。2004年,民政部提出了新的撤縣設市標準建議。盡管如此,“縣改市”的閥門并沒有完全打開,直至2010年,民政部只批復了云南蒙自、文山兩個縣撤縣設市,江西德安縣部分區域設立共青城市的申請。
縣域經濟“做大做強”的沖動、大城市發展的瓶頸使“縣改市”在新型城鎮化的助推下重新上馬,如何避免上世紀90年代的“假性城市化”、重啟市鎮體制改革則是一個全新的命題。
擴權強縣
盡管戶籍、土地管理制度并沒有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與上世紀90年代相比,新一輪“縣改市”所依托的社會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2012年全國中小城市綜合實力百強縣中,縣級市占據前30強中25席,前10強中的9席,江蘇昆山、江陰、張家港、常熟、吳江等縣級市已進入GDP“千億俱樂部”。
中國城市經濟學會中小城市經濟發展委員會秘書長楊中川2012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在全國2206個中小城市中,縣級市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占據半壁江山,未來,縣級市將成為中國城鎮化發展的中堅力量。”
擴權強縣無疑是城鎮化的下一個增長點。長久以來,如何釋放縣域經濟的活力一直是行政區劃改制的中心議題。此次改革可以說與2009年中央政府提出的“省直管縣”重大戰略、上世紀80年代的“縣改市”一脈相承。
“‘撤縣設市’對集村成鎮、并鎮成城、連城成市、加速城填化建設步伐和規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97年,城鎮化率達30%左右,去年城鎮化率到了52.6%,一半的人已經在城里了,很多縣城的人口規模、產業支撐已經有一定的規模。但與世界城鎮化的標準系數還有一定的差距。中國到現在為止,才658個城市(包括最新獲批的三沙市),城市的規模和我國的人口數量還是不匹配的。”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易鵬說,現階段城市的數量太少。
學界普遍認為,撤縣設市已經到了必須重新開啟的時候。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張占斌說,過去收緊設市政策自有道理,但是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長期下去也有問題,這個政策在推進城鎮化發展的大背景下,也需要改進。
浦善新也表示,今后增設大量的市是大勢所趨。他曾撰文稱,1997年以前,我國市的增長趨勢與城鎮化發展軌跡高度正相關,而縣改市凍結以來則呈負相關,呈停滯、倒退趨勢,與城鎮化的高速發展相背離。另一方面,1980年代以來作為主導的縣改市模式有明顯的局限性,不符合設置城市行政區的基本宗旨,也從根本上限制了市數量的增長。
“解決中國市的發展問題,不是簡單地恢復縣改市,而是在充分理論準備和宏觀考量的前提下,研究行政區劃的總體改革思路,探索新的市制改革方向。”浦善新說。他建議按照實行省、縣、鄉三級制的行政區劃改革目標,創新市制。第一,以市為基層城市型政區,總人口5萬人以上,其中城鎮人口的比重超過70%的鄉級政區可改設市;第二,以都市縣為縣級城市型政區,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60%,且至少有一個50萬人以上大城市的縣級政區可改為都市縣。
新一輪的“縣改市”必然對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戶籍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有解決長期生活在城鎮,卻并沒有市民身份的1.6億農民工的“半城鎮化”問題,實現城鄉一體的教育、醫療、就業等公共服務體系,才能避免粗放型的“城市化”。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