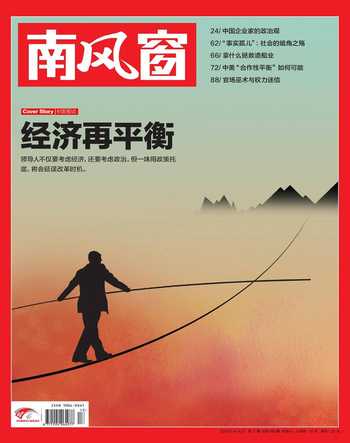政策底,還是市場底
覃愛玲

李佐軍如今已不愿多談兩年前那次內部報告中提及的經濟危機預測。在那個內部報告中,他預測,根據政府所采取應對措施的不同,危機或在2013年7、8月份出現,或將在2015、2016年爆發。
今年6月,這一內部報告被業內人士找出,在網上飛速流傳。由于這個兩年前的論述與當前經濟形勢有某些吻合之處,一時,李佐軍的宏觀經濟分析判斷能力被業界廣為推崇。
鑒于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擔憂,他愿意在可談的范圍內,就有關問題與媒體進行交流。
最壞的時候還沒有來臨
《南風窗》:您對中國宏觀經濟分為經濟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分析,很有啟發性。您認為,目前中國宏觀經濟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周期中?
李佐軍:經濟增長有長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長周期是技術進步周期(康德拉耶夫周期),約50~60年左右;中周期是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變化周期(朱格拉周期),經常與政治換屆周期疊加,約8~10年左右;短周期是存貨周期(基欽周期),約36個月~4年左右。這種分類主要是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由于中國屬于體制轉軌過程中的國家,這種分類只具有參考作用。
中國經濟正處于短周期的下降階段,從2010年二季度開始往下,這個周期的底還沒到。雖然由于刺激政策,去年四季度出現了小反彈。預計今年三四季度會繼續緩慢下行。最近中央采取了溫和刺激政策,可能會帶來一兩個季度后的小反彈,但不會持續太長時間。
從中周期看,下行從2008年就開始了,2009年初的政府刺激政策帶來了一年左右時間的快速反彈,2010年二季度重回下行通道。而2012年5月采取的穩增長措施,帶來了當年四季度的小反彈,今年一季度又重回下行通道。除非采取強有力刺激政策,否則下行將繼續。
從長周期看,從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正處于從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速增長階段下臺階的階段。
綜合以上分析,從長中短周期來看,中國經濟處于下行疊加階段。
《南風窗》: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多久才能見效,有沒有一定的規律性?
李佐軍:這要看刺激的范圍和程度。2009年一季度的強有力刺激政策,在當年二季度效果就顯現出來了。2012年5月的穩增長政策是在兩個季度后才顯示出效果。而最近中央政府采取的新刺激政策,要更溫和一些,預計產生的效果也會更小。
《南風窗》:您的意思是,這一輪中國經濟的底部,即最壞的時候,還沒有到來。根據您的判斷,這個底會在什么時候出現?
李佐軍: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周期只有市場底。但在中國,多數時候因為政府不敢面對市場底,只好不斷制造政策底,經濟增長就會出現政策底和市場底兩種情況。比如,2009年一季度的6.2%和2012年三季度的7.4%就屬于典型的政策底,其實當時的市場底還未到,但被政策底所折轉。
市場經濟有其內在的波動規律,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個中周期底部,每隔4年左右有一個短周期底部。在經濟周期尤其是中長周期下行階段,經濟增速下滑乃勢所必然,要克服對增速下降的恐懼。
增速下滑會帶來很大挑戰,應該對經濟增速過快下滑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有所防范,但增速下滑也帶來了改革、轉型和調整的機會,經濟底部是經濟系統消化矛盾和積聚新動力的休息區。一味地用政策托底,阻止市場經濟內在的發展規律,反而會延誤改革和調整時機。

中國經濟近幾年的底都是政策托出來的。只要我們停止經濟刺激,市場底就會到來。如果不采取刺激政策,經濟觸底反彈需具備以下條件:經濟泡沫已擠出,如房價等資產價格、金融暴利和實體經濟產能過剩等泡沫擠出;對中周期底部來說,作為新的增長點的新興產業形成;對長周期底部來說,新技術革命取得突破。在中國特定的國情下,制度變革取得重要進展,也會產生經濟發展的巨大紅利。
新“穩增長”爭議
《南風窗》:上半年,政府對“改革”的提法很多,并在“錢荒”等關鍵性時刻,發出“不托底”的信號,但最近一段時期,隨著“穩增長”、“合理空間”、“新4萬億”等政策話語及具體措施的出臺,給人感覺是,政府又開始出臺保增長措施了。
李佐軍:領導不光要考慮經濟,還要考慮政治。而且一種發展模式往往具有慣性,要重新開始一種新的發展模式,肯定面臨諸多難點,因此有時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行為。
但市場經濟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政策底對市場底的干預,最終還是要接受經濟規律的考驗。
《南風窗》:這次政府出臺新的“穩增長”措施后,您一直試圖將穩增長解釋為經濟不發生大起大落,而非具體的數字。
李佐軍:最近,很多人在關心穩增長的增速底線,究竟是7.5%,還是7%,或者6%等。其實,穩增長只是為了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很難有具體的經濟增速數字底線。數字是可以造出來的,高一點低一點沒有絕對意義。真正的底線應是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平穩地釋放風險,并順利地推進改革和轉型。
注意“穩增長”和以前提的“保增長”是有區別的。“保增長”是指將經濟增速保持在某個百分點之上,如“保八”;穩增長是指使經濟增速變化保持平穩態勢。保增長只能使經濟增速向上;穩增長既可使經濟增速向上,也可使經濟增速向下,只是要平穩向上或向下,防止經濟大起大落。
《南風窗》:社會上對這種新的刺激政策爭議仍然很大,不少人覺得可能會加劇經濟原有的泡沫,延緩改革進程。
李佐軍:穩增長只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暫時手段,在周期下行階段減緩下行的速度,不能改變周期。在經濟增速合理區間內,更應抓緊的是調結構和促改革。只有調結構才能擠出已有泡沫,培養新增長點,迎來可持續的健康增長。只有促改革才能為穩增長和調結構提供根本性動力。不能為穩增長而忽視了調結構和促改革。過度的穩增長會減輕調結構的壓力,延緩改革的時機。
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主要有以下四大類:一是包括出口、投資和消費在內的需求因素;二是包括勞動力、資本、資源和技術等在內的要素投入因素;三是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等因素;四是中國特色的動力因素,包括扭曲和壓低生產要素價格,壓低福利保障支出、增加經濟建設支出,刺激政策和政府企業化等。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一、三和四類因素都遇到問題、難以為繼的階段,出路在于重回“斯密定理”,依靠制度促分工,分工提效率,效率促發展。
近年來,學界、媒體和政府在討論經濟增長時,言必稱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外需不行了就擴大內需,投資不行了就增加消費。不可否認,“三駕馬車”是經濟增長的三大短期需求動力。政府喜歡這“三駕馬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種凱恩斯主義對GDP的拉動作用見效快,立竿見影。但這種短期見效的手段,往往有許多長期的副作用和“后遺癥”。
按照見效快慢排序,穩增長措施可大致排序如下:1、調整統計數字;2、央行釋放流動性(含印鈔、降息、降準、放松信貸等);3、大規模項目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如棚戶區改造);4、出口退稅和消費刺激;5、鼓勵重點產業發展(最近是信息產業和節能環保產業等);6、釋放改革紅利。
見效最快的方法,往往是“后遺癥”最大的。改革是最慢的方法,卻是長效最健康的方法。
改革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本
《南風窗》:您對中國經濟發展新動力的分析很獨特,而且特別強調“改革”對于解決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重要性。
李佐軍:對。制度變革是觀察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視角,在經濟增長供給邊“三大發動機”中,制度變革是根源性動力,因為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都依賴于制度變革。觀察中國經濟增長關鍵看新一輪改革能否順利推進,若能,則中國經濟再保持10年左右的6%~8%的中速增長是完全可能的,否則前景堪憂。
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是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的唯一出路。目前,我國經濟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相疊加的階段,世界經濟也處于深度調整之中。越是在這種矛盾集中時期,越是要依靠改革,加快改革步伐,這是過去30多年實踐反復證明的真理。因此,以經濟社會政治的全面改革促進結構調整,乃當務之急。
《南風窗》:接下來想聽聽您對當前一些具體熱點經濟問題的看法。比如,前段時間出現的“錢荒”,您覺得反映了什么問題?
李佐軍:“錢荒”反復來襲的最主要原因是,制度和模式導致經濟整體效率下降,政府干預經濟過多,資金被配置到不合理地方。7月底銀行間拆借利率重新上升,部分銀行提高抵押貸款利率和理財產品收益率,取消房貸優惠,說明錢荒還未走遠。
中國經濟問題的主要表現是高房價、錢荒、債務風險和產能過剩等,追根溯源是企業效率和國民經濟配置效率的下降。造成兩個效率下降的原因是企業成本上升、創新活力減少、國有企業過多進入競爭性領域、政府控制資源過多且進行低效率經營,而這些又是由政改與經改不平衡造成的。
《南風窗》:最近中央要求全面審查地方債務,反映了對地方債務問題的巨大擔憂,就您來看,目前地方債的風險有多大?
李佐軍:兩年前,隨著大規模投資集中還款期的到來,一些地方政府就開始面臨很大的債務償還壓力,但因有如下招數,很多風險被暫時掩蓋了:繼續賣地,以及房價上漲的助力;債務延期展期;借新還舊;強征預征稅收等。但這些舉措并不能從根源上化解債務,只是將矛盾后推了。
要化解地方債務危機,根本出路是政府要回歸公共服務職能,將經濟職能交給企業和市場,政府不能辦企業;從政績考核上,不能再以GDP論英雄;還有就是,硬化政府預算約束,建立投資決策失誤責任終身追究制。
《南風窗》:您如何理解最近國務院出臺的“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這一政策?
李佐軍:從以往經驗看,在土地、財稅等制度不改革情況下進行房地產調控效果不好,而這些改革尚需時日,為避免愈調愈漲,所以提平穩健康發展。房價波動牽一發動全身,為嚴防金融風險,故促房產市場平穩發展。房地產積弊甚多,必須推進改革和轉型,故要促其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