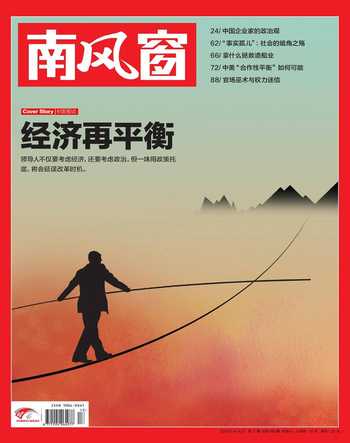另類學(xué)者潘毅
甄靜慧

眼前這個女人瘦瘦小小,穿著寬大的亞麻衣服,挎?zhèn)€麻布包包,走路時闊袍大袖揚起來,似乎大風(fēng)一刮就會飄走。她一開口說話就瞇著眼睛笑,就像我們已經(jīng)很熟了,怎么都無所謂。
第一次見到她是2011年,其時她正帶著西班牙經(jīng)濟學(xué)教授Inaki滿中國跑,在北大、中大、香港理工大學(xué)演講,“推銷”蒙德拉貢合作社的社會經(jīng)濟實踐經(jīng)驗。第二年,又聞?wù)f她在北京折騰社會經(jīng)濟論壇。
似乎不易理解,這個從“資本主義的”香港來的學(xué)者,卻對社會主義有著異乎尋常的執(zhí)著,并批評“沒有經(jīng)濟民主作為基礎(chǔ)的民主是虛偽的民主、不徹底的民主”。
她還有個“怪僻”,對跟隨她讀碩士、博士的學(xué)生有個不成文“規(guī)矩”—不允許他們畢業(yè)后呆在高校的學(xué)術(shù)殿堂里,把他們通通“趕”下去,回內(nèi)地當(dāng)基層干部、辦NGO。
事實上,她自己呆得最多的地方也是“田野”。聞知我要約訪她,一位記者咋呼著說,“她一定不簡單”—這位記者曾聽她學(xué)生說,去年他們?nèi)プ鰤m肺病調(diào)研,貧窮鄉(xiāng)村土房子條件太差,為了涼快點,晚上她直接躺倒在泥土地上睡,由是生出驚嘆,“什么教授能睡土地板啊!”
從早期女工,到建筑工人、富士康、煤礦工人,潘毅的關(guān)注點始終著眼在中國內(nèi)地工人問題上,這樣的課題不要說在香港學(xué)術(shù)界根本沒人感興趣,上世紀(jì)90年代即使在中國內(nèi)地也少人問津。
她是潘毅,一個接地氣的香港理工大學(xué)社會學(xué)教授。
不走尋常路
你要是問潘毅,“在香港學(xué)術(shù)界,你可算一朵奇葩?”她會興高采烈答,“是是是。”仿佛那是一種榮耀。
她當(dāng)然有在學(xué)術(shù)主流中揚名立萬的資本。在極其崇尚精英主義的香港,她的學(xué)術(shù)道路順?biāo)斓眠B自己都感嘆:1998年于倫敦大學(xué)完成人類學(xué)博士學(xué)位即進入香港科技大學(xué)任教;2005年因《中國制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下稱《中國女工》)一書獲得被譽為“社會學(xué)界奧斯卡獎”的米爾斯(C. Wright Mills)獎;剛剛40歲出頭便升任香港理工大學(xué)正教授,在香港高校中算得上是年輕有為。
然而,早在10多年前于倫敦大學(xué)攻讀博士學(xué)位的時候,她就隱約意識到,自己將來可能不會走一條主流的學(xué)術(shù)道路。
與那些安安穩(wěn)穩(wěn)呆在學(xué)術(shù)殿堂里的學(xué)者不一樣,潘毅個子雖小,卻特能折騰。你要是突然給她打個電話,她多半不在香港,要么在工地聽故事,要么在塵肺村睡地板,要么正在大東北煤礦把自己鬧得灰頭土臉。“我相信‘現(xiàn)實社會的復(fù)雜性大于理論,理論是由復(fù)雜的社會現(xiàn)實抽象出來的。所以我的根基是深入社會進行調(diào)研。”她反對很多學(xué)者“理論先行,然后套入現(xiàn)實社會”的方式。
《中國女工》是她因關(guān)注中國工人問題嶄露頭角的“第一炮”。2007年,她又盯上了內(nèi)地建筑行業(yè),召集一波又一波的學(xué)生,在建筑工地調(diào)研,在媒體撰文、發(fā)布大量調(diào)研報告,質(zhì)疑大行其道的“建筑包工制”。
一般學(xué)者調(diào)研,目的是做出學(xué)術(shù)成果,但于潘毅而言,那才是剛剛開始。她的調(diào)研報告均成系列:新鮮出爐,先到處聯(lián)絡(luò)媒體和網(wǎng)絡(luò),向公眾發(fā)布;然后她會關(guān)注問題有沒有改善,于是再去調(diào)研、發(fā)布報告。甚至同時發(fā)起社會行動、成立NGO,直接推動問題的解決。
較為完整地觀察她,會發(fā)現(xiàn)一條“調(diào)研-通過媒體施壓-社會行動/成立NGO-再調(diào)研-再施壓”的脈絡(luò)。她非常喜歡媒體,喜歡到一個記者跟她說話時完全嗅不到學(xué)者式的矜持。聽到特別有價值的問題時,她還會興奮地拍桌子,笑得牙齒露出來,眼睛看不見了,說,“對對對,這個你寫,這個你寫。”
她有一股韌勁,一旦盯上了某個認(rèn)為不對勁的問題,就死咬不放。
2010年,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yè)富士康發(fā)生員工連環(huán)跳樓事件,她與內(nèi)地、臺灣學(xué)者聯(lián)合,成立兩岸三地學(xué)者調(diào)研團隊,做出一份超過7萬字的調(diào)查報告,列舉了富士康“六宗罪”:濫用學(xué)生工、生產(chǎn)體制充滿規(guī)訓(xùn)與懲罰、工人生活空間被多重擠壓、缺乏勞動保護且瞞報工傷、陌生冰冷的朋輩關(guān)系、工會形同虛設(shè)。
半年后的2011年3月,他們又針對“富士康是否在內(nèi)遷廠區(qū)中改善了用工待遇和條件”進行第二次調(diào)研,這次潘毅要求部分學(xué)生以普通工人身份打入富士康內(nèi)部,親身體驗一個多月的打工生活。兩個月后,第二份調(diào)研報告出爐。
轉(zhuǎn)眼間3年過去,社會關(guān)于富士康的討論雖然尚未停止,但各方關(guān)注無疑已經(jīng)漸漸冷淡下來。唯在潘毅這里并非如此,她和學(xué)生們?nèi)阅鼗钴S在富士康周圍:調(diào)查、監(jiān)督,為工人提供服務(wù)、培訓(xùn)。還有一些零散的調(diào)研結(jié)果出來,以致有媒體編輯說,“現(xiàn)在最怕聽潘老師提富士康”—新聞熱度確實過去了,但又知她的滿腔義憤,不忍潑她冷水。
從早期女工,到建筑工人、富士康、煤礦工人,潘毅的關(guān)注點始終著眼在中國內(nèi)地工人問題上,這樣的課題不要說在香港學(xué)術(shù)界根本沒人感興趣,上世紀(jì)90年代即使在中國內(nèi)地也少人問津。作為一個民間學(xué)者,她的犬齒不算太鋒利,被她咬一口不至于傷筋動骨,但只要問題一天不解決,她會10年如一日地一直咬,令企業(yè)和政府部門如芒在背,不得安寧。這種主動與媒體交好和“死纏爛打”的風(fēng)格,也與香港學(xué)術(shù)界的精英主義格格不入。“她的行事風(fēng)格更像NGO。”另一位媒體人說。
反精英
在潘毅看來,她之所以變得“另類”,與她的成長經(jīng)歷不無關(guān)系。
“我在內(nèi)地出生,小學(xué)4年級才移民香港,把很多早期社會主義的記憶帶到了香港。”因為新移民身份,她既看到香港繁榮的一面,也看到了社會的分化。“在這里出身很重要,中產(chǎn)家庭的下一代會一直保持相應(yīng)的生活水準(zhǔn),沒錢的人則再過幾代都不可能買到房子,有錢人和窮人生活的社區(qū)完全隔離,幾乎不可能通過個人努力改變命運。”
“香港也不是所謂福利的天堂。財富被壟斷在少部分人手里。當(dāng)一個公務(wù)員、一個大學(xué)老師,你可以過中產(chǎn)以上生活,買樓,送孩子到國外讀書。但普通人呢,沒有失業(yè)金,沒有養(yǎng)老金,最低工資也是近兩年才出現(xiàn)的。”
潘毅并不是這種社會體制的受害者,恰恰相反,她本是個不大不小的“既得利益者”:雖是新移民,家庭條件卻相對富裕,自己又是被視為精英階層的高校教授。但她厭惡從這樣的社會分化中獲益。
“我是一個非常反精英的人。”她說,在香港和英國,親眼目睹資本主義發(fā)展成熟的結(jié)果,內(nèi)心非常失望,因此對曾經(jīng)生活過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定想象。然而,當(dāng)她真正踏足中國內(nèi)地,襲來的是別樣的感受。
那是上世紀(jì)90年代初,正值大批港臺企業(yè)將生產(chǎn)線往大陸轉(zhuǎn)移,正在念大學(xué)的她跟著師兄師姐到珠三角早期工廠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一件衣服在香港賣5000元,工人每月只有一兩百元工資”;工人被要求住在工廠,窗戶裝上密密的鐵欄,防止他們偷了東西往外扔;“工廠經(jīng)常發(fā)生火災(zāi),他們無法逃生,一次就燒死七八十人”。
她震驚了,難以理解:“為什么我們要(為市場經(jīng)濟)付出這樣的代價,這種付出是否必要?”后來,她撰寫博士論文,自然而然選擇了“中國女工”為課題,且在珠三角的工廠呆了七八個月,與“打工妹”們同吃同住,跟著她們探親訪友、回鄉(xiāng)過年,同時,看著她們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工傷、懷孕、墮胎、自殺……
這次刻骨銘心的田野調(diào)查,奠定了她后來“劍走偏鋒”的學(xué)術(shù)方向。
“我不能接受,一個社會主義制度允許自己的工人一天工作14個小時,沒有周末,一間集體宿舍住著幾十名工人,一把火就把他們燒死。”總是笑瞇瞇的她罕有地露出交織著悲傷和憤怒的表情。
“我比其他知識分子更早看到工人所面臨的處境,或者說階級矛盾的問題。”當(dāng)她這么說的時候,非關(guān)炫耀,有的怕是孤獨與憂傷。
從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jì)初,她一再找其他學(xué)者探討,漸漸明白彼此分歧所在。“香港是資本主義的天堂,大學(xué)教授在這里享有地位和資源優(yōu)勢,大部分人都不會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有所質(zhì)疑。內(nèi)地學(xué)者則往往對資本主義社會諸如‘美國夢懷有向往。他們認(rèn)為,當(dāng)時的種種問題只是‘陣痛,是因為市場經(jīng)濟還不成熟、監(jiān)管不力,如果繼續(xù)開放市場,問題就解決了。”
“然而,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經(jīng)驗告訴我并不是這樣的。香港夠成熟了吧?現(xiàn)在中國內(nèi)地的社會矛盾,就是當(dāng)年香港的矛盾。”
“我無法站在高處看別人的痛苦”
“怎么辦?社會主義!”潘毅說。但她絕不承認(rèn)自己是“左派”。“左派人士寄希望于上層人士的改革”,她恰恰相反,對官僚架構(gòu)和公知群體均不抱希望。
她辦公室的書架上,放著四五個版本的《中國女工》,書的原版是英文,2005年出版后被譯為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波蘭文、中文出版發(fā)行。然而鮮少有人知道,這本書1997年就寫完了,被她擱在一旁,一直到需要參評科大終身聘用制資格時,才不得已發(fā)表。
原因是,她“不知道這本書寫給誰看”。“寫書的時候,用了在當(dāng)時很前衛(wèi)的后現(xiàn)代理論”,完稿,她即反思:這樣的書,學(xué)術(shù)圈看了有用嗎?女工們呢,根本看不懂。“成名作”的寫作在她看來是極不成功的。
醞釀這本書的1996年,潘毅和同學(xué)完成中國女工調(diào)研項目后,在深圳成立“女工服務(wù)中心”,即現(xiàn)在“女工關(guān)懷”的前身,這是中國內(nèi)地早期勞工NGO的雛形。此后,潘毅每做一個工人群體的調(diào)研,都會成立相關(guān)的NGO,為該群體服務(wù)、培訓(xùn),力求提升其自我保護和維權(quán)意識等基本素質(zhì)。而服務(wù)于這些NGO的,多為她的學(xué)生。
“做完學(xué)術(shù)調(diào)研,我會感到很內(nèi)疚,接受不了自己作為一個研究者,看到了別人的痛苦,完成自己的研究,然后離開。”她也不允許自己的學(xué)生這樣做,“我要求他們畢業(yè)后全部去基層工作,有這個共識,才來跟我。”
博士生梁自存來自中國內(nèi)地,原來在清華大學(xué)讀碩士,隨潘毅做過一些調(diào)研,就鐵了心要跟她。我們見面的時候,攝影師正在替潘毅拍照,他“撲哧”一聲笑,“還以為誰在拍婚紗照呢。”潘毅指著他嚷嚷:“這個學(xué)生很壞!”
大男生眼里的潘毅亦師亦友,“她待人完全平等,生活中你不會把她看成老師”,但內(nèi)心的尊重并不稍減分毫。潘毅跑過來反駁,“哪里平等,他經(jīng)常欺負(fù)我。”我們趕她走,她又“蹬蹬蹬”跑開了。
讀研時,梁自存曾想到高校任教,現(xiàn)在完全改變了主意,打算畢業(yè)后回內(nèi)地成立勞工NGO。這條路已有很多師兄師姐走過—近四五年,潘毅沒有招過一個香港學(xué)生,追隨她的都是來自中國內(nèi)地,愿意在社會底層服務(wù)的青年。
潘毅的寫作風(fēng)格也在不斷的調(diào)整中發(fā)生變化。“現(xiàn)在我的目標(biāo)很清晰,所有書都是寫給大眾,寫給工人群體看的,我希望扮演一個啟蒙教育的角色,教育應(yīng)該是為平民而做的。”
她并非苦大仇深的那種人,卻熱衷于踐行改造社會的理想。“我現(xiàn)在想回內(nèi)地教書,再也不寫那什么鬼的英文著作了。”最后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