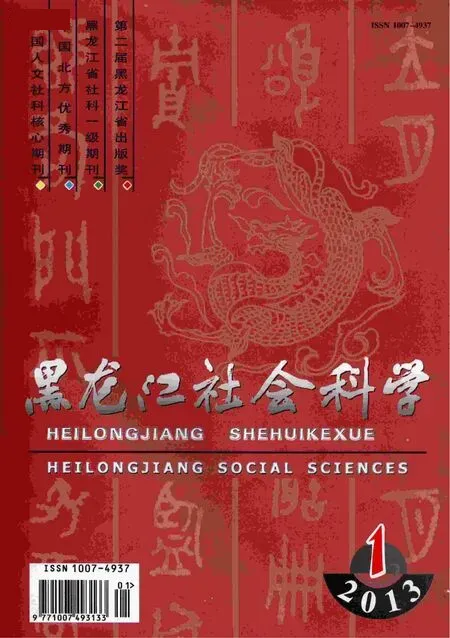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演化特征與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
劉 琳,賈根良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 經(jīng)濟(jì)學(xué)院,北京 100872)
一、處于“十字路口”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
眾所周知,現(xiàn)代人類活動(dòng)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影響日益擴(kuò)大。第二次工業(yè)革命奠定了大規(guī)模生產(chǎn)范式的主導(dǎo)地位,人類也開始不斷驅(qū)使“永不停歇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車輪”。時(shí)至今日,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對(duì)自然資源的依賴和耗竭已經(jīng)達(dá)到了空前水平,對(duì)“經(jīng)濟(jì)車輪”賴以依附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破壞也無以復(fù)加。這是近年來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作為一門倡導(dǎo)“從最廣泛意義上研究生態(tài)系統(tǒng)與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之間復(fù)雜關(guān)系的學(xué)科”,獲得了較高關(guān)注和迅速發(fā)展的原因之一,它也被寄望能夠更好地解決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生態(tài)保護(hù)的兩難困局。
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與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及其環(huán)境學(xué)科分支有著很大不同。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是在自然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約束下,研究如何實(shí)現(xiàn)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一門學(xué)科。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持有有機(jī)的、整體的世界觀,相比機(jī)械的、原子論的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將資源配置效率放在首位的狹隘觀點(diǎn),“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認(rèn)為有效配置很重要,但本身絕不是目標(biāo)……更重要的是規(guī)模和分配。”[1]由于在理論基礎(chǔ)、分析框架和學(xué)科目標(biāo)等整體上均體現(xiàn)出了優(yōu)勢(shì),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被認(rèn)為在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掀起了一場(chǎng)“生態(tài)革命”。
一般認(rèn)為,肯尼斯·博爾丁于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提出的“宇宙飛船地球”、“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和“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等一系列生態(tài)經(jīng)濟(jì)觀點(diǎn),是當(dāng)代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興起的標(biāo)志。從博爾丁開始,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逐漸發(fā)展融合了哲學(xué)(環(huán)境哲學(xué)、生態(tài)倫理)、物理學(xué)(熱力學(xué))、生物學(xué)(遺傳學(xué)、進(jìn)化論、生態(tài)學(xué))和經(jīng)濟(jì)學(xué)(外部性理論、福利經(jīng)濟(jì)學(xué)、產(chǎn)權(quán)理論、行為經(jīng)濟(jì)學(xué)等)等諸多學(xué)科的思想。但是,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xué)科,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迄今為止在諸如理論基礎(chǔ)、基本假設(shè)和研究對(duì)象等諸多問題上仍存在大量分歧,以至于許多學(xué)者對(duì)搞清楚“什么是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這一基本問題抱著一種無所謂的態(tài)度,甚至認(rèn)為沒有必要?jiǎng)澐制鋵W(xué)科屬性[2]。這種“認(rèn)識(shí)論”缺陷極大地限制了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發(fā)展和完善。
為了便于比較分析,筆者對(duì)當(dāng)代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研究領(lǐng)域內(nèi)的一些主要學(xué)科及其特征進(jìn)行了簡(jiǎn)單歸類(如下表所示),需要注意的是,表中的每列學(xué)科之間都是相互交叉和滲透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與其相鄰學(xué)科之間的交叉聯(lián)系錯(cuò)綜復(fù)雜,對(duì)其認(rèn)識(shí)的諸多分歧也集中于此。如趙金龍等(2010)認(rèn)為,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屬于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范疇[2],這實(shí)際上是將其與新古典傳統(tǒng)為主的資源與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劃為一類。彼得·巴特姆斯則認(rèn)為,“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涵蓋了一個(gè)寬泛的主題,這些主題有一部分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的主題,也包括人類生態(tài)學(xué)和生物經(jīng)濟(jì)學(xué)等新的派生領(lǐng)域。”[3]25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下表中使用了“制度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一詞作為一類學(xué)科的統(tǒng)稱,它們的共同特點(diǎn)是,都將(廣義的)制度或其中的某些因素納入分析框架之中。如馬克思主義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生態(tài)社會(huì)主義和公害經(jīng)濟(jì)學(xué)等,都在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的分析中納入了對(duì)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但這類學(xué)科中的多數(shù),現(xiàn)在基本上被主流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視為異端思想而遭到排斥。對(duì)于“協(xié)同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認(rèn)識(shí)尚存分歧:有些學(xué)者認(rèn)為,以Norgaard 等人為代表的協(xié)同演化理論是將生態(tài)學(xué)的協(xié)同進(jìn)化原理應(yīng)用于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乃至整個(gè)社會(huì)變遷的分析,因此其某些領(lǐng)域可以部分地歸入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研究范疇;有些(包括筆者)則認(rèn)為其更多地屬于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分支,因?yàn)樗脱莼?jīng)濟(jì)學(xué)一樣為事物的發(fā)展機(jī)制提供了解釋;而Kallis則認(rèn)為協(xié)同演化理論更多的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方法論,而非某種具體理論[3]66。

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與其交叉學(xué)科
上表羅列了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與其交叉學(xué)科之間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在研究對(duì)象上,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資源與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制度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雖然都關(guān)注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問題,但是側(cè)重點(diǎn)卻各有不同。在基本世界觀和人性假設(shè)上,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制度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協(xié)同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差別不大,但資源與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卻是個(gè)顯著例外,這主要?dú)w因于它們各自信奉不同的哲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基礎(chǔ)。對(duì)于學(xué)科目標(biāo)而言,資源與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追求納入負(fù)外部性考慮后的福利與增長(zhǎng)的最大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則首先關(guān)注可持續(xù)的規(guī)模和公平;制度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某些領(lǐng)域則比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更進(jìn)一步,主張縮減一切物質(zhì)規(guī)模,并尋求所有物種之間的平等和正義;協(xié)同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則主要關(guān)注主體與其外部環(huán)境間的互動(dòng)和演化機(jī)制。學(xué)科目標(biāo)的不同也導(dǎo)致這些學(xué)科在分析工具上各有特點(diǎn)。
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工具和政策主張上,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和資源與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顯示出了高度的相似性,而制度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則往往排斥數(shù)學(xué)模型和市場(chǎng)工具。與在理論層面的革命性相比,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在實(shí)踐層面卻并無高明之處,它實(shí)際上是一種糅合了資源與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制度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環(huán)境政策的“大雜燴”。
“政策大雜燴”是新舊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理論調(diào)和的結(jié)果。事實(shí)上,許多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研究者一直在嘗試調(diào)和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與新古典傳統(tǒng)的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理論。赫爾曼·戴利可算做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成果反映在其最近出版的教科書中。從某種程度上看,戴利等人的調(diào)和是成功的,他們幾乎在傳統(tǒng)學(xué)科的所有舊領(lǐng)域內(nèi)闡發(fā)了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的新思想。但遺憾的是,這種調(diào)和卻難以避免對(duì)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路徑依賴”。在某些方面,許多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實(shí)際上沿襲了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的靜態(tài)思維,如評(píng)價(jià)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環(huán)境影響時(shí),他們還是傾向于成本—收益分析,只是需要重新評(píng)估生態(tài)服務(wù)和自然資源的價(jià)值。同時(shí),多數(shù)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也主張將福利經(jīng)濟(jì)學(xué)、行為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實(shí)驗(yàn)經(jīng)濟(jì)學(xué)等學(xué)科的研究成果運(yùn)用于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研究領(lǐng)域。這部分導(dǎo)致了包括戴利在內(nèi)的許多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在理論構(gòu)架和政策建議上與傳統(tǒng)環(huán)境理論的區(qū)別不夠突出,甚至大同小異。
與戴利等大部分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對(duì)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學(xué)所持的鮮明批判態(tài)度不同,有些研究者則過于樂觀地認(rèn)為,只要解決了“規(guī)模問題”和“估值問題”,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就可以實(shí)現(xiàn)與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無縫對(duì)接”。于是他們開始沉迷于“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和閾值計(jì)算”、“生物多樣性的測(cè)度”和“自然資源與生態(tài)服務(wù)的價(jià)值估計(jì)”等技術(shù)問題。然而,由于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之間的復(fù)雜聯(lián)系和動(dòng)態(tài)多變,準(zhǔn)確測(cè)算任何“閾值”不僅在理論上難以實(shí)現(xiàn),而且在實(shí)踐中也缺乏檢驗(yàn)事實(shí)——如果允許超越生態(tài)閾值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崩潰的出現(xiàn),以驗(yàn)證估算的準(zhǔn)確性,那么這種估算本身就將失去意義。生物多樣性水平的測(cè)度也存在著因人類認(rèn)知能力的局限性而對(duì)物種破壞和滅絕程度的嚴(yán)重低估。而對(duì)自然資源的使用價(jià)值和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服務(wù)價(jià)值進(jìn)行計(jì)算,雖然有利于進(jìn)行成本—收益分析,以便將其納入主流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分析框架,但是卻將使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重回新古典傳統(tǒng)的靜態(tài)均衡分析,更是“唯市場(chǎng)論”在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研究領(lǐng)域的入侵,這是與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生態(tài)本位觀根本相悖的。事實(shí)上,過分注重成本—收益分析等靜態(tài)比較,并偏好數(shù)學(xué)模型的構(gòu)建,已經(jīng)在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中造成了比較嚴(yán)重的“思維靜態(tài)化”和“數(shù)學(xué)形式化”,其某些研究領(lǐng)域甚至已經(jīng)被新古典理論的靜態(tài)框架所同化。正如John Gowdy & Jon Erickson(2005)所指出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正處在十字路口上……(我們不應(yīng)該在)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新瓶中裝上瓦爾拉斯的舊酒”。
二、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演化屬性與制度視角
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多學(xué)科交叉特點(diǎn)和有機(jī)的生態(tài)本位觀,決定了其應(yīng)當(dāng)采用一種系統(tǒng)性的研究視角,兼顧研究維度的整體性和演化性。但是目前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研究更多地采用了整體的而非演化的視角,它注重探究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之間的交互聯(lián)系,卻鮮有為系統(tǒng)的發(fā)展演變機(jī)制提供解釋。在目前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的四大前沿領(lǐng)域(即工業(yè)生態(tài)學(xué)、環(huán)境庫(kù)茲涅茨曲線、生態(tài)系統(tǒng)穩(wěn)定性和生態(tài)足跡)中,只有“環(huán)境庫(kù)茲涅茨曲線”部分地關(guān)注了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與環(huán)境變化之間的動(dòng)態(tài)演化關(guān)系,其他則偏重以整體視角對(duì)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之間的聯(lián)系和互動(dòng)進(jìn)行考察,如運(yùn)用了生物群落共生性類比的工業(yè)生態(tài)學(xué)就尤為明顯。另外,目前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研究集中在自然、城市和區(qū)域三個(gè)層次上,這基本上是按照生態(tài)或社會(huì)要素的共生性或聚集性劃分的。這種劃分方式本身有利于整體性視角在研究中的運(yùn)用,卻不易進(jìn)行演化動(dòng)態(tài)分析。也就是說,目前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持有一種不完善的系統(tǒng)性研究視角,它正在用整體性的“長(zhǎng)腿”和動(dòng)態(tài)性的“短腿”跛足前行。
事實(shí)上,無論是從思想還是從理論淵源上看,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都應(yīng)具有先天的“演化特質(zhì)”。首先,從思想淵源上看,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誕生本身就是達(dá)爾文的進(jìn)化論思想廣為傳播的結(jié)果。自《物種起源》發(fā)表之后,事物的變化作為一種演化過程的觀點(diǎn)已逐漸被自然和社會(huì)科學(xué)的諸多領(lǐng)域所接納,這些領(lǐng)域的新發(fā)展也反過來為進(jìn)化思想提供了佐證。在熱力學(xué)上,“熵”定律決定的時(shí)間單方向性和孤立系統(tǒng)復(fù)雜程度的不可逆性,為生物和社會(huì)由簡(jiǎn)單到復(fù)雜、由低級(jí)到高級(jí)的進(jìn)化路徑提供了理論支持。在生態(tài)學(xué)上,達(dá)爾文主義則為生物多樣性、共生、競(jìng)爭(zhēng)及其進(jìn)化提供了一種自然選擇的機(jī)制。而在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達(dá)爾文主義則展現(xiàn)了一種非決定論的和開放系統(tǒng)的歷史觀。因此,達(dá)爾文主義并非生物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的特定理論,而是復(fù)雜演化系統(tǒng)的一般理論[4]。可以說,正是演化思想潛移默化地滲透到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的交叉研究領(lǐng)域內(nèi),才導(dǎo)致了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產(chǎn)生。再者,從理論淵源上看,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兩位主要奠基人物尼古拉斯·喬治斯庫(kù)-羅根和肯尼斯·博爾丁,對(duì)演化思想同樣作出過重要貢獻(xiàn)。羅根的演化思想集中體現(xiàn)在他將熱力學(xué)和生物學(xué)的隱喻和類比應(yīng)用于對(duì)經(jīng)濟(jì)乃至社會(huì)的分析之中;博爾丁則發(fā)展了一種類似生態(tài)動(dòng)力學(xué)的演化理論,并在1981年出版了以《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命名的學(xué)術(shù)專著。雖然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他們是否屬于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尚存爭(zhēng)議,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他們都持有演化的研究視角,并致力于在生態(tài)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和社會(huì)學(xué)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如今學(xué)術(shù)界普遍公認(rèn)的演化經(jīng)濟(jì)思想尤以納爾遜和溫特等人的觀點(diǎn)最具代表性,然而“以博爾丁和羅根等人為代表的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在時(shí)間上還要早于納爾遜和溫特的演化思想,但過去并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楊虎濤(2006)則明確指出,肯尼思·博爾丁、赫爾曼·戴利和尼古拉斯·喬治斯庫(kù)—羅根等三位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奠基人物,都是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生態(tài)思想代表人物[5]。
那么,為何當(dāng)代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卻忽視了“演化”這一重要屬性呢?筆者認(rèn)為,主要原因是由于當(dāng)代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在研究中實(shí)際上是排斥制度因素的,從而制約了其研究框架的系統(tǒng)性。從上表可以看出,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與制度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最大區(qū)別,就在于是否廣泛考慮了各種(廣義的)制度因素,而協(xié)同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更是側(cè)重為這些制度因素聯(lián)合體的演化機(jī)制提供解釋。盡管在某些研究領(lǐng)域,如對(duì)某些狩獵—采集型社會(huì)的分析中,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較充分地考慮了制度因素及其變遷,并注重演化分析和歷史比較,但這只是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領(lǐng)域內(nèi)的“小眾”。多數(shù)情況下,制度因素更多地被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視為外生變量。對(duì)那些納入制度因素的交叉學(xué)科,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甚至隱含地抱有一種蔑視態(tài)度。如戴維·皮爾斯就曾諷刺環(huán)境倫理學(xué)者的道德說教對(duì)環(huán)境事業(yè)并無幫助;而彼得·巴特姆斯則批評(píng)協(xié)同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將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擴(kuò)展至環(huán)境領(lǐng)域乃至整個(gè)社會(huì)變遷,其基本原則是制度框架中一切都是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然而這樣籠統(tǒng)的陳述卻很難應(yīng)用于實(shí)際”[3]60。
然而,在分析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問題時(shí)納入制度因素曾經(jīng)是環(huán)境研究領(lǐng)域內(nèi)的流行做法。例如20世紀(jì)中期,德國(guó)和日本的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界在分析環(huán)境問題時(shí)就從來沒有脫離對(duì)制度因素的考慮。日本環(huán)境學(xué)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宮本憲一,就十分注重不同的經(jīng)濟(jì)制度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其著作《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與其說是一部教科書,還不如說是一本關(guān)于不同制度和發(fā)展水平的國(guó)家之間的環(huán)境糾葛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和經(jīng)濟(jì)史教材[6]。當(dāng)時(shí)類似的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說更多地被稱做“公害經(jīng)濟(jì)學(xué)”,一個(gè)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強(qiáng)調(diào)發(fā)達(dá)國(guó)家對(duì)欠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污染物等公害輸出,以及新興國(guó)家的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經(jīng)濟(jì)模式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但是時(shí)至今日,這種分析環(huán)境問題的制度傳統(tǒng)卻逐漸被主流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所忽視。在當(dāng)代西方生態(tài)環(huán)境研究領(lǐng)域,像約翰·貝拉米·福斯特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生態(tài)學(xué)者只能被算做是環(huán)境政治學(xué)者,雖然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在此制度下的主流經(jīng)濟(jì)學(xué)如何導(dǎo)致了嚴(yán)重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危機(jī)[7]。
這種現(xiàn)象是令人深思的,對(duì)制度因素的忽視使得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作繭自縛”,嚴(yán)重影響了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發(fā)展為一門系統(tǒng)性的分析框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取得較快發(fā)展的那些領(lǐng)域恰恰是納入了對(duì)制度及其演化維度的考慮。如上文所述的對(duì)狩獵—采集型社會(huì)的研究,目前已經(jīng)成為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甚至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的熱點(diǎn)。鑒于此,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應(yīng)當(dāng)重視對(duì)制度及其演化性的關(guān)注,這將催生一門新的研究領(lǐng)域——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
三、淺析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內(nèi)涵特征
目前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演化思想已研究頗多。如Jeroen C.J.M.van den Bergh(2007)和Giorgos Kallis & Richard B.Norgaard(2010)較為詳細(xì)地介紹了環(huán)境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演化思想,后者甚至提出要開創(chuàng)名為“協(xié)同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新領(lǐng)域;在國(guó)內(nèi),楊虎濤(2010)[8]也較早對(duì)這一問題進(jìn)行了探討。但是,“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作為一個(gè)新的概念和學(xué)說體系,尚未引起學(xué)術(shù)界的足夠重視。只有楊虎濤(2011)[9]明確對(duì)“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相關(guān)范疇進(jìn)行了概述。那么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究竟有哪些內(nèi)涵特征呢?這就像它的名字那樣具有“演化的”不確定性,但我們還是可以部分地概括其某些基本特征和主張。
1.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哲學(xué)觀和方法論特征
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是演化性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在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研究領(lǐng)域中的全面應(yīng)用,在某種程度上是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與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結(jié)合。因此,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除了具有當(dāng)代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超越新古典傳統(tǒng)的哲學(xué)優(yōu)勢(shì)之外,還應(yīng)體現(xiàn)出自身獨(dú)特的哲學(xué)特質(zhì)。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不僅應(yīng)當(dāng)堅(jiān)持整體主義的哲學(xué)傳統(tǒng),摒棄亞里士多德哲學(xué)的原子論和牛頓哲學(xué)的機(jī)械觀,而且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傳統(tǒng)的功利主義哲學(xué)基礎(chǔ),也將被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所排斥。由于功利主義注重對(duì)苦樂結(jié)果的比較,而一般不考慮實(shí)現(xiàn)苦樂的動(dòng)機(jī)與手段,因而自主流經(jīng)濟(jì)學(xué)確立功利主義哲學(xué)基礎(chǔ)之后,物質(zhì)財(cái)富的增長(zhǎng)就成為衡量經(jīng)濟(jì)成功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這是與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所倡導(dǎo)的生態(tài)理念根本相悖的。排斥功利主義,就意味著摒棄將物質(zhì)財(cái)富的無限增長(zhǎng)作為目標(biāo)的目的一元論,并重視人的動(dòng)機(jī)、手段與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過程。這必然要求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在整體框架上做根本性變革,納入對(duì)“生態(tài)行為動(dòng)機(jī)”等制度因素及其實(shí)現(xiàn)過程的考察,并顯著改進(jìn)傳統(tǒng)的制度生態(tài)理論和協(xié)同演化理論在解決實(shí)際問題上的缺陷。
由于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所持的哲學(xué)觀與主流經(jīng)濟(jì)學(xué)存在本質(zhì)不同,因此在方法論上它反對(duì)主流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數(shù)學(xué)形式主義,并確立了定性分析對(duì)定量分析的指導(dǎo)性地位。鑒于此,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將主要采取歷史的、比較的、回溯的和歸納的研究方法,并將歷史經(jīng)驗(yàn)與定量分析有機(jī)結(jié)合。這將使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與任何“數(shù)學(xué)形式化”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理論區(qū)分開來,也為未來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發(fā)展奠定了思想基礎(chǔ)。
2.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自然科學(xué)基礎(chǔ)及其缺陷
在自然科學(xué)上,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將主要借鑒進(jìn)化生物學(xué)、熱力學(xué)和系統(tǒng)動(dòng)力學(xué)的思想精髓。因?yàn)?(1)進(jìn)化論思想本質(zhì)上是一種動(dòng)態(tài)演化的方法論體系,因而具有普遍的適用性,這是道金斯的“普遍達(dá)爾文主義”能夠應(yīng)用于解釋社會(huì)演化的原因所在;(2)熱力學(xué)中的“熵”定律和系統(tǒng)復(fù)雜性增加的不可逆性為事物發(fā)展和演化的方向性提供了佐證;(3)系統(tǒng)動(dòng)力學(xué)為事物基于系統(tǒng)行為的發(fā)展動(dòng)態(tài)與內(nèi)在機(jī)制間的依賴關(guān)系的結(jié)構(gòu)、聯(lián)系和演化提供了定量和數(shù)理分析框架。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將固守于熱力學(xué)和生物學(xué)的隱喻和類比,原因有兩點(diǎn):(1)理論適用性問題。就進(jìn)化論而言,在經(jīng)濟(jì)學(xué)中對(duì)其性質(zhì)的不同認(rèn)識(shí)就曾導(dǎo)致了“演化”概念的濫用——彼此對(duì)立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說都用它為自己的理論辯護(hù)。如當(dāng)許多反對(duì)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承認(rèn)“新達(dá)爾文主義”的正統(tǒng)性之時(shí),哈利勒卻令人信服地論證了“新達(dá)爾文主義”就是生物學(xué)中的新古典主義。熱力學(xué)的適用性同樣存在問題,如Peter A.Corning(2001)就認(rèn)為,“熵”理論對(duì)多層次、多維度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只有部分適用性[10]。(2)理論本身的問題。最近遺傳生物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的突破進(jìn)展——“表觀遺傳學(xué)”的研究表明,外部環(huán)境可以通過一系列生化機(jī)制(如DNA甲基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環(huán)境中個(gè)體的DNA性狀,從而使本代個(gè)體將外部環(huán)境影響遺傳給下一代。這表明即使在生物進(jìn)化層面,拉馬克主義也很可能是成立的,“生物進(jìn)化是達(dá)爾文式的,社會(huì)演化是拉馬克式的”二分法將失去意義。而宇宙中最可靠的基本物理定律——“熵”定律,最近業(yè)已受到理論和實(shí)驗(yàn)的雙重挑戰(zhàn)。如G.M.Wang 等(2002)就通過實(shí)驗(yàn)證明,在一定條件下孤立系統(tǒng)內(nèi)部的短時(shí)期、小規(guī)模的自發(fā)性熵減反應(yīng)是可以發(fā)生的。雖然該結(jié)論還無法對(duì)熱力學(xué)定律在宏觀尺度上的應(yīng)用產(chǎn)生任何影響,但這必然會(huì)對(duì)將其作為“永恒真理”的世界觀基礎(chǔ)的許多學(xué)科產(chǎn)生重大的思想沖擊,當(dāng)然包括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和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
因此,我們拒絕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過分使用生物學(xué)和熱力學(xué)的隱喻和類比。生物學(xué)和熱力學(xué)的新思維對(duì)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具有重要的啟發(fā)價(jià)值,但是當(dāng)其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需要擺脫這些理論、隱喻和類比的束縛的時(shí)候,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者們就更應(yīng)當(dāng)勇于摒棄它們并尋找新的支持。
3.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科基礎(chǔ)
在社會(huì)科學(xué)基礎(chǔ)上,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將主要以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為基礎(chǔ),并從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制度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協(xié)同演化理論甚至新古典框架的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分支等學(xué)科中汲取精華。
由于演化思想在理論構(gòu)架上具有先天優(yōu)勢(shì),已經(jīng)有些學(xué)者提出了在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框架下對(duì)各種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理論進(jìn)行重構(gòu),如Jeroen C.J.M.van den Bergh(2007)就明確了演化的觀念和方法在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中運(yùn)用的可能性。可以說,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正是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在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研究領(lǐng)域和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運(yùn)用,它注重新奇、選擇和路徑依賴等演化概念,并將廣義的制度因素或其中的某些方面納入分析框架之中。
應(yīng)當(dāng)注意到,制度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協(xié)同演化理論同樣將制度因素納入其分析框架,而后者更強(qiáng)調(diào)對(duì)演化屬性的關(guān)注,如Norgaard(1994)已將協(xié)同演化理論成功地應(yīng)用于處理害蟲、殺蟲劑和美國(guó)環(huán)境政策間的協(xié)同演化問題。那么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與同樣納入了制度因素并注重演化分析的協(xié)同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又有什么區(qū)別呢?正如上文彼得·巴特姆斯批評(píng)協(xié)同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時(shí)所指出的,協(xié)同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過分偏重于對(duì)演化機(jī)制的抽象解釋,因而存在著實(shí)際應(yīng)用層面上的困難;而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整體性視角反而更有利于對(duì)現(xiàn)實(shí)事物的普遍聯(lián)系和相互作用進(jìn)行解構(gòu)和分析。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正是將二者在不同研究維度上的優(yōu)點(diǎn)進(jìn)行了有機(jī)結(jié)合,既不失演化性在不同情境下對(duì)事物發(fā)展動(dòng)因的解釋能力,又兼顧了整體性在研究現(xiàn)實(shí)問題上的優(yōu)勢(shì),這正是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系統(tǒng)性內(nèi)核的本性使然。
4.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核心概念和框架特征
(1)“新奇”是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核心概念,創(chuàng)新是其演化的動(dòng)力。“新奇”是演化的核心范疇,是劃分演化與非演化理論的基本標(biāo)準(zhǔn);而“新奇的創(chuàng)生”即創(chuàng)新,是永無休止的經(jīng)濟(jì)變化的原因所在。魏特認(rèn)為,新奇在不同學(xué)科中具有不同的含義,如在生物學(xué)中,新奇涉及群體基因庫(kù)中的隨機(jī)突變和選擇性復(fù)制;而在經(jīng)濟(jì)學(xué)中,新奇就是人類新的行動(dòng)可能性的發(fā)現(xiàn)。如果新的行動(dòng)可能性被采納,那么這種行動(dòng)就被稱為創(chuàng)新[11]。至于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新奇及其創(chuàng)生概念不僅包括傳統(tǒng)意義上的那些影響和解決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的新技術(shù)和新發(fā)明的創(chuàng)造(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也包括新的技術(shù)—經(jīng)濟(jì)范式之于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時(shí)產(chǎn)生的新可能性(路徑創(chuàng)新);更寬泛和更重要的“新奇創(chuàng)生”包括,新的生態(tài)思想和環(huán)境倫理觀念的誕生,基于新的生態(tài)理念下的新的個(gè)人和群體行為模式,以及在這些新觀念和行為模式下產(chǎn)生的一系列新制度、新慣例和新范式(理念創(chuàng)新)。
(2)研究框架的系統(tǒng)性和包容性是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框架特征。一個(gè)系統(tǒng)性的研究框架必須兼具整體性和演化性,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演化的發(fā)生必須有其賴以依存的系統(tǒng)本體,而系統(tǒng)整體各部分之間的有機(jī)聯(lián)系則是演化進(jìn)程的結(jié)果使然。二者的區(qū)別也很明顯,整體性反映了事物之間的普遍聯(lián)系,而演化性則強(qiáng)調(diào)事物的發(fā)展變化。由于分別克服了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協(xié)同演化理論在演化性和整體性上的不足,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因而是一種真正的系統(tǒng)性研究框架,既兼顧了整體性在分析事物之間的普遍聯(lián)系和互動(dòng)機(jī)制上的優(yōu)勢(shì),又具備對(duì)事物發(fā)展變化動(dòng)因的解釋能力。
鑒于此,筆者認(rèn)為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實(shí)際上是一種更高層級(jí)的學(xué)科,許多現(xiàn)有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理論和流派,如生態(tài)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史、生態(tài)哲學(xué)與環(huán)境倫理、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制度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協(xié)同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當(dāng)然也包括傳統(tǒng)的資源與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實(shí)際上都可以算做是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在不同情境下的特例。一如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有可能對(duì)現(xiàn)有的許多經(jīng)濟(jì)學(xué)流派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綜合一樣,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包容性,也將允許其對(duì)以上學(xué)科中的精華思想和理論進(jìn)行整合和重構(gòu),這將帶來理論上的重大創(chuàng)新。
四、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研究領(lǐng)域、實(shí)踐優(yōu)勢(shì)及其對(duì)中國(guó)的重要意義
正如本文所論證的,當(dāng)代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對(duì)制度因素及其演化機(jī)制的考慮,這實(shí)際上制約了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因地制宜”地發(fā)展出一系列政策工具。制度缺位導(dǎo)致了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在實(shí)踐層面上的乏善可陳,這正是其政策建議不能在世界范圍內(nèi)被廣泛接納的主要癥結(jié)所在。尤其對(duì)于那些正在全力實(shí)現(xiàn)工業(yè)化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和正在貧困線上掙扎的欠發(fā)達(dá)國(guó)家而言,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一些政策主張(如限制物質(zhì)財(cái)富的增長(zhǎng)、縮減經(jīng)濟(jì)規(guī)模、關(guān)注公平和正義等)是備受質(zhì)疑和詰責(zé)的。最近,作為最大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和最強(qiáng)的發(fā)達(dá)國(guó)家,中國(guó)和美國(guó)都暫停了綠色GDP 核算項(xiàng)目。這從一個(gè)側(cè)面反映出,即使對(duì)于制度和發(fā)展水平迥異的國(guó)家而言,在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中披露環(huán)境問題的負(fù)面影響都是不受歡迎的。
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將有希望打開這種尷尬局面。由于對(duì)“制度因素及其演化”給予了充分的重視,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不僅更加有利于當(dāng)代生態(tài)經(jīng)濟(jì)思想和理論在不同制度背景的國(guó)家之間進(jìn)行傳播,而且將在實(shí)踐層面顯著改善當(dāng)代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與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趨同狀況。另外,由于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采取了歷史的、回溯的和比較的研究方法,因而應(yīng)當(dāng)具有運(yùn)用歷史經(jīng)驗(yàn)對(duì)事物的現(xiàn)狀和發(fā)展進(jìn)行解釋和預(yù)測(cè)的理論優(yōu)勢(shì),這使其能夠?qū)ι鷳B(tài)—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系統(tǒng)的發(fā)展趨勢(shì)作出更為科學(xué)的判斷。可以預(yù)見,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研究領(lǐng)域?qū)⒅饕杏谝韵聨讉€(gè)方面:(1)生態(tài)系統(tǒng)在人類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不同發(fā)展階段上的承載能力和可持續(xù)性;(2)生態(tài)環(huán)境變化、人類生態(tài)觀念與個(gè)體行為模式之間的演化和互動(dòng)機(jī)制;(3)產(chǎn)業(yè)、城市、區(qū)域三大層面上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的演化,如怎樣從演化視角理解生態(tài)—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空間聚集性和擴(kuò)散效果;(4)不同維度下(產(chǎn)業(yè)、城市、區(qū)域和國(guó)家)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可持續(xù)發(fā)展規(guī)劃;(5)跨國(guó)的和全球性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及其政策協(xié)調(diào);(6)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系統(tǒng)的協(xié)同演化機(jī)制及其未來發(fā)展趨勢(shì);(7)新技術(shù)—經(jīng)濟(jì)范式與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同時(shí),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將在許多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熱點(diǎn)問題上展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實(shí)踐優(yōu)勢(shì),如野生動(dòng)植物資源的保護(hù)和利用、全球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南北國(guó)家之間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義務(wù)和政策協(xié)調(diào)、不同制度背景和經(jīng)濟(jì)狀況國(guó)家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計(jì)劃,以及制度類別對(duì)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理論適應(yīng)性的挑戰(zhàn)等[12]。當(dāng)然,所有這些研究主題在剔除了制度因素及其演化機(jī)制的情況下是很難被理解和解決的。
對(duì)于中國(guó)而言,人均能源資源的嚴(yán)重不足長(zhǎng)期阻礙了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內(nèi)生性發(fā)展,這迫使中國(guó)采取一種外向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這種模式在利用外部資源上本應(yīng)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shì)(如資源匱乏的日本就很好地利用了外部資源),但是在中國(guó)的翻版卻完全變質(zhì)。長(zhǎng)期以來,為了充分利用中國(guó)大量的廉價(jià)勞動(dòng)力,確保充當(dāng)“世界工廠”的比較優(yōu)勢(shì),中國(guó)寶貴的自然資源和能源價(jià)值被長(zhǎng)期“連帶”地人為壓低,并且環(huán)境破壞和污染成本也被基本忽視。這本質(zhì)上是一種對(duì)外國(guó)企業(yè)和消費(fèi)者的“廉價(jià)資源補(bǔ)貼”,卻為我們自身帶來了嚴(yán)重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矛盾。鑒于此,如何合理地開發(fā)和利用中國(guó)稀缺的自然資源和能源,在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同時(shí)提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縮小貧富差距,并促進(jìn)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和諧發(fā)展,將是中國(guó)未來發(fā)展面臨的嚴(yán)峻挑戰(zhàn)。
目前正在發(fā)生一場(chǎng)以可再生能源為基礎(chǔ)的新技術(shù)—經(jīng)濟(jì)范式的革命,它所引起的生態(tài)創(chuàng)新和制度因素的變革,能否在中國(guó)產(chǎn)生出有利于創(chuàng)新的某些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新模式,而使我們有能力迎接未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嚴(yán)峻挑戰(zhàn)呢?這是一個(gè)錯(cuò)綜復(fù)雜的問題,但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至少能夠?yàn)橹袊?guó)迎接這一挑戰(zhàn)提供可行的理論支持與實(shí)踐引導(dǎo)。許多當(dāng)前在中國(guó)特有的制度環(huán)境下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階段中產(chǎn)生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都能夠在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嶄新框架下得到重新闡釋和解決;而對(duì)于未來基于可再生資源范式革命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而言,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就有可能通過對(duì)不同國(guó)家的制度環(huán)境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階段的歷史經(jīng)驗(yàn)考察和比較分析,找到為中國(guó)“量身定做”的發(fā)展戰(zhàn)略,這是以往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研究的單一視角所難以做到的。當(dāng)前的兩大現(xiàn)實(shí)問題就是如何運(yùn)用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對(duì)中國(guó)稀土等稀有金屬資源的開發(fā)利用和新能源產(chǎn)業(yè)(如光伏和風(fēng)力發(fā)電等)的困局進(jìn)行分析,中國(guó)的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者應(yīng)當(dāng)致力于構(gòu)建和發(fā)展這樣一種演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
[1][美]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原理與應(yīng)用[M].徐中民,譯.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7:10.
[2]趙金龍,董謙,王軍.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必須明確的兩個(gè)問題[J].經(jīng)濟(jì)縱橫,2010,(3).
[3][德]彼得·巴特姆斯.數(shù)量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如何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的可持續(xù)發(fā)展[M].齊建國(guó),等,譯.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0:25.
[4]賈根良.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與達(dá)爾文主義文獻(xiàn)述評(píng)[J].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評(píng)論,2004,(2).
[5]楊虎濤.兩種不同的生態(tài)觀——馬克思生態(tài)經(jīng)濟(jì)思想與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穩(wěn)態(tài)經(jīng)濟(jì)理論比較[J].武漢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6,(6).
[6][日]宮本憲一.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學(xué)[M].樸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
[7][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tài)危機(jī)與資本主義[M].耿建新,宋興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8]楊虎濤.交匯與分野——馬克思與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對(duì)話[M].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2010.
[9]楊虎濤.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講義——方法論與思想史[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11.
[10]Peter A.Corning.Thermoeconomics:Beyond the Second Law[J].Journal of Bioeconomics,2002,(1):57-88.
[11]賈根良.理解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J].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04,(2).
[12]賈根良.演化經(jīng)濟(jì)學(xué):現(xiàn)代流派與創(chuàng)造性綜合[J].學(xué)術(shù)月刊,2002,(12).
- 黑龍江社會(huì)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80后”知識(shí)精英的社會(huì)政治態(tài)度——基于對(duì)6所985高校在校生和畢業(yè)生的對(duì)比分析
- 符號(hào)光環(huán)的追隨與迷失——“80后”群體的奢侈品消費(fèi)與時(shí)尚文化研究
- “80后”的職業(yè)群體差異
- 東北地區(qū)加快落實(shí)《中俄合作規(guī)劃綱要》對(duì)策研究
- 儒學(xué)與生態(tài)文明——“國(guó)際儒學(xué)論壇·2012”學(xué)術(shù)會(huì)議綜述
- “80后”社會(huì)群體特征及變遷(專題討論)“80后”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及其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