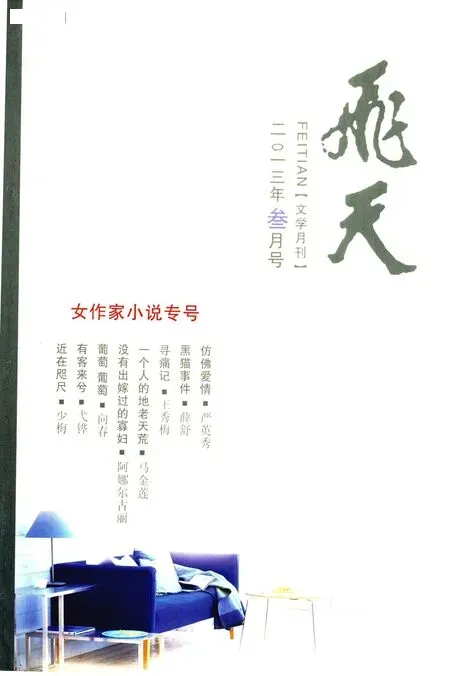葡萄 葡萄
向 春

向春,小說作家。2000年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在《十月》、《中國作家》等刊發(fā)表中短篇小說多篇,并被多種選刊轉(zhuǎn)載。著有長篇小說《河套平原》、《妖嬈》等五部。獲甘肅省政府敦煌文藝獎、黃河文學(xué)獎、《作品》“金小說”獎。魯迅文學(xué)院第二屆高級研討班學(xué)員。中國作協(xié)會員。現(xiàn)居蘭州。
它是葡萄
葡萄的手指
我被它弄得很疼
一直都在默默尖叫
——丁燕《葡萄一夢》
她不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更不驚艷。她的泳衣墨守成規(guī),一抹銀藍(lán)或一道墨紫。她走在沙灘上,像中國書法里的一撇或者一捺。她看兩旁的人,便發(fā)現(xiàn)了人們驚悚的表情——他們微微張開的嘴里正好夠放一枚葡萄。女人笑出了酒窩。她的乳名叫葡萄,所以她經(jīng)常想起葡萄。這是一個正午,太陽像一枚銅錢擱在她的頭頂上,一個光屁股孩子指著她的后背說,快看啊,快看啊,她的身上有個影子,她的身上有個影子!
她的身上有個影子。她自己看不見。像自己的骨骼看不見自己的鮮血。影子是打不碎的。比如十二歲的那一年,她經(jīng)常夢見雞蛋。她睡覺的時候非常警覺,總擔(dān)心什么東西被打爛,總擔(dān)心什么東西覆水難收。當(dāng)夜色傾斜的時候,她就像一個潑婦跳起來,牙簽似地喊,起床!起床后照鏡子,發(fā)現(xiàn)了自己和一個影子重疊在一起。她家的鄰居說,你家這閨女像誰呀,怎么這么黑?當(dāng)時她正在雙臂交叉脫一件緊繃在身上的毛線衣,她的身子長大了,毛線衣小了,卡在肩膀上拽不下來。聽到這句話,為了掩飾自己的尷尬,像被誰出其不意地搔了一下,她突然嘎嘎大笑,笑著笑著就號啕起來。她想念著影子的黑,夜色的黑,想的時間長了,她就心想事成了。
女人的職業(yè)是排列文字楔入標(biāo)點符號。她酷愛藍(lán)天一樣的文字和雨水一樣的標(biāo)點。當(dāng)男人們艷羨古代帝王后宮的三千佳麗時,她就說: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有四千呢!她指的是漢字。
白天她把文字做成文章像把米粒做成米飯。晚上她睡在一本字典上,今天在二十三頁,明天在九十八頁。她有一本字典,舊了,那是她年復(fù)一年的麥田。
她經(jīng)常想送她字典的那個人,那個人的名字叫老石頭。
老石頭姓石,是小女人五年級時的語文老師。老石頭從大西北來,中專畢業(yè)后分到小女人出生的海濱城市,做了小女人的老師。文革開始了,學(xué)生們不上課了,老師們都到操場上去扣土坯,實在沒什么可干的就翻院墻下面的沙子。一天老石頭正在翻沙子,一個小石子硌了鐵鍬發(fā)出了尖銳的聲音,這時正好一個工宣隊站在老石頭身后。老石頭撿起了這個小石子放在自己口袋里,繼續(xù)翻沙子。翻完沙子回到教室,只有小女人一個學(xué)生坐在課桌前。這時那個工宣隊走進(jìn)教室來,逼著老石頭把他口袋里的寶貝東西交出來。老石頭說沒有什么寶貝東西。對方說沒有什么寶貝東西你為什么把它收到口袋里?雙方僵持了好長時間,老石頭無奈把那個小石頭掏出來,展在手心上。那是一個心形的鵝卵石,圓潤的,上面仿佛有汗。工宣隊悻悻地走了。對對方小小的捉弄讓老石頭和小女人開心地大笑,笑完了,他們面對面地坐下講課,仿佛一對老朋友。他手把手地教小女人寫毛筆字,小女人手累了的時候就晃著他的大手說,歇一會兒歇一會兒,老石頭。他的手是那么大,她的手放在他的手心里,像小鳥放在鳥窩里。小女人的心啾啾地鳴叫起來。她抬起頭來。老石頭盯著她的眼睛看,盯著看盯著看,直到盯出水來。老石頭說:葡萄,你快快長大,快快長大啊!這時小女人的眼里就綻出琥珀色的淚花。
那一個春天,他們在不停地種蓖麻。在田埂上,向日葵下,或者就在舊蓖麻旁。老石頭挖一個坑,小女人點一顆籽。春天風(fēng)大,天空干得像一只火柴盒。隔一陣,老石頭就嗑開一只蓖麻籽,在手心里捻碎,往小女人的臉上抹。小女人趁機(jī)就像小狗伸出舌頭舔他的手掌心,那里有細(xì)細(xì)的紋路,一片腥咸的樹葉。那一年的蓖麻長得真旺啊,葉子稠密得插不進(jìn)去眼光。累了,歇一會吧。老石頭坐在地堰上,小女人坐在他的膝頭上。天是那么藍(lán),盯著一塊白云看,人就飛起來,風(fēng)像鳥長出了翅膀。老石頭的腿酸了,小女人站起來,發(fā)現(xiàn)老石頭的膝蓋上有殷紅的血。小女人驚悚地冒出了眼淚,抱著老石頭的膝蓋說,你的腿怎么破了,是我把你割破的嗎?小女人摘下脖子上的紗巾,包扎那只膝蓋,心疼得嚶嚶地哭。
老石頭的膝頭迎接了她的初潮。
老石頭說,葡萄,以后不要坐在濕地上。
葡萄說,我知道,坐在濕地上蟲子就會鉆進(jìn)來。
一個晚上,老石頭送小女人回家。分手時,是在一棵老榆樹下,月亮像一只黃燈籠掛在樹梢上。小女人撲進(jìn)老石頭懷里說,抱抱葡萄,抱抱葡萄啊!
可是第二天正午,所有的人都看見,在粗壯的老榆樹皮上,有著老石頭抱緊小女人的影子。
后來老榆樹長,老石頭和小女人也長。
他因為送她回家而認(rèn)識了她的母親。母親是個熱心人,看著這么英俊的一個小伙子就說,有沒有對象啊?嬸子給你介紹一個。每到星期天,他們騎著自行車到鄰近的地方去看對象。母親給他介紹過話務(wù)員播音員小學(xué)老師。黃昏的時候她藏在他們回來必經(jīng)的一棵老楊樹后面,她抱著那棵老楊樹哭,后來那棵老楊樹被她哭死了。
他教她游泳,教她戰(zhàn)勝最可怕的東西。他們站在海邊,他讓她盯著海水看,又給他講了一個陳舊的故事,一個人落入水中拼命掙扎呼救,等別人把他救起后,才發(fā)現(xiàn)水只到臍部。水裹挾了身體后,他說,放松四肢,平衡身心,均勻呼吸,你是滄海一粟,漂起來飛起來——他馱著她向大海走,向大海的深處游。她伏在他的背上,時而在水中時而在水上。正當(dāng)她在藍(lán)天和大海間飛翔的時候,他像一條魚從她身下溜走。她像一條落水狗一樣掙扎,充滿了死亡來臨時的恐懼。她嗆一口水升出海面,他在離她一米遠(yuǎn)的地方,只要伸一下胳膊就能抓住她。她再嗆一口水升出海面,他仍然在離她一米遠(yuǎn)的地方無動于衷。她筋疲力盡,絕望,放棄,她停止了掙扎——就這樣她漂起來,陽光刺得她睜不開眼,他的氣息纏住了她,她眼淚洶涌,頭發(fā)像海藻一樣呻吟。
最后一次見老石頭,老石頭送她一本字典,把“葡萄”兩個字精心地圈起來。他說,葡萄,好好學(xué)漢字。年僅十三歲的小女人不知道老石頭一去會有多遠(yuǎn),因為她不知道這個世界有多大,路有多遠(yuǎn),人心有多深。她撒嬌地努著嘴說,學(xué)多少才夠啊?老石頭說,四千個吧。
有太陽的時候,小女人就坐在老石頭翻沙子的那堵墻邊抱著字典看。以后的二十年,女人在數(shù)家珍似地數(shù)漢字時,發(fā)現(xiàn)字典里除了葡萄被圈住外,“吐魯番”也用紅線勾了出來。小女人想老石頭是回到家鄉(xiāng)吐魯番的葡萄溝里去了。
她再沒有看到老石頭,在小女人長成女人的過程中,叫老石頭的那個人跟她成長在了一起。像那棵雌雄同體的樹,結(jié)果以后,一個是果核一個是果肉。
再沒有人叫過她葡萄。
和所有的女人一樣,她在青春紅火圓實的時候似乎愛上了一個男人。
這個男人愛她,瘋狂地愛她。他說我的女人啊我的女人啊,我不知道怎么愛你啊我不知道怎么愛你啊!仿佛愛是一只刺猬。一個男人愛上一個女人就算愛上了冰,熱了就會化,化了就會走。男人撫摸她的時候像撫摸一刃刀鋒,近了疼,所以他搓著手頓著足搖著頭發(fā)著抖,像膀胱里的一泡尿憋過了頭。
他給女人買水果,他吃果皮女人吃果肉。他給她買數(shù)不清的內(nèi)衣,說內(nèi)衣才是穿給他看的,才是私密的。女人經(jīng)期時,男人切菜就會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他說,要流血一起流血,最好血要流在一起。他們像一對生死與共的戰(zhàn)士,面對著唯一的敵人,命懸一線,惺惺相惜。更仗義的是,他非常君子,他給她買了房子后,她睡床,他睡沙發(fā)。他舍不得啊,像對待一只桃子,他摩挲著桃子,舍不得剝開她,一味地癢癢著。男人把自己的臉伏在女人的肚臍眼上說:我想進(jìn)去,我想進(jìn)去,這樣你就不會離開我了。仿佛他是一個無助的想返回子宮的嬰兒。
傍晚他們坐在海邊,看一望無際的海,張望他們深不見底的未來。漲潮時,他們被一次次卷進(jìn)大海,直到月亮升起來,男人永遠(yuǎn)不撒手地抱著女人如海水永遠(yuǎn)不放棄魚。
終于到了新婚之夜,男人言之鑿鑿地說,我要吃了你,你是月亮我不嫌涼,你是太陽我不嫌燙。世界上的新婚之夜通常都是一場舊社會,人吃人的。他說,我吃了你之后,你就是我的了,就是我了。想你的時候我就從我身子里把你掏出來,想咋愛就咋愛。
這是一個月夜,也許是上弦也許是下弦。兩個人貼得很近,男人幾乎是女人的一張皮。男人踅摸著,要像一只蟲子進(jìn)入果實內(nèi)部。這時電話鈴聲響了,門鈴響了,表鈴響了,大街上的汽笛響了,從四面八方傳來一個聲音,甚至從女人的身體里發(fā)出聲音,女人的身體像一把長笛——這個聲音非常急促地叫著葡萄葡萄——這個聲音是那么遙遠(yuǎn),那么清晰,他們兩個人都聽得很真切。女人瞇縫起眼睛回憶著這個熟悉而遙迢的聲音,說,誰在喚我的乳名呢?可是身邊人早已跳了起來,他像老鷹抓小雞一樣把女人提起來又摔下去:是什么人這么叫你的乳名呢?是什么人在這個時候仍然叫你的乳名呢?男人的手向著女人的脖子掐過來。像握一只葡萄酒瓶,他對著赤裸裸的女人咬牙切齒地說:葡萄葡萄,我要把你裝進(jìn)瓶子里!他反復(fù)說著這句話,仿佛念著一道魔咒。
女人喃喃地說,那是過去。男人又把“葡萄酒瓶”倒過來拎著,絕望地說,過去就是未來!
女人愣怔了片刻,這是一個被哲學(xué)的過程。一株過去的樹木變成了一副未來的家具。
男人痛心疾首,一塊新鮮的豆腐,舍不得吃舍不得吃,最后這塊豆腐就沒心沒肺地餿了。
愛終究是一個很空洞的詞,或者愛就是一個窟窿,是一個不治之癥。那個表面披肝瀝膽的男人,立刻病來如山倒。
女人無話可說,她一層層地穿著衣服,她穿得很厚很厚。但是一輪滿月終于瘦下去了,對于那個男人來講一直瘦到了無。可是男人上來扒她的衣服,說,這些都是我的,人可以走我的東西不能走!他的意思是,你可以帶走我的心,但不能帶走我的衣服。女人劈里啪啦脫光了衣服,白嘩嘩地走出去。太陽懸掛在藍(lán)天上,大街上,人們看到,一個影子裹挾著一個女人,絕塵而去。
后來女人只能獨處。她一個人去飯店吃飯,服務(wù)員就放兩雙筷子,兩只酒杯。雨天,她不用遮傘也淋不著身子,雪天,她不穿棉衣也渾身溫暖。
晚上她經(jīng)營著她的文字,白天她習(xí)慣做白日夢。四十歲生日的這一天,她想喝一點酒。她從來是滴酒不沾的。但四十歲了她想喝一點酒。她倒了一玻璃杯的葡萄酒放在嘴邊,酒香撲面而來把她的鼻子變成了一個花朵。這是一股陽光曬裂葡萄的香味,紫色的汁液泛漫著泛漫著溢出來。女人周身烘熱,仿佛靠在童年的一堵旁邊是一堆沙子的土墻上曬著太陽,太陽的光芒像麥芒一樣刺得她渾身發(fā)癢,她想笑,想笑。她瞇上眼睛看到了自己一片酡紅,她被自己的美麗懾服了。她對著鏡子舉起酒杯,在自己的額頭上碰了一下說:干杯!陽光和酒進(jìn)入女人后,女人的身體酥潤起來,飄忽起來,她的雙臂葡萄藤一樣抱住自己的雙乳,她的雙唇柔媚地欲說還休地努起來,像正在吮吸一只葡萄——在一個非常遼闊的陽光地帶,天上有三個太陽。葡萄藤架起的綠色長龍蜿蜒起伏,一直伸展到太陽升起的遠(yuǎn)方。在遮天蔽日的綠色中點綴著一幢幢金黃色的蜂窩狀的房子。女人站在房子的中央,陽光篩進(jìn)來照在她的身體上,像一條剛被網(wǎng)住的帶著滿身鱗片的赤條條的魚。這時腳步聲響起了,自葡萄溝里響起了,在蜂房邊響起了,那聲音像一串清脆的木魚。但是一陣風(fēng)吹過后,腳步聲就散了,漸漸地消失了……
女人的夢斷流了,她從夢中干渴地出來。她睜開眼睛,站在鏡子前,發(fā)現(xiàn)她身上太陽曬成的網(wǎng)格狀依然在,黃褐相間。女人駭然。這個夢揮之不去,每天午后,女人受著它的引誘喝下一杯葡萄酒后,那個夢就會重復(fù)。但是腳步聲一直沒有走進(jìn)蜂房里,在蜂房門口就隱遁了。
女人憔悴了萎靡了,她整日蝸居在陽光準(zhǔn)時照進(jìn)來的斗室里,一只胳膊和另一只胳膊交叉起來抱緊自己的身體。夢醒之后天空就下起了太陽雨。密集的雨點像一窩葡萄敲打著玻璃窗,她隔著玻璃用手觸摸這些小精靈,她的十個手指頓時醉得東倒西歪。
終于有一天,女人收拾了行裝從斗室里走出來,她要一直向西去,向著有葡萄的地方去。一進(jìn)葡萄溝她就迷了路。馬路邊土房的墻上寫著白色的標(biāo)語,“計劃生育男人有責(zé)”,這是一個有男人有女人有葡萄的地方。其實也無所謂迷路不迷路,女人本來就不知道要走什么路。她像一條蛇百折千回地纏進(jìn)了葡萄藤里。
太陽西斜時,她的臉轉(zhuǎn)向西邊。
她驚呆了——她看到了夢中屢屢出現(xiàn)的蜂窩狀的房。
這是蜂房,是吐魯番人用來風(fēng)干葡萄的房子。蜂房的五面墻用土坯參差地拼砌成網(wǎng)狀,像蜂窩一樣錯落有致,這種結(jié)構(gòu)的房子最適合陽光和空氣的輪轉(zhuǎn),最容易把葡萄晾制成葡萄干兒,當(dāng)?shù)厝私凶鳌胺浞俊薄?/p>
女人穿梭在蜂房間像古埃及人穿梭在大小金字塔間。
終于在一間蜂房前站定了,她夢中的蜂房就是眼前的蜂房。它是土質(zhì)的,多少年的風(fēng)雨駁蝕使它古樸渾然。與其他蜂房不同的是,它的表面嵌著一顆顆小石子和碎陶片,在斜陽下五彩繽紛地璀璨著。
此時女人當(dāng)然想起了老石頭。向前走了七步,女人就走進(jìn)了這間蜂房。蜂房的葡萄架上只晾了一半的葡萄,沒曬到太陽的是紫色的,曬到太陽的是玫瑰色的。女人站在蜂房的中央,承接著穿過蜂墻的萬道陽光,她薄如蟬翼的衣裙里的皮膚又逐漸黃褐分明地網(wǎng)格狀起來。這時就有腳步聲響起,木魚般的聲音走近,就有一雙手托起女人的身體對女人耳語說:你是葡萄嗎?
女人發(fā)現(xiàn),首先是架上的葡萄因鼓脹而破裂,紫色或玫瑰色的汁液流淌著如檐下的春雨。其次看見自己身上重疊著一個溫暖飽滿的男人影子。
女人帶著這個影子離開吐魯番的時候,發(fā)現(xiàn)太陽是從東邊落下去的。一個類似于庫爾班的大叔告訴她,這間蜂房的主人是何年何月何日辭世的。女人一點都不覺得奇怪,那個日子正是她的新婚之夜。
重新回到生活了幾十年的海濱城市,女人對著大海說,葡萄回來了。她褪下了黑色的衣裙,穿上明媚的時裝,在灰色的都市里飄逸得如一束飛揚的蠶絲。四十歲的女人豐滿起來青春起來,最神奇的是,女人一笑,兩只酒窩里就溢出葡萄酒的香氣。
她遇到了朋友蔣萊。那一陣她在構(gòu)思一個聾子愛上瞎子的故事。聾子聽不到瞎子在說什么,瞎子看不見聾子在打手勢,他們靠一種叫“飛樂蒙”的氣息或信息相互吸引,以彼此觸摸為交流手段,愛情一觸即發(fā)。有一天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去一趟醫(yī)院,他們猜測對方,可能是想去醫(yī)院問問他們能不能有孩子。站在醫(yī)生面前,瞎子說他(她)想把角膜移植給聾子愛人,聾子愛人當(dāng)然沒聽見。聾子打手勢說他(她)想把角膜移植給瞎子愛人,瞎子愛人當(dāng)然看不見。最后醫(yī)生把他們的手放在一起,邊打手勢邊說,你們可以有一個健康聰明的孩子,回去試試吧,兩個腦袋總比一個腦袋好,三個腦袋總比兩個腦袋好。這樣她當(dāng)瞎子時,就讓蔣萊當(dāng)聾子,她在蔣萊身上摸來摸去,蔣萊怕癢,躲避。為了追趕,她頭上碰了核桃大的包。
蔣萊看上去是一個瘦弱的女人,她不愛男人,甚至鄙視。她老說男人傻,尤其是高個子的男人,說他們的心離大腦太遠(yuǎn)。她沒有真正地愛過一個男人,所以作為局外人對愛情看得比較清楚。她說愛只能求人格的平等,不能求分量和深度的相等。我愛你一斤你就應(yīng)該愛我八兩?我愛你一米你就應(yīng)該愛我三尺?付出愛后要回報,這叫什么愛!你愛別人別人就應(yīng)該愛你嗎?你對別人付出了別人就應(yīng)該愛你嗎?一個富人愛上了一個窮人,他對窮人說,我有錢你應(yīng)該愛我。窮人說你有錢是你自己的我為什么要愛你?富人說,我把我的錢分給你一半,你要愛我!窮人說,那我和你一樣有錢,我為什么要愛你?富人說,那我把我的錢都給你,你要愛我!窮人說,那我就成了富人你成了窮人,我為什么要愛你?
她們?nèi)ル娪霸嚎措娪啊_M(jìn)影院前蔣萊從街邊的小賣鋪里買了一瓶小二鍋頭,坐到座位上后強迫她喝掉一半,剩下的蔣萊一飲而盡。這是她們第二次看《泰坦尼克號》,她們要求對方不要睜開眼睛,在醉酒的狀態(tài)下聽音樂。再睜開眼睛時,電影院里空蕩蕩的,工作人員在旁邊拽她們的袖子。她們喜歡電影院,因這這里像黑夜,所有的人都是影子。影子這種東西,看上去總是醉著。
令人驚奇的是一次體檢。大夫摘下雪白的口罩說:你知道自己懷孕了嗎?女人聽到這聲音像是天外來音,但她也不覺得奇怪。接著大夫又說:你知道自己懷的是葡萄胎嗎?
葡萄,以后不要坐在濕地上。
我知道,坐在濕地上蟲子就會鉆進(jìn)來。
就這樣女人被推進(jìn)了手術(shù)室,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是:女人一直微笑著,她酒窩里的葡萄酒香味兒,首先把進(jìn)來麻醉女人的麻醉師醉倒了。大夫切開女人的身體后,更加濃郁的葡萄酒香味兒又醉倒了主治大夫。
從此女人就成了傳說中西域的香妃,她出入公共場所,就有不勝酒力的人頻頻醉倒。
終于有一天出事了。
一個晚上,一個出租車司機(jī)帶著一個客人開著桑塔納,這個司機(jī)很熱情,給客人講八卦。他說,前幾天的一個深夜,他拉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他沒敢正面看那個女人,因為他上夜班很長時間沒挨著女人了,他怕自己有邪念。他一本正經(jīng)地問,到哪兒?女人說,到殯儀館。到了殯儀館,女人給了他一百塊錢說不要找了,他接過錢說謝謝。第二天交班的時候,他數(shù)錢,發(fā)現(xiàn)里邊有一張一百塊錢的冥幣。客人說,唉呀真的嗎?司機(jī)笑著說,我就這么一說你就這么一聽,看你快睡著了,逗你玩的。走到一個窄路段,前面一男一女相擁著,怎么按喇叭都不讓路。可能是這一對情意綿綿的男女相擁的姿勢太美妙,觸動了司機(jī)心底的一些美好,好心的司機(jī)只能在他們的后面滑行著。這一天正好風(fēng)大,正好頂風(fēng),便有濃郁的葡萄酒的香氣一陣陣向桑塔納襲來,沒多久司機(jī)的臉色就潮紅起來。這樣不勝酒力的司機(jī)就無法控制地向這兩個幾乎絞在一起的男女撞去——受驚而醒的司機(jī)和顧客同時看見,在車撞上這一對人的剎那,男人把女人向旁邊推了一把。車上的兩個人同時認(rèn)為,女人沒事兒,那個男人可能完了。
他們下了車,在地上和車下找那個男人,可是都沒有。那個女人站在馬路旁笑吟吟地不說話。
他們忙問:那個男人呢?
女人說:哪里來的男人?
她不再理會這兩個唐突的男人,轉(zhuǎn)過身依然酒香四溢地向前走。隱入夜色時,那兩個男人看見,前面有一對男女相擁著絞在一起,像一根葡萄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