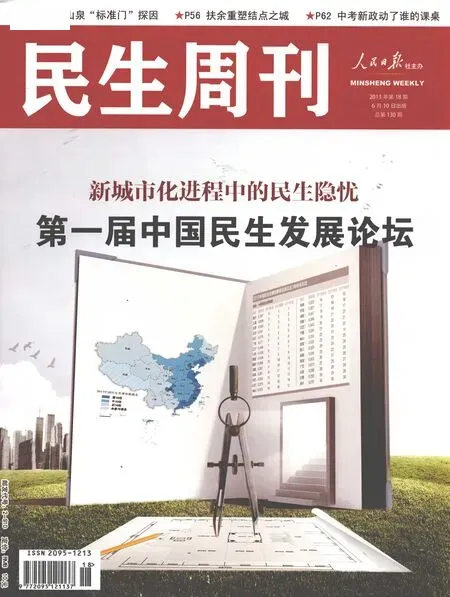彭真懷:用新城鎮(zhèn)化盤活經(jīng)濟(jì)全局
□ 本刊記者 潘陽(yáng)
□ 本刊記者 郭鵬
彭真懷:用新城鎮(zhèn)化盤活經(jīng)濟(jì)全局
□ 本刊記者 潘陽(yáng)

彭真懷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地方政府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
“新型城鎮(zhèn)化在拉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中具有托底作用,應(yīng)當(dāng)上升為國(guó)家戰(zhàn)略,所有的經(jīng)濟(jì)政策和制度設(shè)計(jì)都有必要指向這個(gè)落腳點(diǎn)。”
“郡縣治則天下安”。目前,全國(guó)94%的國(guó)土面積在縣級(jí),75%的人口在縣級(jí),整個(gè)鄉(xiāng)鎮(zhèn)政權(quán)是國(guó)家政權(quán)的管理末梢。在第一屆中國(guó)民生發(fā)展論壇上,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地方政府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彭真懷認(rèn)為,相應(yīng)的機(jī)構(gòu)改革必須加強(qiáng)力量,權(quán)利必須下沉。應(yīng)重視小城鎮(zhèn)的政策投入不足、工農(nóng)業(yè)發(fā)展本末倒置等城鎮(zhèn)化問題,用新型城鎮(zhèn)化盤活經(jīng)濟(jì)全局。
小城鎮(zhèn)政策投入不足
近10年來(lái),彭真懷一直從事小城鎮(zhèn)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體制等方面的調(diào)查研究。他指出,任何一個(gè)不帶偏見的人都會(huì)看到,小城鎮(zhèn)建設(shè)關(guān)聯(lián)度高、影響面大,在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lái)越突出,直接體現(xiàn)農(nóng)民生活和農(nóng)村文明的總體水平。
改革開放33年來(lái),我國(guó)建制鎮(zhèn)由2173個(gè)增加到19249個(gè),數(shù)量上增加了17076個(gè)。再加上1.8萬(wàn)多個(gè)鄉(xiāng)級(jí)鎮(zhèn),小城鎮(zhèn)的人口、地域和規(guī)模顯著增長(zhǎng),其經(jīng)濟(jì)總量提升、社會(huì)事業(yè)發(fā)展、綜合實(shí)力增強(qiáng),是名副其實(shí)的城鄉(xiāng)和工農(nóng)連接紐帶,是農(nóng)村社會(huì)公共品的提供基地和服務(wù)載體。
同時(shí),彭真懷也注意到,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按當(dāng)時(shí)的人口分配耕地,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這就造成了目前普遍存在的外嫁女問題,以及2.5億新生代農(nóng)民種田無(wú)地、上班無(wú)崗、低保無(wú)份,像候鳥一樣在城鄉(xiāng)之間遷徙流動(dòng)。
在他們身后,還站著8700萬(wàn)留守老人、兒童和婦女。這些新生代農(nóng)民本質(zhì)上就是流民,沒有什么發(fā)展空間。這是一個(gè)必須解決而且回避不了的經(jīng)濟(jì)壓力,是一個(gè)必須抓緊而不能拖延的政治任務(wù)。
在彭真懷看來(lái),新型城鎮(zhèn)化在拉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中具有托底作用,應(yīng)當(dāng)上升為國(guó)家戰(zhàn)略,所有的經(jīng)濟(jì)政策和制度設(shè)計(jì)都有必要指向這個(gè)落腳點(diǎn)。“縱觀歷史,農(nóng)民、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問題是歷朝歷代治亂成敗的首要因素。”
面對(duì)我國(guó)發(fā)展不平衡、不協(xié)調(diào)和不可持續(xù)的問題依然突出,經(jīng)濟(jì)下行風(fēng)險(xiǎn)越來(lái)越嚴(yán)峻的形勢(shì),新型城鎮(zhèn)化是目前唯一可以培育的空間因素。但讓彭真懷深感憂慮的是,在政策、資金和項(xiàng)目資源的使用上,中央政府的慣性思維是向直轄市和計(jì)劃單列市傾斜,省級(jí)政府的慣性思維是向省會(huì)城市和本省的次區(qū)域中心城市傾斜,對(duì)于小城鎮(zhèn)的政策設(shè)計(jì)相對(duì)認(rèn)識(shí)不足,重視程度不到位,經(jīng)常處在搖擺不定的狀態(tài)中。
他認(rèn)為,現(xiàn)在最需要做的,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jí)政府官員必須統(tǒng)一思想,凝聚共識(shí),改變“先城市、后農(nóng)村,先市民、后農(nóng)民,先工業(yè)、后農(nóng)業(yè)”的慣性思維,對(duì)的就堅(jiān)持,不對(duì)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lái)后抓緊研究解決。
用新型城鎮(zhèn)化盤活全局
彭真懷指出,新型城鎮(zhèn)化這場(chǎng)真正的改革將改變中國(guó)歷代統(tǒng)治者對(duì)農(nóng)民、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的態(tài)度,是中國(guó)幾千年沒有過(guò)的大變局,將改變我們五千年農(nóng)耕社會(huì)對(duì)農(nóng)民的剝奪、對(duì)農(nóng)村的侵害。“新型城鎮(zhèn)化要給國(guó)家一個(gè)未來(lái),讓農(nóng)民人生有出彩的機(jī)會(huì)。”
彭真懷認(rèn)為,新型城鎮(zhèn)化需要在兩個(gè)層面發(fā)力。第一個(gè)層面是,讓地級(jí)以上城市消腫,解決虛假城鎮(zhèn)化遺留的城鎮(zhèn)問題。第二個(gè)層面是,讓縣城和小城鎮(zhèn)建設(shè)釋放真正的改革紅利。“在這個(gè)方面進(jìn)行試點(diǎn),也是中央經(jīng)濟(jì)工作會(huì)議提出的趨利部分,可以帶動(dòng)整個(gè)國(guó)家成長(zhǎng)的空間。”
此外,彭真懷還建議用新型城鎮(zhèn)化盤活全局,提高農(nóng)民的收入,提升農(nóng)業(yè)效益;鼓勵(lì)資本下鄉(xiāng),改變農(nóng)業(yè)靠天吃飯的局面;對(duì)農(nóng)業(yè)進(jìn)行區(qū)域化布局、標(biāo)準(zhǔn)化生產(chǎn)和加工,從源頭上解決整個(gè)中華民族的食品安全問題。
彭真懷強(qiáng)調(diào):“中央財(cái)政在經(jīng)濟(jì)形勢(shì)不好的情況下,在地方拿不出很多錢支持城鎮(zhèn)化的時(shí)候,提出民營(yíng)企業(yè)撬動(dòng)社會(huì)資本進(jìn)行城鎮(zhèn)化建設(shè)。”
2009年,國(guó)家提出鼓勵(lì)中小企業(yè)投資的“國(guó)29條”,緊接著又在2010年提出了鼓勵(lì)民間資本的“新36條”。彭真懷指出,新型城鎮(zhèn)化讓中國(guó)的民營(yíng)企業(yè)經(jīng)營(yíng)者對(duì)自己的發(fā)展環(huán)境不再表示懷疑,不再把自己的子女教育放到國(guó)外去、把資產(chǎn)轉(zhuǎn)移到國(guó)外去。“因此,我們只要給出這樣一個(gè)政策,就可以盤活這個(gè)國(guó)家‘三農(nóng)’的全局。”
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不容忽視
彭真懷提出,用新型城鎮(zhèn)化引領(lǐng)中國(guó)的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是我國(guó)的根本前途和出路。
以美國(guó)為例,他分析道,美國(guó)是一個(gè)發(fā)達(dá)國(guó)家,也是全世界農(nóng)業(yè)最發(fā)達(dá)的國(guó)家。美國(guó)的工業(yè)化建立在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的基礎(chǔ)之上,所謂的飛機(jī)、汽車、鐵路都是為農(nóng)業(yè)服務(wù)的。農(nóng)業(yè)與美國(guó)的成長(zhǎng)有密切關(guān)系。“如此比較,國(guó)內(nèi)各個(gè)地區(qū)制訂規(guī)劃的時(shí)候,一直以農(nóng)業(yè)降低為榮,完全是一種本末倒置。”
彭真懷將產(chǎn)業(yè)發(fā)展形容為蓋大樓:“第一產(chǎn)業(yè)是農(nóng)業(yè),是最基礎(chǔ)的,是地基;第二產(chǎn)業(yè)是在農(nóng)業(yè)基礎(chǔ)之上為農(nóng)業(yè)服務(wù)的工業(yè)化。從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分工來(lái)講,這是一個(gè)邏輯過(guò)程。”
“我們削弱了農(nóng)業(yè),在這個(gè)基礎(chǔ)上談我們的工業(yè)化,因此我們發(fā)現(xiàn)工業(yè)化出現(xiàn)了一些糟糕的情況。國(guó)家發(fā)改委一個(gè)規(guī)劃下來(lái),各個(gè)省市進(jìn)行復(fù)制,縣級(jí)小城也復(fù)制,產(chǎn)業(yè)自然就會(huì)過(guò)剩。”
彭真懷最后提出,中國(guó)這么大一個(gè)國(guó)家,按照35%的城鎮(zhèn)化率,還剩有8億農(nóng)民,目前沒有任何國(guó)家的現(xiàn)行道路可供遵循,任何一個(gè)西方理論都不適合中國(guó)的基本狀況。
“現(xiàn)在的農(nóng)民以種糧為恥,離開了農(nóng)村,留下的是5900萬(wàn)留守婦女、4800萬(wàn)留守兒童和5000萬(wàn)老人。如果我們的農(nóng)民都以種糧為恥,國(guó)家走得就不會(huì)長(zhǎng)遠(yuǎn)。” 彭真懷說(shuō)。
此外,85%的群體事件發(fā)生在農(nóng)村,垃圾到處堆,污水到處流,這就指明了國(guó)家未來(lái)社會(huì)管理的重點(diǎn)。“我們之所以提出農(nóng)村的污染問題,就是要把這個(gè)研究當(dāng)做我們的責(zé)任和使命,切實(shí)研究新型城鎮(zhèn)化進(jìn)行過(guò)程中的問題。”
□ 編輯 郭鐵 □ 美編 王迪
王雍君:城鎮(zhèn)化要從權(quán)益保護(hù)入手
□ 本刊記者 郭鵬

王雍君 中央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財(cái)經(jīng)研究院院長(zhǎng)、政府預(yù)算研究中心主任
王雍君認(rèn)為,民生沒有得到可靠保障的原因,是因?yàn)槲覈?guó)目前采取的是有缺陷的方法及有缺陷的保障機(jī)制。
保障與改善民生是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安全運(yùn)行的需要。目前,我國(guó)正處于加快發(fā)展的戰(zhàn)略機(jī)遇期,也是各類社會(huì)矛盾的凸顯期,大量社會(huì)矛盾均集中在與民眾日常生活直接相關(guān)的就業(yè)、公共衛(wèi)生、教育、環(huán)保等方面。
中央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財(cái)經(jīng)研究院院長(zhǎng)、政府預(yù)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認(rèn)為,民生之所以成為備受關(guān)注的問題,是由于民生沒有得到可靠的保障。對(duì)于沒有可靠保障的原因,他在第一屆中國(guó)民生發(fā)展論壇上指出,這是因?yàn)槲覈?guó)目前采取的是有缺陷的方法及有缺陷的保障機(jī)制。
王雍君總結(jié)了方法和機(jī)制方面的一些缺陷。
他認(rèn)為,第一個(gè)缺陷是由于政策制訂者喜歡隨便做承諾。承諾有兩類,可信承諾與不可信承諾。但現(xiàn)實(shí)中不可信承諾要比可信承諾多得多。
第二個(gè)缺陷是目前給民生提供保障的方法主要是“貼標(biāo)簽”。文件只要清楚地標(biāo)明教育支出、社會(huì)保障支出、養(yǎng)老支出和醫(yī)療衛(wèi)生支出等,貼上這個(gè)標(biāo)簽,就斷定是一個(gè)民生政策,但是政策制定后,卻不去關(guān)注真正的受益者是不是普通民眾。一些案例已經(jīng)表明,許多地方增加了資金投入,但是民生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反而造成了大量浪費(fèi)。
第三個(gè)缺陷,王雍君認(rèn)為,是均等化這個(gè)概念。他分析,城市不可能也不應(yīng)該和農(nóng)村均等化。“比如城市的主路有五六個(gè)車道,而農(nóng)村只要有一條小路就可以了;城市有很多醫(yī)院、學(xué)校,如果把最好的醫(yī)療和教育資源,都集中在農(nóng)村,人為地強(qiáng)調(diào)均等化是沒有必要的。”他說(shuō)。
每年,國(guó)家財(cái)政收入都在增加,但是,民生方面的問題卻越來(lái)越多。對(duì)此,王雍君認(rèn)為,城鎮(zhèn)化一定要從權(quán)益保障入手,他多次強(qiáng)調(diào)無(wú)權(quán)益即無(wú)保障。
“權(quán)益有最低標(biāo)準(zhǔn)和最高標(biāo)準(zhǔn),如果權(quán)益不分標(biāo)準(zhǔn),會(huì)帶來(lái)很多詬病。”他說(shuō),“所以中央政府要真正轉(zhuǎn)化決策,把權(quán)利放開,交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根據(jù)當(dāng)?shù)氐膶?shí)際情況取長(zhǎng)補(bǔ)短,這或許就能實(shí)現(xiàn)監(jiān)管保障的最低標(biāo)準(zhǔn)。”
他認(rèn)為,政府還要完善司法救濟(jì)體系,借鑒英國(guó)的發(fā)展思路,在公民的眾多權(quán)益中劃分出公權(quán)益,當(dāng)法定權(quán)益沒有得到保障或者受到侵害時(shí),公民可以通過(guò)申訴,來(lái)尋求司法救助,保障自己的權(quán)益。
總之,在王雍君看來(lái),無(wú)權(quán)益即無(wú)保障,無(wú)保障即無(wú)民生,無(wú)救濟(jì)即無(wú)權(quán)益,他認(rèn)為保障權(quán)益是中國(guó)城鎮(zhèn)化背景下,解決民生問題的終極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