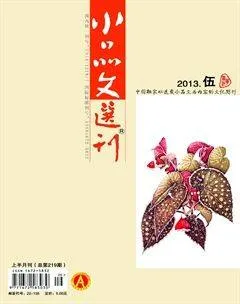永遠的窗口
2013-07-05 02:11:44黃永玉
小品文選刊
2013年9期
我二十四五年前畫過一幅油畫,后來送給朋友,他帶到香港來,在八七年我加題了些字在上面:
“一九六七年余住在北京京新巷,鄙陋非余所愿也。有窗而無光,有聲而不能發;言必四顧,行必蹣跚,求自保也。室有窗而為鄰墻所堵,度日如夜,故作此以自慰,然未敢奢求如今日光景耳。好友南去,以此壯行。黃永玉補記于一九八七年。”
我想,油畫如果有點意義,題些字在上頭亦無妨。
文革期間,我住的那些房子被人霸占了,只留下很小一些地方給我一家四口住。白天也要開著燈,否則過不了日子,于是我故意地畫一個大大的,外頭開著鮮花的窗口的油畫舒展心胸,也增添居住的情趣。
文革之后接著是“貓頭鷹案”,周圍壓力如果不是有點幽默感,是很難支撐的。
阿Q自從向吳媽求愛失敗后,未莊所有的老少婦女在街上見到阿Q也都四散奔逃,表示在跟阿Q劃清界限,保持自己神圣的貞潔。
我那時的友誼關系也是如此。大多朋友都不來往了。有的公開在會上和我明確界限;有的友情不減而只是為了害怕沾染干系;這都需要我用幽默感和自愛心去深深體諒他們的。
我不是阿Q“一失掉卵泡就唱歌”這樣的人:他開朗無心,而具備善自排遣的本領和心胸。
幸虧還剩下幾個“遺孑”式的朋友。他們都沒有當年那批廣大的朋友顯赫;花匠,郎中,工人,旅店服務員……之類,甚至膽子極小的小報編輯。有的公然堂而皇之大白天走進“罐齋”來看我,有的只能在晚上天黑以后戴著大口罩沖進屋來。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