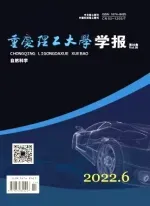地震荷載作用下錦屏地下廠房動力分析
楊 瓊,張建海,殷榮剛,劉喜康
(四川大學水力學及山區河流開發與保護國家重點實驗室,成都 610065)
錦屏一級水電站位于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鹽源縣和木里縣境內,是雅礱江干流下游河段的控制性水庫梯級電站,主要任務為發電。工程正常蓄水位為1 880.00 m,總庫容為77.6 億 m3,裝機容量為3 600 MW(600 MW×6臺)。主廠房、主變室、尾水調壓室三大洞室平行布置,其中主廠房和主變室尺寸分別為276.99 m×25.90 m×68.63 m、197.10m ×24.24 m ×25m,尾調室為2 個圓筒洞室,下部直徑為36 m,高為83 m。
錦屏地下廠房5#機組段地質條件如圖1所示。廠房巖體基本為大理巖夾綠片巖,圍巖類別以Ⅲ1類為主,主要發育有f13、f14、f18三條斷層。其中:f13斷層產狀為N50~60°E,主斷面起伏、光滑,主斷帶寬為1~2 m,層面裂隙及平行斷層的裂隙發育,弱風化;f14斷層位于主廠房上游處,產狀為N50~70°E,主斷面起伏、光滑,破碎帶一般寬50~100 cm,由斷續分布的糜棱巖、角礫巖及少量斷層泥組成,多呈碎裂-鑲嵌結構;f18斷層避開三大洞室,穿過尾水連接洞,產狀為N75E,se<75,斷層處圍巖類別為IV類。
現場進行的地應力勘探表明,圍巖普遍出現中等~強烈的劈裂剝落及彎折內鼓現象。結合右岸地下廠區進行的地應力測試成果分析,廠區最大主應力量值為20~35.7 MPa,屬于高地應力區。廠區基本烈度為VII度,50年超越概率5%的水平峰值加速度達到0.167 g,抗震問題突出。

圖1 錦屏地下廠房5#機組段剖面地質圖
按照設計方案,錦屏地下廠房三大洞室錨桿支護采用預應力錨桿(Ф32,L=12/9 m,T=120 kN)及普通錨桿(Ф32/Ф28,L=7/6 m)交錯布置,局部區域布置有鎖口錨桿(Ф32/Ф28,L=12/9 m)。錨索主要布置有預應力錨索(L=25/30 m,T=2 000/2 500 kN)和對穿錨索。另外,在尾水連接洞洞頂與母線洞底部布置有7排錨筋樁(3Ф32),并布置了10排對穿錨索(T=1 500 kN)。
地下廠房一般由于受到周圍巖體的約束,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相對于地面結構而言)[1]。然而隨著我國西部高地震烈度區一批大型地下洞室群的建設,以及對“5·12大地震”等震害實例的研究[2-3],地下洞室的抗震問題日益受到地震工作者的高度重視。地震荷載作用下地下洞室變形和破壞演化直接關系到地下洞室結構的地震穩定性[4-7]。
本文以錦屏地下廠房5#機組段中心線斷面為對象,建立了二維有限元數值模型,詳細模擬了斷層等地質特征以及洞室圍巖系統支護;選取合適的地質力學參數,采用輸入加速度時程法[8-10],對5#機組段地下廠房二維有限元模型進行動力時程分析。本文主要研究地震荷載作用下的洞周位移、速度及加速度響應情況,并將圍巖的動力破壞區和動拉應力區與靜力作用下進行對比,評價圍巖穩定性,提出合理的抗震加固建議。
1 計算方案
1.1 計算范圍
錦屏地下廠房二維有限元動力分析選取5#機組中心線斷面(樁號0+126.8 m)為研究對象,X方向(N28°E)由上游指向下游,截取長度共589.0 m;鉛直向Y方向底部取至▽1470.0m高程,頂部延伸至山頂。二維建模時根據設計院提供的地質剖面(圖1),嚴格模擬巖層界面、地形、斷層等地質特征。巖體均采用二維4節點等參實體元及其退化單元模擬,共計離散為4 705個節點和4 227個單元。圖2給出了研究區域的二維網格,圖3為開挖區二維網格圖及錨桿錨索單元。
1.2 計算參數
本次二維有限元動力計算采用的巖體力學參數如表1所示,廠區圍巖類別以Ⅲ1類為主,斷層處圍巖類別為IV類。

圖2 錦屏地下廠房5#機組段二維網格

圖3 錦屏地下廠房5#機組段開挖區錨桿錨索單元

表1 錦屏地下廠房圍巖參數建議取值表
1.3 地震作用效應
本次動力計算時,地震波從模型底邊界輸入,左右側邊界考慮為輻射邊界,山頂自由面采用自由邊界。
50年超越概率5%的水平峰值加速度為0.167 g。圖4為輸入的水平向地震波加速度。計算采用的系統阻尼系數ζ=0.05,輸入瑞雷阻尼系數 α =0.523 3,β =0.004 8。

圖4 錦屏地下廠房輸入地震波水平向加速度
2 計算結果
在地震波P50=5%(峰值水平加速度0.167 g=1.638 m/s2)的作用下,三大洞室特征節點及單元位置如圖5所示。

圖5 5#機組段特征節點及特征單元位置
2.1 動位移、速度特征
地震荷載作用下,各特征節點動位移、速度、加速度振動幅值見表2。
由表2可見:三大洞室上下游邊墻特征點處的水平向及鉛直向位移差異較小,均在2 mm以內;另外上下游邊墻特征點處水平向及鉛直向速度差異也較小,在1.78 cm/s以內。可見,三大洞室在地震作用下協調振動。
主廠房的水平向動位移略大于主變室和尾閘室的水平向動位移;而主廠房的鉛直向動位移略小于主變室和尾閘室的鉛直向動位移。主廠房上游邊墻節點754處水平向最大動位移達2.944 cm,鉛直向最大動位移達0.925 cm。
三大洞室的水平向速度基本接近,主廠房上游邊墻節點754處的最大水平速度達11.523 cm/s,與下游邊墻節點1665處的最大水平向速度11.427 cm/s基本接近。另外,上游邊墻節點754處的最大鉛直速度達7.187 cm/s,與下游邊墻節點1665處的鉛直向最大速度7.898 cm/s相差僅0.71 cm/s。
2.2 動加速度特征
地震荷載作用下,廠區最大水平向及鉛直向動加速度等值線如圖6所示。可見地基輸入加速度隨高程上升,地震波受岸坡自由面反射而出現加速度放大現象,廠房三大洞室處于加速度平穩區。三大洞室的水平向加速度在2.5 m/s2至2.7 m/s2之間,鉛直向加速度在 1.7 m/s2至 1.8 m/s2之間。加速度極值分布明顯受到斷層影響,f14和f18之間的區域加速度較小。
如表2所示,主廠房上游邊墻節點754的水平加速度最大達2.781 m/s2,與輸入水平峰值加速度1.638 m/s2相比,放大倍數為1.70;其鉛直加速度最大達1.886m/s2,與輸入鉛直向峰值加速度1.092m/s2相比,放大倍數為1.73。

表2 地震波作用下地下廠房特征節點的位移、速度、加速度

圖6 最大水平向及鉛直向加速度等值線圖
2.3 動靜破壞區特征
圖7、8分別為動、靜力作用下廠區圍巖破壞區分布情況,可見圍巖動力破壞區分布規律與靜力相近,但是破壞范圍和深度有所增加。
地震荷載作用下,主廠房及主變室頂拱破壞區深度進一步增大,分別達到3.91 m和4.4 m,相比靜力作用下加深約0.6 m和0.82 m。主廠房下游巖錨吊車梁塑性區深度則達到了9.05 m,相比靜力作用下的8.26 m加深了0.79 m。另外,主廠房機窩處塑性區深度有明顯增大,其上下游分別達到了6.65 m和7.19 m,相比靜力作用下的6.11 m和5.34 m分別增加了0.54 m和1.85 m。主變室邊墻由于加固措施的作用,上游邊墻僅出現零星塑性破壞點,而下游受到煌斑巖脈的影響,塑性區在6.96 m以內。尾閘室由于采用筒式結構,僅在上游邊墻出現剪切破壞區,深度為4.07 m左右,與靜力作用下相比有所增加,但尚未與f18塑性區貫通。
由于錦屏地下廠房支護措施較強,圍巖強度和整體性得到提高,且尾閘室采用了筒式結構,因此有效減小了塑性區發展。該地下廠房在地震作用下,塑性區擴展微弱,塑性區范圍和深度與靜力情況下相比僅略有增加,設計采用的支護措施可以滿足抗震要求。地震作用下的錦屏地下廠房整體處于良好工作狀態。

圖7 動力作用下5#機組段洞周破壞模式

圖8 靜力作用下5#機組段洞周破壞模式
2.4 動靜拉應力區特征
在地震波作用下,地下廠房各點應力發生波動,致使廠房周圍拉應力區擴大。鑒于錦屏一級地下廠房處于高地震區,動力狀態下的廠房拉應力區是支護設計的重要指標,圖9給出了靜力及動力計算所得拉應力區包絡圖。

圖9 動靜拉應力區包絡圖
由圖9可知,動拉應力區略大于靜拉應力區,且在局部區域有新拉應力區生成。主廠房動拉應力區主要出現在巖錨梁、上游邊墻中下部及機窩開挖區淺表,其中下游邊墻巖錨梁部位的動拉應力區深度達3.45 m。主變室在下游邊墻處新增動拉應力區,其深度在3.3 m以內。尾閘室在上游邊墻底部及下游邊墻處新增動拉應力區,其深度在3.41 m以內。總體來說,動拉應力區深度較小,最深在 3.7 m以內,其量值也一般小于0.2 MPa。
3 結論
1)當地震波為P50=5%(ah=0.167 g)時,主廠房的上、下游邊墻處水平向及豎直向動位移和速度值基本接近,差異較小,表明三大洞室在地震荷載作用下協調振動。另外,廠區處于加速度平穩區,其水平向和鉛直向加速度大約在2.5~2.8 m/s2和1.7~2.0 m/s2之間,與輸入峰值加速度相比,放大倍數約為1.53 ~1.83。
2)廠區動力破壞區與靜力作用下相比規律較為一致,但范圍有所增加。其中主廠房下游巖錨吊車梁破壞區深度達到9.05 m,相比靜力作用下的8.26 m加深了0.79 m。另外,由于新增塑性區多發于洞室頂拱和邊墻淺表層,建議對邊墻和頂拱增加一些柔性支護和阻攔網,以減小地震發生時可能出現的掉塊。
3)廠區動拉應力區略大于靜拉應力區,且在局部區域有新拉應力區生成。動拉應力區主要出現在洞室頂拱、上下游邊墻淺表部及主廠房巖錨梁、機窩開挖區淺表。動拉應力區深度較小,最深在3.7 m以內,量值也一般小于0.2 MPa。
[1]劉寧.地震荷載作用下地下廠房洞室群的動力響應分析[J].水力發電學報,2011,30(6):25 -29.
[2]張雨霆,肖明,李玉婕.汶川地震對映秀灣水電站地下廠房的震害影響及動力響應分析[J].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2010,29(S2):3663 -3670.
[3]鄭永來,楊林德.地下結構震害與抗震對策[J].工程抗震,1999,(4):23 -28.
[4]李海波,馬行東,李俊如,等.地震荷載作用下巖體洞室位移特征的影響因素分析[J].巖土工程學報,2006,28(3):358 -362.
[5]王如賓,徐衛亞,石崇,等.高地震烈度區巖體地下洞室動力響應分析[J].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2009,28(3):568-575.
[6]李海波,蔣會軍,趙堅,等.動荷載作用下巖體工程安全的幾個問題[J].巖石力學與工程學報,2003,22(11):1887-1891.
[7]隋斌,朱維申,李曉靜.地震荷載作用下大型地下洞室群的動態響應模擬[J].巖土工程學報,2008,30(12):1877-1882.
[8]李良權,方丹,楊忠良.地下廠房洞室群動力反應時程分析[J].三峽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2,34(3):1-5.
[9]張建海,何江達,范景偉,等.天龍湖地下廠房地震動力放大區及動拉力區三維有限元分析[J].四川大學學報:工程科學版,2002,34(4):10 -13.
[10]黃潤秋,王賢能,唐勝傳.深埋隧道地震動力響應的復反應分析[J].工程地質學報,1997,5(1):1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