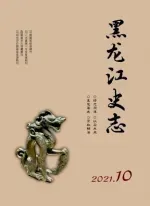源于“古孝”和“今孝”社會問題的初級思考——社會養老問題的提出
紀進鳳
(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一、古孝的內涵與外延分析
中國自古諺云:百善孝為先。如《孝經》所云“夫孝德之本也”;《三字經》也有“首孝悌,次見聞”的訓喻。孔子曾論三年之喪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⑴就是說,孩子自從生下來,沒有三年的時間是沒有辦法脫離父母的懷抱的。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⑵。“為子者,當履父之道。”“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可為孝也。”⑶這些都是在講述,子女為什么應該盡孝,怎樣盡孝道的。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父母活著的時候要孝敬他們,父母死的時候,要根據禮節安葬他們,祭祀他們,并且要守孝三年,以回報父母三年擁懷的養育之恩。又如諺語:樹為蔭影而藝之,子為老年而舉之。凡為人子女,盡孝于其父母,則他日亦可對其子女,要求同一權利。由“孝”自然也生出“敬”來,即“孝敬”;由“敬”亦生出“順”來,即“孝順”。如:母亦同于父。為子者,當非常尊崇之。英國使者麥克多爾卿(Lord Macartney)曾于1792——1793年率第一個英國使團來華,見康熙皇帝“年已六十歲,猶每朝步而朝太后,以表敬禮”。⑷。不難看出中國古代孝道無論在具體百姓生活還是在皇宮貴族中,都已經具備了理論性與較強的實踐性。考量中華五千年的孝史,不難發現,孝的真理,其實質在于追求一種情感——感恩的情感,或者說是在人類無止境的繁衍過程中不斷實踐著的一種人類原始情感的回歸。這是從“古孝”貫穿到“今孝”的基礎,也是中華文化精髓部分得以恒久繼承的源泉。但是,這種理解還是遠不夠的。這僅是對“古孝”做出的狹義概念和解釋,或者說是再現“古孝”的實質內容。
因為在中國古代社會里,“古孝”已經被賦予了更廣泛的涵義。“所謂孝者,亦由于志而判,亦由于行而判”。即,孝不僅要有思想意識來進行評價,還要有行動作為來進行評價,追究思與行的統一。這里的“志”,也可以理解為現代意義上的言語尊敬與溝通到位,因為思想意識的最佳表現形式就是語言,即“說”。所以只說不做,或只做不說,都稱不上“孝”;只有又說又做,才能謂之完美的孝道。《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凡行之有所欠者,皆由于不孝而起。不忠于君,不孝也(“忠孝兩全說”);為官吏而不盡職,不孝也;不信于朋友,不孝也;臨陣而無勇,不孝也。因此,孝者不能單獨靠“孝行”來進行判斷,“實為百行之動機也”⑸。黑格爾曾總結中國古代社會的“孝”為:家庭之義務,自法律而命之,決不可得而違背⑹。傳統社會以“孔孟”治國,儒家理念善其晚年的思想一直貫穿始終,強調弘揚孝道和家庭倫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會公德亦深得人心,孝順有加者可受到鄉親稱贊和社會肯定,漢朝就有“舉孝廉”官職,這是宏觀道德教化舉措。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古孝”是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綱常的根本,也是維持統治階級統治地位的法理依據,更是用以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政治手段和思想工具。
以上分別從狹義和廣義上,對“古孝”進行了闡釋。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體,既然有“孝”的一面,便也有“不孝”的一面。中國古代對“不孝”做出最明確解釋的,當屬孟子。如《孟子.離婁章》云:“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這些世俗“五不孝”的總結,可以說涵蓋了各個方面,已經比較齊整。另外,孟子還提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三不孝”說。顯然,前“五不孝”對實踐“今孝”還是具有很大借鑒意義的。而無后三不孝說,已經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逐步被淘汰在歷史長河中了。
二、今孝的社會性新內涵分析
歷史早已踏上了21 世紀的跑步車。有區別于“古孝”的“今孝”,已經不再局限于“唯父母命是從”的教義上,已經不安分于“老吾老”的理想社會。“今孝”早已開始訴求現實社會里,作為下一代家庭支柱的子女的解放、平等和自由;更多地訴求來自現實社會和國家的保障和義務。這也是“今孝”在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孿生出來的“務實”性,或者說實踐性。理想與現實的差別在于:理想的社會里可以有烏托邦、共產主義;而在現實的社會,人的社會行為會因為個人的社會心理因素,個人社會認知因素的影響而導致社會行為結果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從而有非孝、非善、偽惡、真惡的社會現象與社會真實。這便是“墨菲定律”——事情如果有變壞的可能,不管這種可能性有多小,它總會發生——得以驗證的現實基礎。
其實,社會養老的號召,即“今孝”的“社會養”精神,也被更廣泛的應用到學術與理論界。然而,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政府決策能力的局限性,以及社會民主、民權發展的滯后性,導致中國現代社會在養老的問題上出現了一個介于法律與道德規范之間的真空地帶,——“古孝”今天狹義概念的尷尬,即“古孝”提倡“敬老”“家養”,而“今孝”提倡“尊老”“社會養”,甚或,“社會養”兼“家養”。把國家和社會的義務融合到了“古孝”之中,便得到了“今孝”的新內涵。這即是由“古孝”“家養”演變到“今孝”“社會養”概念屬性發生質的改變的結果,也是人類在社會文明進步過程中尋求自身最終解放的信息符號。
之所以會出現“今孝”“社會養”的新內涵,從社會的角度來分析,有以下產生的背景。
1、隨著近現代西方民權思想與社會公民思想的深入發展與影響,促使“今孝”產生了更多的社會概念,這一概念的出現更是對滯留于“古孝”“家養”的傳統孝道的理念挑戰。
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還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乃至烏托邦社會實踐的失敗,都是西方文明發展史上民權訴求過程中,理論與實踐的萌芽與起點。而近代中國,從康梁戊戌變法,到青年五四運動,也是繼續西方民權思想的實踐延伸。直到中國人找到符合自己的民權思想,即民權運動代表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主、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思想,中國才正式拿到了社會公民權利的鑰匙。新中國的成立是這一思想偉大實踐的成功。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所發出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宣誓與“人民萬歲”、“為人民服務”的歷史承諾,更是將民權思想徹徹底底地擺到了每個人的餐桌上。
2、現代計劃生育國策的直接結果就是“一家一孩、一家兩孩、男女平等”,從而改寫了中國自古以來“大家庭觀念、家族觀念”,生男孩傳宗接代等封建思想,促使“古孝”“家養”的傳統,逐步喪失了大家庭組織的客觀環境,形成中國社會家庭的小型化發展趨勢,。
中國家庭平均人口數量從歷史的進程上看已經明顯呈現縮小趨勢。據統計,中國家庭平均人口由1949年以前的每戶5.17-5.38人到1955年每戶4.47 人。從70年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到中國90年代,家庭規模明顯縮小,1980年為每戶4.61 人,到1990年則為每戶3.92 人,2000年為每戶3.46 人,2010年為每戶3.25 人。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調查數據,1 人戶、2 人戶、3 人戶家庭戶數總和占全國家庭總戶數的比例由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三種戶數綜合的55.3%提高到99.31%(7)。一個初級的社會細胞——家庭,正在中國社會人口政策的引導下趨向于小型化,即基本呈現出一個獨立的三口之家態勢。根據每25年一代人的繁衍規律,未來家庭,一對夫妻,需要贍養二代4 個老人甚至三代8-16 個老人,顯然,這樣的“家養”負擔,已經遠遠超出一個小型家庭的承受范圍。
3、小型家庭的社會地位獨立化、自由化的偏好,引發社會呼喚“今孝”“社會養”。
根據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在全國40193萬戶中,一代戶13736 萬戶,占34.18%,較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34049 萬戶中一代戶7389 萬戶,增加了6347 萬戶;二代戶19223 萬戶,占47.83%,較2000年二代戶20196 萬戶,減少了973萬戶;三代戶占6956 萬戶,占17.31%;四代戶276 萬戶,占0.69%。(8)一代戶的增加,和二代戶的減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表明由父母及其未成年子女構成的家庭、空巢家庭(由不與父母同居的老年成員構成)、單身家庭數量都在增長,混居的家庭規模正在減少。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老年人的養老生活基本上是獨立于子女的小型家庭生活的。而這些小型化家庭已經越來越偏好于家庭自身的社會獨立地位與行動的自由度,即獨享一個三口之家的空間與時間,以及簡單的三口之家的社會關系與天倫關系。
綜上,由社會人口政策導向的現代家庭小型化的社會偏好與趨勢,也已經造成“古孝”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
三、戰略性解決農村今孝實施的方案和建議
其實,“今孝”“社會養”已經具備了一系列的實踐因素。如《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二十條規定:國家建立養老保險制度,保障老年人(年滿60 歲)的基本生活。第二十一條規定:老年人依法享有的養老金和其他待遇應當得到保障。有關組織必須按時足額支付養老金,不得無故拖欠,不得挪用。國家根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職工工資增長的情況增加養老金。這些法律條文是中國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提出了國家養老、社會養老的宗旨。是“今孝”的“社會養”精神在社會決策方面的法律實踐。
但是,這些法律上的實踐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法律的實質,只是告訴社會人應該怎么做,如果不這樣做應該受到什么樣的懲罰。而要具體解決老人的養老問題,還必須付諸更多社會政策上的行動。而社會政策制定的主體更應當深入農村生活,進行實地考察,提出最佳符合農村老人養老的方案與模式,如合理的“社會養”兼“家養”模式等。筆者在考量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和中國人口老齡化階段的基礎上,本著謹慎的原則,提出以下農村養老問題的三個戰略階段。
第一階段: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是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而與此同時,這段時間也是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階段。在此階段(2010——2020年)期間,中國將平均每年新增596 萬老年人口,年均增長速度達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老齡化水平將達到17.17%,其中,8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3067 萬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因此,在這個階段應當逐步在農村養老問題上,采取傾斜性與獨立于城市養老制度的措施,實現“以“家養”為主,“社會養”為輔”為目標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初級普及階段。
第二階段:在中國經濟于205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階段(2020——2050年),也是中國人口加速老齡化階段。伴隨著20 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進入老年,中國老年人口數量開始加速增長,平均每年增加620 萬人。到2023年,老年人口數量將增加到2.7 億,與0-14 歲少兒人口數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 億,老齡化水平推進到30%以上,其中,8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9448 萬,占老年人口的21.78%。在此階段,基本實現農村社會養老模式的戰略過渡。在農村養老問題上,采取健全的社會政策與配套的財稅政策,由第一階段逐步過渡到以“社會養”為主,“家養”為輔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中級普及階段。
第三階段:從2050年到2100年,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階段時,中國人口也將進入穩定的重度老齡化階段。2051年,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將達到峰值4.37 億,約為少兒人口數量的2 倍。這一階段,老年人口規模將穩定在3-4 億,老齡化水平基本穩定在31%左右,80 歲及以上高齡老人占老年總人口的比重將保持在25-30%,進入一個高度老齡化的平臺期。在這個階段,采取穩健的社會政策和配套的財稅政策,在農村養老問題上,全面實現經濟上“社會養”為主,“家養”為輔的養老模式的全社會、全農村的全面普及,實現城鄉統籌一體的養老保障體系。
顯然,人口老齡化必將帶來一些新的矛盾和壓力,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提出新的挑戰:在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方面,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的壓力巨大;在建立滿足龐大老年人群需求的為老社會服務體系方面,加快社會資源合理配置,增加為老服務設施,健全為老服務網絡的壓力巨大;在處理代際關系方面,解決龐大老年人群和勞動年齡人群利益沖突的壓力巨大;在協調城鄉和諧發展方面,解決農村老齡問題,特別是中西部落后和老少邊窮地區老齡問題的壓力巨大。同時,中國政府和社會還必須付出巨大成本來調整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社會管理體制等,以適應人口年齡結構的巨大變化。
事實上,實現“老有所養”還有很重要的配套內容,就是“病有所醫”。人老了最怕得病。政府可以通過適當加大大病統籌的比例、提高專門針對大病的統籌補貼、加大重大疾病的報銷比例等舉措,讓老年人能看得起病,真正擁有一個幸福健康的晚年。
注釋:
(1)歷史哲學(The Lectureson Philosophy of History)/(德)黑格爾著.——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2)中國人的氣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美)明恩溥(Arthur H.Smith)著.——北京:中華書局,2006(2007 重印)。
(3)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關聯法規/ 法律出版社法規中心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05。
(4)中國涉老政策文件匯編/ 孫陸軍.——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9.02。
(5)當代中國家庭結構變動分析,王躍生,2006.06
(6)2009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來源:民政部門戶網站??時間:2010- 06- 10
(7)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
(8)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