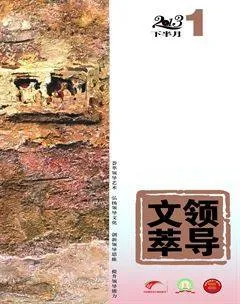中東的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
□基辛格
人們在談到阿拉伯國家動蕩時往往會一一羅列都推翻了哪些獨裁者,但是歸根結底,革命的首要評判標準是建設了什么,而不是破壞了什么。
美國在埃及左右為難
美國自責與胡斯尼·穆巴拉克這個非民主領導人糾纏得太久,從而敦促穆巴拉克下臺。然而,待穆巴拉克真的下臺后,原來那些欣喜的示威者并沒有變成繼承人。相反,沒有絲毫民主履歷、向來敵視西方的伊斯蘭激進派卻當選總統。他們遭到了支撐前政權的軍方的反對。世俗的民主力量被邊緣化了。
從始至終,埃及及其政府是國際社會無可回避的現實。美國政府面對冷戰和該地區日益顯現的混亂,判定必須與一個重要的、愿意為地區和平承擔風險的阿拉伯國家合作。當初,先是蘇聯的冒險主義然后是蘇聯解體的后果,面對這些局面,美國何時可以直接干預該地區內政?從尼克松到克林頓,美國歷屆總統都判斷,這樣做的風險超過收益。喬治·W·布什政府的確敦促穆巴拉克允許進行多黨選舉,批評他壓迫異見人士,奧巴馬總統在上任之初也堅持了類似的做法。美國外交政策對于其他國家——尤其是中東地區——國內治理所呈現的缺點而言,既非原因,也非解決方法。
埃及的革命遠未結束,穆斯林兄弟會和軍方對關鍵機構的職能角力正酣,支持它們的選民力量卻不相上下。美國的政策左右為難。如果美國在冷戰期間犯的錯誤是過分強調安全因素的話,那么現在它可能犯的錯誤就是把派系多元主義與民主混為一談。
現實與理想并非二選一
在這些震蕩中,圍繞美國外交政策的決定因素,爭論再度燃起。現實主義者從安全戰略角度對事件作出判斷,理想主義者則把事件看作推動民主的機遇。但是,戰略與理想主義不是二選一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鼓起勇氣面對問題:我們是冷眼旁觀這些國內進程還是試圖左右這些進程?我們支持其中一方還是支持選舉程序?我們對民主的堅守能夠避免走向基于有管理的公民投票和一黨統治的教派專制主義嗎?
在埃及,支持一個由多為穆巴拉克附庸組成的軍事委員會會傷害民主感情。受意識形態驅動的組織利用民主制度追求非民主目標,挑戰地區秩序。對意識形態上的敵人所展現出的真正溫和,我們應敞開懷抱。但在堅持我們的安全利益方面,我們不應猶豫不決。在兩者之間狹窄的通道內,美國的政策絕不能自欺欺人地認為,重要國家都唯我們馬首是瞻。
兩種主義必須協調
要搭建一條取代巴沙爾政權的政治道路比埃及和其他經歷阿拉伯動蕩的國家的情況更為復雜,因為對立派別為數更多、分歧更強烈。如果沒有一個創造性的領導層,建立包容性的政治秩序,那么敘利亞可能分裂成對立的種族和教派實體。
在敘利亞沖突各派中,各方對民主價值觀的承諾以及與西方利益的協調,以最樂觀的態度來看,也是沒有經受考驗的。“基地”組織現在也參與了進來,實際上是站在了美國被要求加入的一方。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決策者面臨的抉擇并非“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結果之間的抉擇,而是在兩種矛盾的不完美之間的選擇,即戰略考量與國家治理考量。我們在敘利亞問題上陷入了兩難境地,因為打破阿薩德家族與伊朗的聯盟符合我們的戰略利益,但我們不愿公開承認這一點。自從阿拉伯起義爆發,已經有四個政府倒臺,還有幾個政府受到嚴重考驗。美國覺得有義務回應并偶爾參與其中,但是在有關方向的基本問題上美國一直沒有作出回答。
美國能夠也應當參與這次走向基于社會寬容和個人權利的社會的長征。但是,絕不能通過把每場戰爭都完全打上意識形態烙印的方式去做。我們還必須把我們的行動納入美國戰略利益的框架內,由戰略利益決定我們發揮作用的程度和性質。走向采納參與式治理和國際合作的世界秩序,需要我們具備經歷中間階段的堅忍。
還需要心向中東新秩序的各方認識到,我們對他們的幫助將由他們與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的兼容程度來衡量。為此,我們現在視為不可調和的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必須得到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