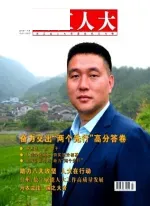斑馬線上的法治
/鄧子濱
人們過人行道時,總不免會碰上一些“鳴響喇叭,加速沖向斑馬線”的“鐵皮將軍”。這是中國城市街頭隨處可見的一幕,也是中國現時法治狀況的縮影。我們有了一定的法治標示和路徑,正如我們有了斑馬線,但我們并沒有認真遵循法治的規則,正如我們并沒有嚴格遵守交通法規。
汽車不讓行人,首先源于歷史慣性。中國最早的有車族無疑是達官貴人,因而在國人的集體記憶中,汽車和權勢聯系在一起。平頭百姓給汽車讓路,就是在給權勢讓路。追憶汽車出現以前的時代,一定級別的官員出門,坐官轎不說,還少不了差人衙役鳴鑼開道。“閑人閃開啦,大老爺過來啦!”你聽,路上的百姓都不過是些“閑人”,官老爺經過,不但要讓,而且要快讓,也就是“閃開”。這種意識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當國人普遍有車后,人讓車已然成為習慣,而當前的路權分配和管理思維也延續并增強了這種定例。汽車時代,何止行人,成蔭的樹木、古老的屋宇,一切都要給汽車讓路。
而汽車不讓行人,也可以曲折地歸咎于行人,因為有太多的行人根本不走斑馬線。這背后同樣有很多原因。中國傳統文化向來重目的輕手段。稍作延伸,就是重實體輕程序,重成效輕規則。哂笑“只看紅燈綠燈,不看有車沒車”,與嘲笑宋襄公“不鼓不成列”是一脈相承的。另一方面,近些年,我們似乎濫用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并使其庸俗化,鼓勵便宜行事,貶斥墨守成規。視規則為束縛,視遵守規則為呆傻,不愿忍受遵守規則的代價,樂于玩味突破規則的利益。
“斑馬線故事”告訴我們:法治成熟需要理性的規則體系,但更需要支撐這些規則的社會情理系統。如果法不容情,或者情不應法,我們所見到的就永遠只能是“斑馬線”上的自私自利和唯我獨尊。
簡而言之,國人不敬畏規則,只懼怕規則背后的人。攝像頭之所以比信號燈更有威懾力,是因為人們相信它背后有一雙權力的眼睛。
當然,規則不受待見還緣于路面上有太多的特權車,它們在堂而皇之地破壞規則,不僅造成了惡劣的影響,也樹立了極壞的榜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壞榜樣的力量更是無窮的,一萬次法制宣傳,也經不起一次對法規的凌駕。總體說來,社會特殊號牌車輛的多寡與法治進步程度成反比。因此,由于特權對規則的扭曲,法治或者一直在昏睡,或者根本就不被信仰。
環顧世界,汽車禮讓行人,香港做得最好,澳門次之;臺灣像塊蹺蹺板,由北向南一路滑坡,臺北很好,高雄很差;放眼歐洲,大致情況是瑞士、德國、英國最好,西班牙、法國次之,奧地利、意大利又次之,捷克、波蘭只能說等而下之。這個排列,同上述國家和地區的法治程度是大致匹配的。法治越健全,斑馬線上越文明;法治越敗壞,斑馬線上越是亂象叢生。
如今,我們治理“中國式過馬路”和整飭各類汽車違規行為,其中就包括“車讓人”。官方的提倡,交警的努力,必然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不過,這個過程也告訴我們,很多事情沒有警察也是可以辦好的,甚至辦得更好。試想一下,讓每條斑馬線附近都站上警察,假如警力充裕,那對于斑馬線上的秩序一定是極為有效的。但有時候我們寧可不要這種“有效”,因為身邊站滿警察只能說明法治的不彰和軟弱。斑馬線是具體而生動的全民法治的課堂,應當在這里學會建設無須權力的秩序,也由此提升人的尊嚴和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