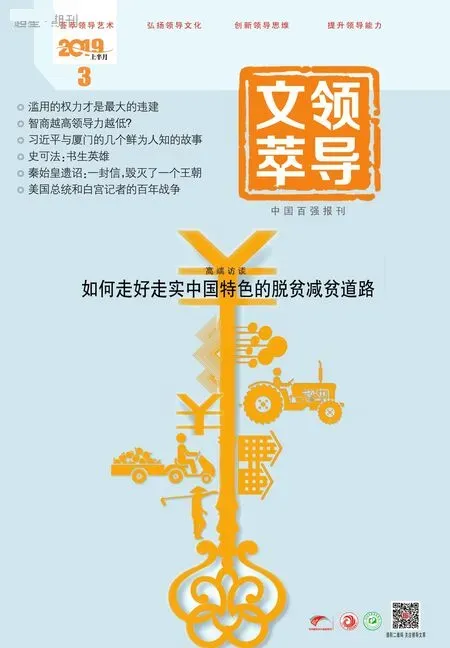美國學者分析“中國學者如何看美國”
□歸宿
中美戰略互疑,似乎已成了當前中美關系中一個熱點名詞和課題。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侃如在共同發表的《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報告中指出,中美雙方對彼此的認識、理解不足乃至偏差,已成為雙方不斷增長的戰略互疑的一個重要來源。最近,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黎友安(Andrew J.Nathan)和蘭德公司高級專家安德魯·斯科貝爾(Andrew Scobell)也發表了文章,試圖解釋中國的戰略分析家們到底怎么看美國,以及他們為什么會這樣看。
文章開篇提出,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外交政策是防御性的,也是一以貫之的:反對外國干涉、維護領土完整、減少鄰國猜疑、維持經濟增長。近二十年來,隨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又擴展到尋求符合中國利益的國際定位以及世界其他大國的接納。對于世界頭號大國美國,中國大多數戰略分析家的看法是:美國是“修正主義”國家,試圖遏制中國的政治影響,并且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
作者認為,中國這一看法的形成,不僅是簡單的基于中國政府對美國政府的認識,更大程度上是緣于中國對整個國際體系的不安全感。
在他們看來,中國的這種“不安全感”有四個層次:首先,中國要維護其被“外部勢力”威脅的政治安全和領土完整;其次,中國要維護邊境的安全和穩定;第三,中國要考慮周邊地緣政治、安全形勢對自身的影響;第四,中國要在更大的國際舞臺上維護權益、爭取利益。然而不幸的是,盡管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美國對中國提供了極大的幫助,但在中國人看來,在這四個環環相扣的利益關切中,美國都站在中國的對立面。
作者同時指出,目前在中國最為流行的國際關系理論——米爾斯海默 (John J.Mearsheimer)的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中國戰略分析家對美國的上述認知。
“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核心觀點是:一個國家會盡自己最大的力量塑造對自己有利的國際環境。在中國的戰略分析家看來,美國在中國周邊增加軍事存在、與亞太地區盟友擴大合作、推進民主等方面的動作,完全符合這一理論。因此,中國體制內的學者大多對中美關系持悲觀態度,認為應當以進攻性現實主義對進攻性現實主義,以更為強硬的政策反擊美國。而那些認為中美關系可以互惠互利的觀點,在學術界往往被“靠邊站”。不過也應注意到,中國政府為了避免“中國威脅論”,在公開的表態中會適當平衡這兩種觀點。
兩位研究者在文中也抱怨,在這種認知的影響下,即便是中美之間互利共贏的合作,在中國人看來也有一些“變味”。如在中美貿易中,雖然中國有大量貿易順差,并持有美國大部分的國債,但中國的戰略分析家依然認為美國實際上占了中國的 “便宜”;美國對于中國經濟開放的鼓勵,也被看成是美國想從對中國的投資中榨取利潤。諸如臺灣、人權、環保等中美關系中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更被認為是美國給中國崛起制造的麻煩——事實上,這些問題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內部多元利益集團對中國的關注不斷上升,美國行政機構并不能完全起到主導作用。即便是中美之間最為核心的臺灣問題也是如此:1972年尼克松曾告訴中國,美國準備放棄臺灣,但出于其國內政治原因,他要到第二個任期才能正式做出這一決定。結果,尼克松第二個任期剛開始沒多久就因為“水門事件”被迫辭職,接任的福特由于在政治上不夠強勢,沒能邁出這一步。卡特上臺后,終止了《美臺共同防御條約》,但美國國會隨即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這一舉動不僅震驚了中國政府,也讓卡特當局大感驚訝。
那么,應該如何應對中國這樣一個對美國有著根深蒂固不信任感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呢?兩位研究者認為,應在中美之間建立新的力量平衡以維持現有的國際體系,但是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毫無疑問將更加重要。
從具體的政策手段來說,應該通過冷靜的專業手段實施,而非夸夸其談。在戰略和貿易上的鷹派語言,更是不利于雙方達成利益共識的努力。同時,美國也應明確自己在中美關系中的利益所在:中國的穩定和繁榮、以臺灣居民愿意接受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在中國外海航行自由、日本及其他亞洲盟友的安全、開放的世界經濟以及對人權的保護。為維護以上利益,美國應做到兩點:一是美國仍然要用實力說話,保持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優勢,二是要抵制中國以不符合西方利益的方式重塑全球法律體系——特別是在人權制度上的努力。而這一切,首先是建立在美國“辦好自己的事”的基礎上的。這些事情包括:維持軍事力量的更新換代、經營和盟友以及其他合作力量的關系、繼續扶持卓越的高等教育系統、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不被竊取、重新贏得世界人民的尊重。
總的來看,黎友安和安德魯·斯科貝爾的文章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中國“戰略分析家”對美國現行對華政策的一些看法。文中提到的一些專家、學者,如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倪峰、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等,也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和指標意義。
但是有一點作者可能沒有認識到:在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領域,中美學界與政界之間的互動關系是完全不同的。美國是學術界的觀點和思想轉化為政府的政策,而中國是政府的政策影響學術界觀點,甚至很多時候,中國學者的一些觀點其實是在為政府政策“背書”。另外,這篇文章也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
不過,中美如果真能像文中所說的那樣,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構成新的力量平衡,不為一些“夸夸其談”所干擾,倒也不失為雙方構建穩定和諧關系的一條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