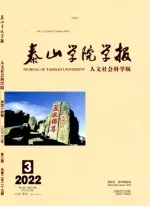白居易詩中之數字與佛禪思想
鄒 婷
(蘇州市職業大學 教育與人文學院,江蘇蘇州 215104)
唐人在詩中頻繁地使用數字,成為其時詩文創作的重要表現形式。從杜審言的“一年銜別怨,七夕始言歸。”(《奉和七夕待宴兩儀殿應制》)李白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望廬山瀑布》)張祜的“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宮詞》),杜甫的“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合香。”(《即事》),到晚唐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春絕句》),唐代詩人自覺且自然地將數字置于詩中,使其顯示出特有的數字美學魅力。這些數字不僅囊括了從一到十、百、千、萬等大大小小的計數單位,還使用了“雙”、“一聲”等多種特殊搭配。這種多變的特殊搭配一方面增強了詩歌的表達效果,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詩歌的節律美感。如張祜《宮詞》中的“三千”、“二十”與“一聲”、“雙淚”所形成的強烈對比突出了宮女凄涼無助的境遇。
數字在詩歌中有著特別的表現功能和藝術價值。它的連用性、可比性、替代性、夸飾性和對稱性在開掘深化詩意的同時,也使詩作本身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感染力。此外,數字入詩的背后也隱含著詩人屬于自我的獨特生命體驗。他們將數字融于詩中,通過這些簡單且毫無情感色彩的概念表達自己獨特的意識與觀念。因此,李白、杜甫、杜牧等人雖然都常以“百”、“千”等數字入詩,但我們卻從“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蜀道難》),“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等詩中看到的是張揚個性、具有天人合一觀念的李白;從“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絕句》)“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中夜》)等詩中看到的是大度沉郁的杜甫。
一
以“百”、“千”、“萬”等數字入詩,不僅可以增強詩歌的磅礴氣勢,渲染詩歌的氣氛,而且還可以開掘深化詩意。因此很多詩人都常常運用“百”、“千”、“萬”入詩來表現夸飾豪放的大度之美,白居易也不例外。但在白詩中所出現的“百”、“千”、“萬”卻常被詩人用以記敘現實狀況。如:“我生來幾時?萬有四千日。”(《首夏病間》)“人生一百歲,通計三萬日。”(《對酒》)“如此來四年,一千三百夜。”(《冬夜》)“四個老人三百歲,人間此會亦應稀。”(《雪暮偶與夢得同致仕裴賓客王尚書飲》)《首夏病間》作于白居易39歲時,他用39×365=14235計算出日子,并以一萬四千日這個實際數字代指了自己的年齡。而《對酒》詩中,人如果能活一百歲的話,通算起來也就是三萬多天。無論是“三萬日”、“一千三百夜”還是“三百歲”,白居易喜歡用刻板、具體的龐大數字來表現自己對時間、生命的感受。這種表達在渲染詩歌氣氛的同時,也更深刻地體現出詩人對無法操控之生命的畏懼,對生命短暫的感嘆。以《首夏病間》為例,“我生來幾時?萬有四千日。自省于其間,非憂即有疾。……內無憂患迫,外無職役羈。此日不自適,何時是適時?”白居易在開頭以巨大的數字計數了自己所生活的天數,在這一萬四千日的統攝下,詩人自言不是憂慮就是有疾病。這種建立在一萬四千日基礎上的自省令人震撼,在這撼人心魄的自省背后同時也透露出白居易對自我的極大關注。由此為鋪墊,與詩末無內憂外患的自適生活進行對照,得出了“此日不自適,何時是適時?”的自省之感悟——及時把握當下的每時每刻是至關重要的。以“百”、“千”、“萬”作為實際計數方式入詩,這是白居易以數字入詩的特點之一。
此外,白居易還常使用龐大的數字來記錄自己的俸祿。洪邁的《容齋隨筆》“白公說俸祿”對此有較為詳細的記錄:“其為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為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凜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從壯年任校書郎到晚年退居洛下,白居易在詩中以具體數字詳細記錄了自己的官俸。這些詩句都可以作為官職、食貨志了。正如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所說:“香山歷官所得,俸入多少,往往見于詩。……此可為官職、食貨二志。”這類數字記錄一方面顯示了白詩記事的平實,另一方面與“如閱年譜”地記錄年齡一樣,文字間折射出白居易強烈的主體意識和平凡的自我之心。
以數字連續記數年齡、記錄日期是白居易數字入詩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洪邁在《容齋隨筆》中也詳細地摘錄了這些詩句:“‘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不準擬身年六十,游春猶自有心情’,……‘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須白頭風眩’……”。從“不展愁眉欲三十”到“壽及七十五”,白居易在詩中用數字清晰、連續地記數了自己的年齡,使人有“如閱年譜”之感。這種數字入詩的方式在其他詩人那里并不多見。同時,他還用數字在詩作中記錄具體的日期,如:“三月三十日,春歸日復暮。”(《送春》)“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曲江感秋二首》之一)“前年九日余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三月三十日的情況,往年八月十五日夜的情景,五十一歲時的狀況,前年、去年、今年同月九日的改變,詩人用清晰的數字記錄下此情此景、彼時彼景。數字的準確具體、一目了然,給讀者留下了清晰的印象。而這種連續、清晰、不可逆轉的印象在感時嘆逝的詩作中也激發了平凡人的恐懼、焦慮之情。一個極度關注自我、感慨個體生命渺小脆弱的凡庸之人——白居易躍然紙上。
時間的流逝、年齡的增長、官俸的變化,這些平淡瑣碎之事借助數字的形式成為白居易反復吟詠的內容。這背后所隱含著的是他對時間生命流逝的感傷憂慮之心,對仕宦沉浮的悲歡喜憂之情,對官軼升遷的復雜感受。而這些都是常人之心,凡人甚至是庸人之情。是什么原因促使白居易如此率性真實地表現自己的凡夫俗子之情的呢?筆者認為白居易的“中人”意識與佛禪思想是他樂于在詩中表現平凡、平庸之情的主要原因。
二
白居易習慣稱自己為“中人”,他是一個努力拼爭與上升和破落之間的“寒士”。他出身平民,具有與平民階層相通的思想情感;但是他的努力又使其在政治階層、經濟地位、社會地位等各方面與平民有著很大的不同。這種“中人”思想,與中唐時代背景下自身所具有的平凡感,多重因素促使白居易在表現“兼濟”思想的同時更感嘆真實生命的渺小脆弱和無法主宰。當這顆敏感平凡之心受到佛禪思想的啟發,蘊藏于身的“平常心”逐漸被發覺。貞元、元和年間,禪宗尤其是南宗禪迅速崛起。白居易在《傳法堂碑》中曾記述了自己向惟寬禪師“問道”的經歷。洪州宗所謂“平常心是道”的思想理論不僅契合白居易“中人”的定位,而且促使他在參悟“平常心是道”的禪理時將自己的情感思想以詩歌的形式記錄并表現了出來。所謂“平常心”就是指“無造作、無是非、無取舍、無斷常、無凡無圣”之心,也就是眾生所具有的不造作、不作分別之心;也是眾生所有的迷與悟而不偏頗之心。[1]這一“平常心”恰恰存在于日常的行住坐臥等活動中。在白居易向惟寬問道那年所作的《自誨》詩,便記述了他“任運修行、隨緣應用”、重視當下現實生活以得道解脫的感悟:“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卻后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而今而后,汝宜饑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病則臥,死則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舍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往哉,樂天樂天歸去來。”詩中,白居易用了一連串的數字表現了個體生命的短暫、渺小,隱含了自己對死亡的畏懼。詩中所說的“饑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正是洪州禪“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皆是道”思想的個人發揮。這也是白居易后來在《有感三首》、《慵不能》等詩中所反復表達且努力實踐的生活信念。[2]
在白居易的一生中,強烈且自覺的生命意識與自我意識始終貫穿其中。較早萌發的自我意識和生命意識使他常常執著地關注自我、關注時間。從“未老發先衰”(《嘆落發》)到“白發生一莖”(《初見白發》),從“一沐知一少”(《早梳頭》)到滿頭白發絲,他將“觀”自身容貌之變化一一入詩。這種敏感使白居易之“觀”從一開始便帶有了某種自覺性。這種自覺促使他很快意識到自我執著所帶來的苦惱。由此,他便有意識地在老莊、道教、佛教中尋求自我可用的“攝生”之道。作為文人士大夫,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促使他常將以官位、俸祿之高低作為自我評價的標準。于是,我們看到,一方面白詩中充滿了對時間、生命流逝的感傷、焦慮、恐懼之情,對功名利祿的渴望追求以及在仕宦得失之間的患得患失之心和歡喜苦悶之情;另一方面,主體意識的自覺又使他在詩中不斷表達自己運用儒釋道之理于觀照、反思中的感悟與超脫。因此,白居易的詩歌常常呈現出明顯的莊禪合論的特點:“本是無有鄉,亦名不用處。行禪與坐忘,同歸無異路。”(《睡起晏坐》)“欲學空門平等法,先齊老少死生心。”(《歲暮道情》)“七篇真誥論仙事,一卷壇經說佛心。”(《味道》)在反復吟詠生死、窮通、聚散之感的同時,詩人通過佛禪、老莊等思想的并用,試圖達到“無念”、“無住”的境界。
佛學思想是“重視人的主體性思維的宗教哲學。”[3]它重視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合一)以提高人的主體意識的自覺性。白居易曾與中唐時期影響較大的幾個佛教宗派如禪宗等有過密切的接觸,并“通學了各宗禪法”。[4]在此過程中,佛禪的慧能與頓悟等思想在無形中增強了他的主體意識的自覺性。因此,在強烈的生命意識和“主觀意識的自覺”的共同作用下,白居易在看空外物與自我以銷盡心中事的基礎上,對自己身為性情中人的凡人本質也有了更深切的認同與接受。在社會經濟地位、階級地位上,白居易將自己定位為“中人”;在俗世生活中,他認定自己是一個追求閑適生活、易感多情、畏懼死亡的渺小、脆弱的平凡人。而佛禪尤其是洪州宗對此類“平常心”的定位更是肯定有嘉。這使白居易得以在詩中更自由地一邊表達感逝嘆老之情,一邊又體悟超越我執的佛理:“兩眼日將暗,四肢漸衰瘦。束帶剩昔圍,穿衣妨寬袖。……坐看老病逼,須得醫王救。唯有不二門,其間無夭壽。”(《不二門》)
談及白居易的佛教信仰,謝思煒認為以白居易為代表的中唐士人接受佛教思想的目的是為了更全面地以佛教思想來檢討和引導自己的人生意識,同時也更熟練地將之與其他思想協調起來并自然地融入到個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中來。因此,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具有調和性和實踐性的特點。[5]現世生活中,白居易運用所掌握的佛教精義思想,從實踐效果出發協調自己入世與出世的矛盾,調和佛教、儒家、道教及老莊的思想,甚至打通了文學綺語與佛教戒律的隔閡。從他中后期所作的《不二門》、《詠懷》、《觀幻》等領悟佛學旨意的詩作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白居易在佛禪思想指導下對自我的反思和認識以及對人性、人生本質的看法。如其詩所言:“強年過猶近,衰相來何速。應是煩惱多,心焦血不足。”(《因沐感發寄郎上人上二首》之二)世間的煩惱使自己迅速衰老,而要徹底銷除煩惱,身心平和,則需要進一步超越自我對一切的執著。“流年似江水,奔注無昏晝。志氣與形骸,安得長依舊?亦曾登玉陛,舉措多紕繆。……亦曾燒大藥,消息乖火候。至今殘丹砂,燒干不成就。行藏事兩失,憂惱心交斗。化作憔悴翁,拋身在荒陋。坐看老病逼,須得醫王救。唯有不二門,其間無夭壽。”(《不二門》)歲月轉瞬,儒士的入世之情也隨著歲月的老去而漸漸消退。功名利祿,只是曇花一現。曾經遵習道教燒丹制藥,憂愁煩惱纏繞心中并未消逝。現在的老病之身,也只有佛教“醫王”方能拯救了。在佛教哲學啟發下,跏趺坐禪、齋戒修行、無生無念之觀成了白居易晚年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垂暮之年到來之時,雖然詩人仍以數字入詩入文,但這些語句卻呈現出與早期不同的心境。比如《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傳好事者》中,便記錄了這次尚齒之會的因緣和壽友相聚的快樂:“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須。手里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文末,詩人還詳細記錄了壽友們的官職與年齡,在這種比照紀史而記友的手法中,可見出詩人的珍惜、享受之情與一絲的炫世之心。面對春意與秋風,暮年的白居易不再為“前心”、世事所困擾,而是在平和的心境中真正享受到當下的閑適與美感。在諸如《新秋喜涼因寄兵部楊侍郎》、《會昌二年春題池西小樓》、《船夜援琴》等晚年的閑適生活詩中,詩人所呈現的更多的是一種“心境皆融”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則直接來源于詩人對佛禪精神的反思。[6]
綜上所述,白居易以數字記敘生活的詩作,不僅體現了詩人真實自然的個性和主體意識的自覺,更體現出詩人對佛禪思想的個人化的詮釋。
[1]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467-477.
[2][4][5]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303 -339、287、292.
[3]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602.
[6]吳學國,秦琰.從“天人和合”到“心境交融”——佛教心性論影響下中國傳統審美形態的轉化[J].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