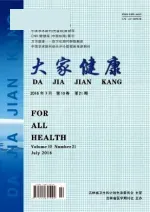新形勢下未婚青年的生殖健康咨詢對策研究
郭曉芹
陜西省延安市吳起縣計劃生育服務站 717600
生殖健康的涵義最早由WHO在1994年提出,并在《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行動綱領》中被采用,是指在生殖系統及其功能和過程所涉及的一切事宜上,身體、精神和社會等方面的健康狀態,不僅僅指沒有疾病或不虛弱[1]。1994年開羅人口與發展大會行動綱領明確要求青少年生殖健康達到的目標是,提供負責任和健康的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務,包括提供適宜的服務與咨詢,解決青少年的性與生殖健康問題[2]。做好未婚青年的生殖健康知識的宣傳工作,提高他們的生殖健康意識,對于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質有重要意義。
生殖健康咨詢存在的問題
計劃生育服務對象狹窄化:咨詢服務是未婚青年獲取生殖健康知識,解決生殖健康問題的重要途徑,然而青年的生殖健康咨詢網點欠缺,計劃生育服務對象狹窄化,是我國未婚青年生殖健康咨詢存在問題的重要原因。未婚青年普遍缺乏性和生殖健康知識,我國長期把計劃生育服務的對象定義為已婚婦女,而未婚青年更需要生殖健康等知識和技術方面的需求,未婚青年的有效需求和計生部門不能滿足他們需求之間的矛盾,使未婚青年的生殖健康知識無處可詢。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在2011年進行的未婚青年生殖健康咨詢服務利用與評價的研究中指出,青年咨詢需要率為39.1%,但是大約60%的咨詢需要未進行咨詢[3]。許多未婚青年不知道去哪里接受教育或者尋求服務。社會提供的服務遠不能滿足他們的性和生殖健康需求。
未婚青年觀念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意識形態、道德標準發生了變化,未婚青年性生活的開放,性早熟與文化傳媒的多樣性,性保健和生殖健康知識的淡薄嚴重影響了生殖健康和生育質量。四川省計劃生育科研有效調查780例調查對象,性與生殖健康知識的各項得分均很低,60.8%的男性和37.7%的女性曾有性行為,發生性行為時有時使用避孕措施者80%,每次都使用者僅占127%,從不使用者占75%[4]。對未婚青年的性健康教育以及生殖健康知識的宣傳和社會道德教育存在的避重就輕,方式滯后等現象,值得我們反思。
生殖健康咨詢體制不健全:我國的“人口健康咨詢師”執業標準中文化程度的要求為初中水平,這明顯不能勝任新形勢下未婚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咨詢工作。一些有錢有勢的人重男輕女觀念嚴重,為了傳宗接代借腹生子、多生、超生、性別鑒定等現象層出不窮,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給很多人帶來生殖健康問題。由于生殖健康咨詢途徑少,健康咨詢機制不健全,每10名未婚青年中才有2人通過某種途徑利用了生殖健康咨詢服務。由于未婚青年的生殖健康咨詢服務質量評價體系不健全,導致相關工作人員態度怠慢,隨訪工作不及時,成為未婚青年的生殖健康咨詢的障礙。
生殖健康咨詢的對策分析
拓寬計劃生育服務對象: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加速進步,計劃生育部門要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相關政策要與時俱進,做到以人為本。在做好已婚婦女生殖健康咨詢工作的基礎上,把未婚青年納入咨詢服務對象。計生工作技術人員按照生殖健康問題的不同類型劃分成不同的小組,有針對性的未婚青年的生殖健康問題分類別提供咨詢服務,并且派專職人員做好隨訪工作。隨訪服務是生殖健康咨詢服務的重要一環,不同的咨詢途徑存在的問題不同,需要有針對性地提高未婚青年生殖健康咨詢服務的可及性和科學性。
加大生殖健康知識宣傳力度:計生部門要加大對生殖健康的宣傳力度,正確引導未婚青年的性行為和生殖觀念。對未婚青年提供具有針對性和可接受性的培訓,生殖健康咨詢工作對女青年要強調自我保護意識,提高安全性行為意識,克服不好意思等心理。避孕節育是開展生殖健康咨詢服務的首要任務,未婚青年工作單位和計劃生意部門可以聯合起來,因地制宜,因人而異,因事而宜的提供生殖健康教育和咨詢等服務,提高生殖健康咨詢的科學性。
建立健全生殖健康咨詢體制:生殖健康咨詢工作機制要以科學發展觀作為指導,堅持疏導為主的生殖健康咨詢方法,建立健全與國際接軌的新機制。工作人員要提高自身素質,端正工作態度,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提高自己的技術服務水平。相關部門制定完善的生殖健康咨詢服務評價體系,包括咨詢需要率與實現率,咨詢途徑利用率、解決程度、滿意程度等,政府要把維護生殖健康咨詢工作作為一種社會責任和社會保障事業去抓,規范市場行為,制止性行為交易市場化,杜絕性行為交易行業化。
在新形勢下做好未婚青年的生殖健康咨詢工作,提供生殖健康教育咨詢服務,全面推進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的發展,對保障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提高綜合國力具有重要意義。
1 王芳.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J].防保康復,2012(31):368.
2 高瑩瑩,張開寧.青少年性與生殖健康服務面臨的新挑戰和新任務[J].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08(12):726-728.
3 楊蓉蓉,韓優莉,談玲芳等.未婚青年生殖健康咨詢服務利用與評價[J].人口與發展,2011(2):94-99.
4 唐永軍,崔念,劉小章等.成都地區未婚流動青年生殖健康現狀和需求分析[J].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12(9):612-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