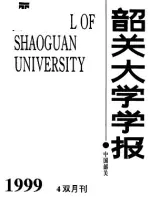銀行保險發展模式選擇分析
(廣東金融學院 保險系,廣東 廣州510210)
銀行保險是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的戰略,是保險公司與商業銀行、郵政儲蓄、基金組織等金融機構合作,通過共同的銷售渠道向共同的客戶群體提供保險產品和服務,以一體化經營的形式來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的一種綜合性金融服務。銀行保險的發展和模式的創新,是經濟全球化、市場化、金融混業經營的必然結果。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競爭態勢,商業銀行紛紛尋求包括保險業務在內的新業務發展機會;保險公司也通過銀行保險的開展拓寬經營渠道、穩定經營、挖掘客戶并節約成本。最終在一系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動下,銀行保險應運而生了。
銀行保險最早起源于歐洲,比利時的CGER、西班牙的La Caixa以及法國的CNP等公司,早在19世紀就開始提供全面的銀行與保險服務了。在中國,銀行保險的起步發展則要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1996年平安保險成立了銀保事業部,2000年8月推出的躉繳型銀行保險產品“千禧紅”一炮打響,自此迎來了中國銀行保險發展的一段黃金歲月。2001年,我國銀行保險保費收入47億元(包含郵政),占全國總保費收入的2.23%;2010年,我國銀行保險保費收入4 399.78億元(包含郵政),占全國總保費收入的30.34%,傭金收入達184.21億元,占整個兼業代理機構總傭金收入的64.99%①數據來源:中國保險年鑒,2010年數據根據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上數據整理而得。。我們可以看出,銀行在發展保險業務方面有其自身的優勢,在這10年間,銀行保險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其保費收入、銀行保險渠道的中間業務收入在所有兼業代理機構中遙遙領先。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雖然我國的銀行保險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相比發達國家,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在目前這種經濟全球化、金融一體化的社會環境下,作為兼業代理主要形式的銀行保險應采取怎樣的發展模式才能持續發揮其優勢互補、強強聯合的優勢,是銀保合作領域值得探究的重要問題之一。
一、銀行保險主要合作模式評析
銀行保險的合作經歷了分業經營制度背景下松散的協議代理階段,到金融混業經營制度背景下緊密聯系的戰略聯盟階段,再到股權參與或設立子公司的滲透階段,這幾個階段的逐步演化,正是銀行保險從初級逐漸發展到高級、漸進式走入一體化的過程。
(一)協議代理模式(Agency Agreement)
協議代理模式是由保險公司和商業銀行簽訂短期的代理合作協議,由銀行利用其經營網點開展代理銷售保險產品、代收保險費、代理資金結算等服務支持。可以說,協議代理模式是金融分業經營下一種最為簡單的合作方式,從銀行的角度來看其優點在于:第一,銀行不用投入特別的資源,僅用其現有網點的剩余生產力即可代理銷售,短期的代理協議對銀行的約束力不大,開辦業務的成本比較低;第二,銀行通過代理保險產品可以拓寬中間業務渠道,代理業務的手續費為銀行增加了一筆較為可觀的收入。而缺點就在于這種短期的代理協議合作方式不穩定,長效合作機制的缺乏使得銀行和保險公司都不愿意過多投入,因此就很難獲得豐厚的報酬,同時這種松散的合作結構,銀行的控制權也較弱,長期來看不利于雙方的共贏。對保險公司來說,通過協議代理銷售保險產品,好處在于以較低的邊際成本潛在地提高了銷售能力,而缺點在于銀行實際很大程度上控制了銷售渠道,雙方的合作關系不穩固,保險公司對銀保的控制權有限[1]。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絕大多數產、壽險公司和銀行之間的合作都處于“協議代理”階段。2003年1月1日實施的新修訂的《保險法》放開了原先一家銀行只能同一家保險公司合作的限制,即以“多對多”的合作模式替代了“1+1”的模式。在此種模式下,銀行對保險公司有了更大的選擇權,銀行與保險公司的合作協議往往是短期續簽,或常常將營銷網點分割給不同的保險公司,頻繁更換合作伙伴。銀行強勢地位的樹立,迫使保險公司展開了代理手續費率的競爭,這樣的完全基于利益的合作勢必影響雙方關系的穩定性,銀保合作的優勢根本無法體現。
(二)戰略聯盟模式(Strategic Alliances)
戰略聯盟的概念最早由美國DEC公司總裁簡·霍普蘭德 (J Hopland)和管理學家羅格·奈格爾(R Nigel)提出,他們認為:戰略聯盟就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有著共同戰略利益和對等經營實力的企業,為達到共同擁有市場、共同使用資源等戰略目標,通過各種協議、契約而結成的優勢互補或優勢相長、風險共擔、生產要素水平流動的一種松散型合作模式。在銀保合作的戰略聯盟模式下,商業銀行將會重點選擇一家到兩家保險公司合作,共同開發產品,共建信息平臺,力求建立長期共享的機制。相比較協議代理模式而言,其優勢在于建立了更為緊密的銀保合作關系[2],雙方通常在項目、產品乃至銷售渠道方面都建立了排他關系,后援部門會為銀行保險提供更多的支持,推動其發展;另外,此種合作模式下,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合作領域更加多元化,不僅產品銷售,在現金管理、電子商務、資產托管等方面都有了進一步的深入合作。戰略聯盟的模式在監管嚴格的亞洲運用得較多,比如在香港市場上,英國保誠保險就與渣打銀行簽訂了獨家銷售協議;2012年10月底,安聯集團也宣布與匯豐銀行簽訂在亞太地區的銀行保險渠道人壽保險10年專屬銷售協議。在中國大陸平安集團也曾在2002年率先提出戰略聯盟的構想,在10月份與中國銀行達成為期8年的全面戰略合作協議,由于相應的條件并不成熟,平安的嘗試并未帶來預想的效果。
(三)組建合資公司模式(Joint Venture)
合資公司模式是指保險公司和商業銀行簽訂資本合作協議,進行資本融合,共同出資建立一家新的保險公司。該公司由銀行和保險公司擁有,共同控制,共享收益,共擔風險。這種模式不僅可以讓銀保關系更加穩固,銀行和保險公司增加潛在收益,且能夠讓銀行參與到產品的研發和設計中去,能夠提供專供銀保渠道的有針對性產品。組建合資公司的模式在歐洲較為常見,像法國Banques Populaires銀行就與卡迪福保險公司共同創辦了Fructitive公司并取得成功。而在中國大陸,由于2003年12月27日頒布實施的新《商業銀行法》第43條規定: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證券經營業務,不得向非自用不動產投資或者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鑒于這樣的法律約束和限制,因此組建合資公司尚未有所嘗試。
(四)金融控股集團模式(Financial Holding Group)
在金融控股集團模式下,保險公司和商業銀行之間交叉持股、相互收購、兼并及合并,或者是銀行收購保險公司,或者是保險公司收購銀行,是實現銀行和保險更高一體化程度的經營模式,一般可以通過兼并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來進行。金融控股集團模式可以讓銀行或保險公司對收購或組建的公司擁有絕對控制權[3];可以使集團內部的潛在規模效益得以體現;可以在集團內部實現風險管理、產品研發及銷售、信息技術等的協同和融合。當然,從國外不少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金融控股集團的模式亦存在不少問題。首先,銀行和保險公司在相互的收購和并購中存在風險;其次,由于銀行和保險公司對對方業務管理經驗的不足,企業文化磨合沖突的存在,都導致了收購或兼并過程中的高昂成本。2009年德國安聯保險并購德累斯頓銀行的失敗案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金融控股集團模式在歐洲和拉丁美洲都較為普遍,像拉丁美洲最大的銀行Santandar投資了20億美元,擴大他們在拉丁美洲的業務能力,提供保險以及其他服務和產品[4]。
二、亞洲國家(地區)銀行保險發展模式的比較分析和啟示
在亞洲各個國家保險銷售的渠道都不盡相同,保險的銷售渠道是同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法律環境密切相關的。從國外情況來看,西歐銀行保險相對比較成熟,這源自于西歐的商業銀行在傳統上就同保險公司聯系密切,且在保險產品的銷售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的銀行和保險因為法律的制約,其聯系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法國、德國、英國和美國銀行保險發展的經驗都值得我們研究和學習,但鑒于我們身處亞洲,文化同宗同源,法律環境相似,銀行和保險業的經營環境相仿,所以其銀行保險成功的發展經驗對于我們來說更具研究和借鑒的意義。
銀行保險目前在亞洲地區正在迅速發展。嚴格意義上說2000年亞洲尚不存在銀行保險,但其產生后發展迅猛,2005年銀行保險在壽險中就已經占到28%,在非壽險銷售中占到2%。這種迅速增長的銷售動力,一是來源于保險公司希望減少依賴收費高昂的代理銷售,通過銀行努力擴大其收入;二是中國、韓國、日本管制的解除大大增加了銀行保險發展的推動力;三是保險公司想利用銀行保險業迅速滲透農村市場。接下來我們將以中國香港為例,來剖析香港銀行保險發展的模式及其經驗。
(一)香港銀行保險的發展模式
香港的銀行業從2000年開始就大舉進軍保險業,銷售的產品主要以投資類產品為主,帶動了整個香港保險業務規模的大幅提升。香港的銀行保險發展主要有兩種模式,分別以匯豐和渣打銀行為典型代表。匯豐銀行和匯豐人壽同屬于匯豐集團,這為集團內的資源整合提供了便利,在銀保產品的銷售中,匯豐銀行將其納入自己銀行產品的銷售體系中,在銷售銀行產品和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協同銷售保險產品,從而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最大限度地留住客戶。經過匯豐銀行的不斷努力,其真正做到了“主動式”銷售,由客戶主動上門購買銀行、保險產品轉變為銀行出去向客戶銷售,在培養這種銷售意識后,匯豐銀行從2003年開始就得到了迅猛發展。渣打銀行在香港和匯豐銀行走的銀保發展路線不同,其與英國保誠保險公司之間建立了“一對一”的長期戰略聯盟合作關系[5],保誠公司一方面負責銀保產品的設計、承保、核保、理賠等業務的處理,另一方面協助渣打銀行做好客戶服務和客戶關系管理,對銀行的銷售人員進行培訓等;而渣打銀行則負責銀行保險產品銷售、銷售流程管理等。銀行保險業務已經成為保誠公司主要的保費收入來源,在2005年第一季度保誠保費中的51%就來自于渣打銀行的保險銷售。
(二)香港銀行保險發展的經驗剖析
不同于內地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香港的金融業實行的是混業經營,大的銀行不僅從事銀行業務,而且從事保險、證券和基金業務等,提供全面的“一站式”金融服務。客戶可以在一家銀行完成幾乎所有的金融業務,香港大型銀行都設有自己的保險公司,即便是專營保險的公司,只要有可能,也都與銀行合作,以便充分利用銀行的優質客戶資源以及品牌擴大保險銷售范圍。
其一,香港的銀行保險銷售渠道廣泛,充分利用了柜面、理財規劃師、電話、互聯網以及郵寄等,并將不同險種的保險產品投放到適合的渠道銷售。比如:汽車保險、航意險等簡易險種通過電話和網絡銷售;而需要較多考慮才會購買的保障型產品則更多在柜臺銷售。
其二,香港的銀行根據金融環境和居民的銷售習慣,重點推出適銷對路的產品。例如:(1)與按揭貸款相關聯的銀行保險產品。香港的按揭貸款業務非常發達,這為該類產品提供了優等的條件。(2)與信用卡有關的壽險產品。香港具有的信用卡持有率非常高,該類產品提供了小額免核保的壽險業務,并且可從信用卡直接轉賬支付保費,方便快捷,得到客戶的認可。(3)開展“強積金”①強積金:是指香港特區政府用法律形式規定的各行各業的在職人員都必須繳納的、強制執行的養老保險基金,屬于社會保障基金性質。業務,通過銀行分行的所有網絡銷售強積金產品。
其三,“客戶經理制”對香港銀行保險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客戶經理與保險營銷員不同,其是保險公司的正式雇員,享有固定底薪,并根據其業績進行傭金提成,客戶經理的選拔注重其高學歷以及過往的銀行工作經驗,他們通過合作銀行取得客戶資料,然后進行預約、面談、最后簽單及提供服務。
三、中國銀行保險發展模式的現實選擇
(一)以分銷協議為主的銀保模式仍然是中國銀行保險的現實選擇
任何一個國家在選擇其銀保合作模式時,其選擇的依據均是該模式的運作效率水平,無論是選擇分銷協議模式、戰略聯盟模式抑或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關鍵在于該模式能在特定的環境中有效運作。通過研究分析,我們發現中國目前仍處在銀行保險發展的初級階段,銀行與保險公司的合作多限于代理銷售,而且這種代理銷售的效率水平較高,起碼到目前為止尚不是選擇一體化經營的最佳時機。
(二)大力發展銀保合作的戰略聯盟模式
銀行和保險戰略聯盟的合作方式,目前在我國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制度環境下是合法合規的。2008年1月16日,中國銀監會和保監會在北京正式簽署了《中國銀監會與中國保監會關于加強銀保深層次合作和跨業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指明銀行和保險之間可以開展深層次合作。顯然,在當前分銷協議模式的基礎上發力發展戰略聯盟的合作方式是最理想的選擇。銀行和保險公司實現戰略聯盟意味著其可以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等戰略目標,雙方可以共享銷售網點、客戶資源、合作開發新產品、建立統一操作平臺、融資合作等,為將來銀保合作的最高層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奠定基礎。
國內不少保險公司和銀行之間已經進行了積極探索和嘗試,例如2003年6月太平洋保險集團與招商銀行在深圳簽訂針對高端客戶的 “金葵花-太平洋”保險計劃,標志著雙方合作進入了深層次的戰略聯盟。2007年1月中國人壽保險公司與招商銀行則在北京簽署了全面戰略合作協議及相關業務領域的具體合作協議,準備在合作發行聯名信用卡、合作開發集合年金計劃、捆綁進行企業年金市場拓展等方面進行積極探索。
(三)金融控股集團模式是我國銀保合作的終極模式
我國銀保混業的破冰要追溯到2008年1月,國務院批準了銀監會和保監會提請的“160號”文件,“160號”文件指示銀行和保險公司可以相互入股,但銀行投資新建保險公司則不被允許,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合資公司的銀保合作模式在國內我們暫且不予考慮。而從當今世界銀保合作的發展趨勢來看,組建金融控股集團已成為主要模式,從國內某些銀保合作上也充分預示了組建金融控股公司將是我國銀保合作的終極模式。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于2009年11月正式發布了 《商業銀行投資保險公司股權試點管理辦法》(銀監發﹙2009)98號),銀行入股保險公司終于拉開了序幕。2009年9月,保監會同意交通銀行收購原“中國人壽”持有的中保康聯51%的股權,中保康聯更名為“交銀康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2010年4月28日,保監會批準北京銀行收購首創集團持有的首創安泰人壽保險有限公司50%的股權,首創安泰更名為 “中荷人壽保險有限公司”;2011年1月,保險會批準了建設銀行收購太平洋安泰人壽保險有限公司51%的股權,并擬更名為“建信人壽保險有限公司”;2010年10月,工商銀行宣布將斥資12億入股金盛人壽,收購金盛人壽60%的股權,交易完成尚有待保監會批準。在保險公司入股銀行方面,亦有中國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在2006年12月斥資56.71億元收購了廣東發展銀行20%的股權;中國平安保險集團于2007年1月投資49億元收購了深圳商業銀行89.2%的股權,并將其更名為平安銀行。從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政策面監管的放松,銀行保險業將來成立金融控股集團是必然的趨勢,金融控股集團強大的規模和控制力可以使銀行保險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婁秋弟.我國銀行保險的戰略聯盟構建:結合新華人壽案例分析[D].杭州:浙江工業大學,2008.
[2]李隆海.我國銀行保險合作模式研究[D].廣州:暨南大學,2008.
[3]高濤.保險公司在銀行保險發展中的風險分析及路徑選擇[J].廣東培正學院學報,2005(4):47-50.
[4]胡浩.銀行保險[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216-244.
[5]張廣華,童芳芳.銀行保險制度研究及路徑選擇[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9:179-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