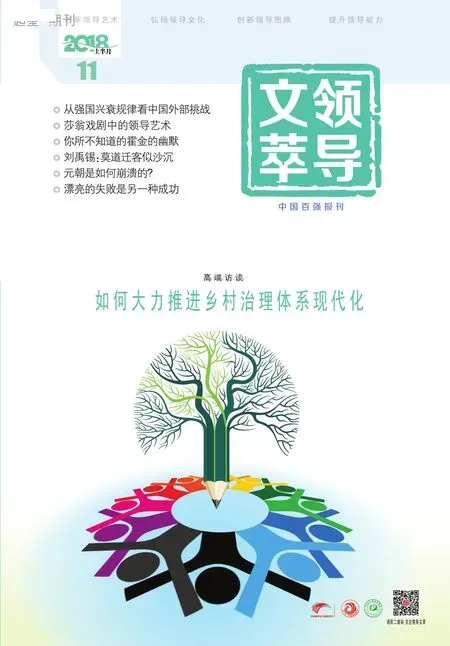清心篤行—吳官正同志二三事
□王志宏 張振明

“今天老百姓還窮成這樣,你還有什么光榮?”
“我現在處理信訪時總是想到窮人,想到要公正地對待老百姓。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忘記了窮人同樣意味著背叛。當領導的一定要關心群眾生活,尤其是關心那些日子過不下去的人的生活,關心城市下崗職工和困難職工,關心農村還沒有脫貧的農民,關心家里出了天災人禍的干部職工。人有困難的時候,是最需要幫助的。找你們信訪的群眾那只是少數,還有好多有困難的群眾沒找你們呢。所以,我們要主動多幫老百姓解決一些困難。”
吳官正到基層調研,到一個村里,看到村干部作風松松垮垮,群眾生活困難,村干部還說:“我們是老區,要發揚光榮傳統。”吳官正說:“老一代為革命做犧牲,那是他們的光榮;今天老百姓還窮成這樣,你還有什么光榮?”跟隨他的同志提醒說:“這個地方是‘通天’的,還是少批評兩句吧。”吳官正說:“老祖宗給我們這塊土地,國家給了我們好政策,共產黨給了我們一頂烏紗帽,我們有什么理由不把事情辦好!”
“花架子”與“智囊團”
“這么大的武漢市,憑我個人的聰明和才能,遠遠不能挑起市長這副擔子。”
1983年3月,吳官正剛剛任職市長,他既未“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未初來乍到踢“頭三腳”,而是游說學府,登門求賢。50天過去了,一個高水平的“智囊團”——市政府咨詢委員會正式成立了。32名咨詢委員中有副教授、高級工程師以上職稱的就占29名。咨詢委員會下設工業、交通、農業、科教、財貿等8個專業咨詢組,共86名成員,幾乎包括了當時社會學科和自然學科的各大門類。
“智囊團”開張大吉,市直機關卻議論紛紛:“剛上臺,就鬧起花架子。”“有本事自己干,拉專家、教授嚇唬誰呀!”
的確,當官的“求教于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可以與“沒本事”畫等號。再說,基層干部對某些領導的“老三招”也摸透了:對上,伸手大講困難;對下,搞命令主義;當這兩招都失靈,就玩起第三招——形式主義和花架子。
“市長大人背后站這么一大排書生,你說這架子花不花?”這說明干部和群眾深深厭惡“花架子”。吳官正心里清楚,現代社會形勢錯綜復雜,事情瞬息萬變,市長不可能是通才,而遇事又要及時作出正確決策,充分運用科學家、專家的專長和智慧以縮短領導職責與個人能力之間的差距,實屬必要。這不能與“花架子”同日而語。
搞改革,每前進一步,總是要遭人非議的。吳官正并不回避。他自信地說,運用“智囊團”,我們是剛剛開始。
老師一番話,省長記一年
1989年3月,江西省教委在南昌市召開教育工作會議。省長吳官正發現在座的有南昌市一中的張富老師,便起身走過去,輕聲問道:“前兩天的會上是你談到你們學校的危房問題的吧?你給我寫個報告,現在就寫。”半個小時后,他再次來到張老師身旁,告訴他自己已在報告上簽了意見,交有關同志辦理了。幾天以后,他又一次見到了張老師,第一句話便說:“危房問題我已經同你們市長面談過了。”一旁的南昌市市長接著告訴張老師:解決危房問題,市里已列入了計劃。
一年之后,春節前夕的一個中午,吳官正突然來到了張老師的家。當張老師手足無措之際,省長已經帶著滿身寒氣在沙發上落座了:“張老師,去年你反映的危房問題,我來看看解決了沒有,也來給張老師拜個年。”
激動中,張老師竟不知如何作答。
人們聞訊趕來,坐了滿滿一屋子。學校領導向省長匯報了一中危房改造的情況:兩幢危房已全部拆除,建房資金也籌集好了,一幢占地約1000平方米的新樓不久將開工。
吳官正欣慰地說:“解決了我就放心了。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改善辦學條件。”
這是一樁小事,卻也堪稱佳話。后來有心人又將此事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概括:老師一番話,省長記一年。
吳官正出生于貧民家庭,憑著自身的勤奮和聰穎,考上了清華大學動力系。他的大學同學回憶說,從本科到讀研究生,冬天他一直穿著同一件破棉襖,還用一根繩子系著。這種生活上的清貧簡樸慢慢地內化成他的一種獨特作風。他任武漢市市長時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起當時的情況時說:“官正同志非常廉潔。他傳承了農民身上最質樸的東西,夏天穿一雙塑料涼鞋,冬天穿一雙解放鞋,穿一件軍大衣,戴一頂軍棉帽。從衣著打扮上看,很難想象他是一個市長。”
生活中,吳官正清心寡欲,工作中他又馬上變成了另一個人,經常處于一種精神高度集中的忘我的工作狀態。這種忘我的工作狀態,從他一開始走上工作崗位便是如此。他由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后即到武漢市葛店化工廠擔任技術員。對于這段工作經歷,武漢《長江日報》1973年刊載的一篇專題報道曾有這樣的描述和記錄:吳官正“拜工人為師,和工人們一起出大力、流大汗……”有一位省領導則回憶說:“一次他在江西生病輸液,聽說發生了緊急安全生產事故,他二話沒說,拔掉針頭,擰開葡萄糖水瓶蓋,咕嘟咕嘟喝完立即趕往現場。”
吳官正常說:“歷史不是寫出來的,是干出來的;老百姓心里有桿秤,這才是衡量正確與否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