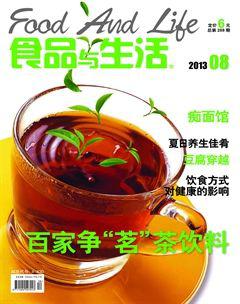豆腐含情
夏敏
1977年我響應(yīng)政府號召上山下鄉(xiāng),戶口從城市遷到農(nóng)村,象征居民戶口的“豆腐票”沒有了,就是這張小小的豆腐票改變了多少年輕人的命運。
那時,我一廂情愿地認定豆腐就是豆制品中的老大。家里的小孩搞不清豆制品和豆腐的關(guān)系,以為豆腐就是豆制品,豆制品就是豆腐。
長大了,漸漸識貨。原來豆腐只是豆制品家族一份子,是眾多兄弟姐妹的一員。這份“人家”很大,你不要想一頁翻盡,嫩豆腐、老豆腐、豆腐干、豆腐皮、豆腐衣、厚百葉、腐竹……猶如將軍沙場點兵,數(shù)不勝數(shù)。
縱觀我的餐桌,沒有一種東西有像豆腐這樣頻繁出現(xiàn)。豆腐是百搭的貨色,煮湯、熬菜、生拌,樣樣都好,冷食熱食皆宜。天熱,來一個涼拌豆腐,清清爽爽;天冷,弄一個麻辣豆腐,渾身通透。渾身疲乏,缺少油水,來一碗紅燒肉,擱任意一種豆制品,驚喜是一定的,一筷子下去,一肚皮返俗,馬上接地氣,浮想聯(lián)翩。
你不要以為豆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它的過去會讓你頓生敬意,曾經(jīng)是身份顯貴的一種菜。有一次朱元璋在逃難當(dāng)中饑餓難耐,已奄奄一息。一位老婆婆把家里的剩飯和青菜豆腐混搭做了一道飯菜給朱元璋充饑。朱元璋狼吞虎咽,問老婆婆是什么菜,老婆婆回答:“珍珠翡翠白玉湯”(珍珠即米飯粒,翡翠即青菜葉,白玉即豆腐塊)。后來朱元璋做了皇帝,時常想念這位恩人,難忘珍珠翡翠白玉湯的美妙之味。古人云:“美食含情”,大概就是如此吧。
北宋文學(xué)家蘇東坡當(dāng)年被貶湖北黃州時,生活條件異常艱苦。灑脫的蘇東坡自食其力,用自己耕種的黃豆制作成豆腐,精心烹飪。朋友吃了風(fēng)味獨特的豆腐菜,贊不絕口,親切稱之為“東坡豆腐”。清代袁牧曾說:“豆腐得味,遠勝燕窩。”
寫到這里,又到了晚餐時間,今晚為家人做一道小清新菜——黃豆芽豆腐湯。挑新鮮的黃豆芽,去根;把自制的咸肉切成薄片,焯水;嫩豆腐切塊待用。黃豆芽放在油里煸透,倒入冷水燒開,隨后放入咸肉、豆腐一起煮,煮到湯色發(fā)白,擱少許鹽,起鍋前放味精吊鮮。口味偏重的,可放一小撮胡椒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