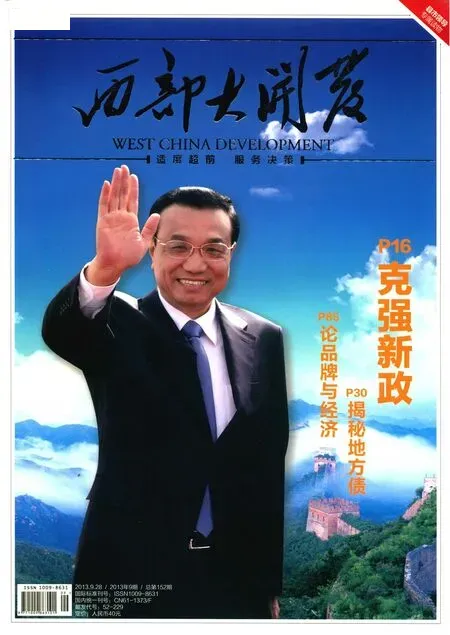山西蒲韓綜合農協試驗
□文/戴志勇 陳建宇
山西蒲韓綜合農協試驗
□文/戴志勇 陳建宇
經濟社會多重職能兼具,土地經營“統分結合”部分規模化,合作金融體系在摸索中發展,山西蒲韓綜合農協樣本有諸多可取之處。

綜合農協這種農村社會經濟組織方式,20世紀誕生于日本,并迅速在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全面推廣。它依法設立、覆蓋全地域和全體農民,以金融、經營、社會、文化等綜合功能全面保障三農,使得農民組織及其組織保護下的農民成為合理共享市場利益的主體。無論風云變幻、政事更迭,該組織方式屹立百年不倒,且至今仍然擁有不斷推陳出新的改善能力。
綜合農協的組織方式在中國大陸有沒有可能實行呢?在山西永濟市,有一個自1998年設立的農民合作組織,歷經15年,至今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不輸于日韓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大陸本土的綜合農協。這就是山西運城地區永濟市的蒲韓鄉村社區。
土地入股,全面合作
農協緣起于1998年在蒲州鎮寨子村建立的“科技服務中心”,2000年又建立了“婦女文化活動中心”,在當地黨政主要負責人的大力支持下,2004年經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為社團,正式設立了“永濟市蒲州鎮農民協會”。2007年更名為“果品協會”。由于業務范圍超越蒲州,跨蒲州和韓陽兩個鄉鎮,所以,自取了“蒲韓鄉村社區”的名字。農民口頭禪還是稱其為“協會”。
這個協會根植于規模足夠大的農村社區——這是協會內部能形成長期可持續、循環式發展的基本條件。
協會橫跨蒲州、韓陽兩個鄉鎮共24個行政村和19個自然村,會員四千多戶,服務的農民群眾超過2.5萬人,占了兩鎮總人口的一半。
這個協會擁有經濟、社會、文化的綜合性功能——這是使得一個規模化的社會經濟體成為生產、消費、分配、交換緊密聯系的有機體的根本舉措。
現在,蒲韓鄉村社區已經成為擁有大宗農產品運銷、有機農業種植和技術推廣、農資購買和消費品購銷、手工藝品生產與銷售、信用合作,以及老年服務、健康服務、垃圾處理、社區教育、農耕文化等多種功能齊備的綜合性的“三農”協會。
這個協會做到了農民共富、利益共享、城鄉合作、社區穩定有序——而這正是我國破解“三農”難題所期望的主要目標。
協會以農民土地入股方式推動土地流轉,形成有機農作物機械化規模生產,并通過產后與各類公司進行規模化銷售合作實現了以較低成本與城市進行交換,使得協會會員連續三年實現戶均收入增長20%,可以說基本解決了小農戶與大生產以及小農戶與大市場對接的難題。
協會不僅在生產、銷售環節實現了小農戶的合作,而且,在生活領域也實現了合作。協會將經濟收入扣除各類成本后的剩余用于三個方面:一是支持蒲韓鄉村社區自身公共服務——老人、兒童、婦女等各類人群所需要的照顧服務、文化教育事業,還有清掃垃圾、村史諺語、節慶禮儀等多方位的公共事業;二是協會經營事業的發展包括購買大型農機具;三是給會員按股分紅。
可以說,協會已經成了當地小農戶共同致富、共享公共利益,維系社區基本社會秩序的當仁不讓的組織者、分配者和管理者。
據筆者八年的跟蹤觀察,蒲韓鄉村社區不僅在農業經營上不輸于日韓以及中國臺灣地區農協,而且,在廣泛深入地聯系農民會員,應其需求而提供公共服務、繼承和弘揚傳統農耕文化等方面還有明顯的超越。
綜合農協的運作方式
蒲韓鄉村社區為什么能獲得如此出色的成效?
首先,是有好的帶頭人、自下而上小農合作的民主自治組織和較完整的組織治理結構。
這個協會三年一選舉,實行理事長領導下的總干事負責制。目前理事長和總干事由一個民辦小學教師出身的農村婦女鄭冰一肩挑,協助總干事的是三個助理——均為三十上下的小伙子,分管經營、公共服務和財務。
協會的基層組織是鄰近的5戶農民結成的會員小組,共有七百多個。小組之上是22個技術產銷班(通通按照專業合作社登記注冊),按各種農作物分類負責農技培訓與推廣,以及農資和農產品的統一訂購、統一銷售和統一集貨。為這22個班進行農業生產與技術推廣服務的是農協的一個經營部門(登記注冊為有機聯合社),由6個專職員工負責。而為這22個班分別進行農資購銷服務和農產品營銷服務的是農協另外兩個經營部門——農資購銷中心和城鄉互動中心。
這樣一種農協治理結構兼顧了公平與效率,以相當低的決策成本實現了以自愿為基礎的集體決策。另外,由于農協處于鄉鎮社區,與村委會不在一個層次,與幾十個村的村委打交道,東方不亮西方還亮,在競爭性的農協社區組織工作中,找到了一種能夠化解與村委會之間的矛盾并得到鄉、縣兩級政府支持的機制。
其次,有良好的組織、分配制度和有執行力的本地農民的工作團隊。
協會在總干事領導下,組成金融部門(資金合作社)、經營部門(有機聯合社、城鄉互動中心、手工藝合作社、農資購銷中心、研發與農技推廣部門(青年農場)、公共服務與文化部門(老年服務中心、健康協會、兒童服務、農耕家園)。
這些部門的員工合起來構成總干事團隊。52名員工基本上是當地農民,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多歲。他們全職授薪,每月底薪800元,根據工作業績考核可以拿到附加工資和年終獎金。
協會每年的收入除去支付員工工資和行政辦公費外,還有可觀的盈余用于協會支持的社區公共服務和會員分紅。
再次,有自行開發的一整套協會農戶工作方式作為農村社區工作的基礎。
協會的農戶工作分為工作人員分片包戶、入戶訪談、農戶檔案、信息收集與傳遞和部門內外交流等一系列首尾相接的工作程序。
為了讓農民出身的協會工作人員永葆和農民密切聯系的本色,協會要求52名工作人員必須承擔分片包戶150-500戶的職責。每個工作人員每天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外,都要到包干戶家中訪談,除了有統一要求的部分例如各戶的人口、耕地、農作物并建立農戶活動檔案外,每個工作人員還要通過經常入戶,及時了解農戶的各種需求,并且在部門的每日晨會和協會的每周、每月工作例會上互通信息。
這其實是一種制度化的基礎信息設立機制和日常信息的交流機制。它不僅密切了協會各部門工作人員之間的聯系,更重要的,是能夠及時發現農戶需求并且及時滿足。老年服務部就是通過這樣的信息交流機制迅速找到了臥床不起的失能老人和殘疾人的需要,為其配備了同村的婦女或者健康老人做照護員。
這套工作方式繼承和發揚了大陸鄉村工作的傳統,與日韓以及中國臺灣地區農協的組織經驗不同,有特色且有實效。
農民有極大的組織創造力
無論從經濟效益還是社會效益看,蒲韓鄉村社區的實踐都是成功的。這個成功主要依靠的是農民自身的組織和制度創新,15年來協會并未收取來自政府的一分錢的支持(不是政府不給,而是協會不要),來自社會的支持也采用的是合作方式,“絕不白拿任何人一分錢”,成為協會自強自立的規則。
頗具啟發意義的是,這個協會的實踐正好跨越了我國1978年農村分田到戶和2006年取消農業稅這兩個重大制度變革的時點,發生在近十年來我國農村地區之間、農民之間的貧富差距迅速拉開,農民權益保護與經濟收入、公共福利等問題并駕齊驅、愈演愈烈,國家用盡種種方式改善卻未見多少成效的大背景下。
協會的成功實踐證實了一個幾乎是老生常談的原理:中國農村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生產力問題,而且是與物質利益相關聯的以農民為中心、以農民合作組織為紐帶聯結的社會關系問題。
僅僅依靠資源配置,無論用什么方式,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由國家和城市向農村輸入資源的方式,還是農民自己組織單純的經濟合作社方式,都無法真正解決這類社會關系問題。僅僅依靠鄉村體制改革,包括撤鄉并鎮、合村并組、減少鄉鎮干部、取消村民組長、加強村支兩委發放干部津貼,推廣大學生村官,建設村級社區服務中心等等,在勞力、土地、資金三要素基本流出農村的現實背景下,已經無力維系農村的基本社會秩序。
在當下的環境下,破解“三農”問題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需要將資源配置和鄉村體制改革整合起來,建立能夠改變現行鄉村資源結構和治理結構的強有力的新型社會經濟組織。它既能給農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又能維護農民的基本權利,還能對改善農村公共服務落后局面做出看得見的貢獻,可以從根本上加強農村內生的解決問題和保持社會秩序穩定的能力。
這就是中國式的綜合農協!它不僅能在既定的“三農”目標上探索新的實現手段,同時還能在實踐探索中深化對原來目標的認識。
蒲韓鄉村社區的經驗表明,農民中蘊含著極大的組織創造力。綜合農協這種新型的社會經濟組織本質上就是中國式的社會企業。它擁有一種奇異的創造力和自我修復力,使得這個組織的可支配資源,無論資產、收入、人才,還有會員以及協會內外的各類經濟、社會組織,都能在不斷更新和自我修復中逐漸長大,同時,協會自身的能力也得到訓練與提升。在這種農民集體實踐的創造過程中,新的意識、新的觀念、新的價值、新的道德、新的倫理、新的制度就迸發出來了。

可是,當代中國學界的知識生產,距離實踐領域已經達到的豐富性和強度何其遠也!
但這也告訴我們,想要尋找的“三農”現代化的普遍標準不在別國和他人那里,就在我們自己腳下。所以,把目光對準當今中國農村的社會實踐,即便現在還處于邊緣地帶,屬于零散和非主流一類,卻對于解決實際問題有奇效的實踐,并從中挖掘支撐中國“三農”現代化的新邏輯、新規則甚至新目標,把它們提升到主流地位上,這,才是學界和政策界迫切要做、該做的事。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