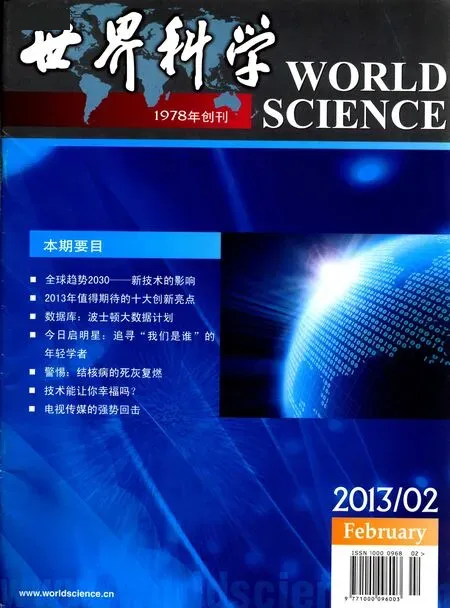“大數據”暢想
思柯

新年伊始,各大科學媒體紛紛為讀者呈獻未來展望的新篇章。在本刊連續兩期推介的一系列新科學圖景中,除了宇宙暴漲新證據和ISON彗星掠日太空秀,以及多國科學家南極冰下湖探秘新生命值得期待以外,氣候變化和醫學健康的有關話題也將備受關注。而歐盟的FutureCT、英國的高能效計算和美國的數據解決方案使信息技術繼續成為看點,還不斷彰顯出科學和未來研究的“大數據”色彩。
“大數據”一詞原本出自天文學和基因研究等科學領域,像斯隆數字巡天計劃就獲得了200萬個天體的光譜數據,人類基因組計劃測出了人類DNA30億個堿基對序列,這些數據對學科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如今的“大數據”則不僅與科學研究直接有關,更多體現的是社交網絡、云計算和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對人類社會產生的重大影響。2007年,數據庫專家吉姆·格雷首次提出了數據密集型的科學研究“第四范式”。2011年,麥肯錫預見“大數據時代”來臨,指出“數據已經滲透到每一個行業和業務職能領域,逐漸成為重要的生產因素;而人們對于海量數據的運用將預示著新一波生產率增長和消費者盈余浪潮的到來。”
美國政府基于對新信息時代的準確把握,于去年3月適時發布“大數據研究和發展倡議”,全面布局“大數據”的研發和應用。這是繼1993年“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計劃”之后,美國實施的新一輪信息化戰略舉措,并沿襲了以往國家總動員的方式,加大投入,以期保持其全球信息技術和產業引領者的地位。波士頓則立志打造世界大數據之都,在未來10年催生“成千上萬的工作機會和數百間公司”。
大數據確實已經滲透到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按照里克·斯莫蘭的說法,“一場非比尋常的、幾乎不可見的知識革命正在席卷商界、學術界、政府、醫療保健機構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事實、產品、書籍、地圖、對話、參考資料、觀點、潮流、視頻、廣告——大數據無處不在,似乎可以重回畢達哥拉斯“數即萬物”的數本主義時代,抽取出宇宙的大數據本質和精髓。
好的世界也是壞的世界,與此同時,“大數據洪水”抑或是“數字化野火”所構成的社會風險也在加劇和蔓延,人們應當認識其陰暗的一面,并有所作為。也許大數據本身就是解決之道,像阿西莫夫《銀河帝國》中,哈里·謝頓建構的心理史學一樣,從銀河數以千萬兆計人口行為分析中預見帝國的興衰,并拯救帝國于危難之中。心理史學靠的是謝頓函數和功能強大的“元光體”,當下,大數據利器的出現也將為時不遠吧。
說到《銀河帝國》,似乎里頭還有一樣叫做“穹頂”的東西,它再造了大氣環境,銀河中心川陀星球的人們生活在金屬穹頂之下,沒有風霜雪雨,更沒有PM2.5等等的毒害,當然也見不到自然的天空,除了皇宮還存有一小片露天庭院。不知道地球的未來,是不是也在阿西莫夫的預言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