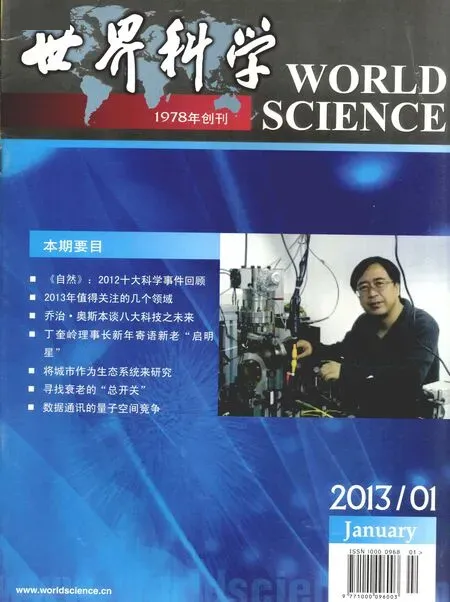科學家對百歲老人寄以厚望
蔡立英/編譯

厄文·卡恩(Irving Kahn)是美國華爾街最年長的證券交易人,盡管已年逾百歲高齡,仍然非常活躍,科學家希望更多人能與他媲美。
在任何一個工作日的早晨,你可能會看到卡恩正前往他在曼哈頓的辦公室,在那里他的職務是投資者和金融分析師——看似尋常,卻又非比尋常——卡恩差不多自1928年以來就一直在這一行工作了。
今年106歲高齡的卡恩是那些活到百歲以上仍能保持心智健全并且出奇健康的老人之一,這些百歲老人引起了衰老研究者們的關注。托馬斯·波爾斯(Thomas Perls)是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大學的一位老年醫學研究專家和新英格蘭百歲老人研究項目主任,他回憶起早年曾遇到過兩位百歲老人,改變了他以前對高齡老者健康狀況明顯不好的想象。當波爾斯在一個康復中心進行康復訓練時,他看到了“一位百歲老人出去后打算為每個人彈奏鋼琴;而另一個百歲老人,一個退休的裁縫正在幫人們補衣服,教別人如何縫紉,進行職業治療。”
但是研究數據日益顯示,達到如此高齡的老人正獲得 “生物學上的援助之手”。例如,波爾斯最近的研究支持了一個被稱為“發病率壓縮”的假設,這個假設是指壽命比平均壽命長得多(至少100歲)的個體趨向于能更長久地保持健康,與年齡有關的疾病比如癌癥和心血管疾病的發病時間會延遲。“這些疾病直到他們生命的大約最后5%的時間才會出現。”波爾斯說。若事實如此,那么對極其長壽現象的研究將使醫學家洞悉許多常見疾病的病理并且找到與之對抗的新方法。
抵抗衰老的“盔甲”
評估遺傳對普通人群健康衰老之貢獻的很多重要研究都是在斯堪的納維亞做的,那里有和平的政治環境和完善的社會基礎設施,使其他地方的那些過早縮短人壽命的外部因素的影響最小化。“過去100年來,我們基本上達到了研究人類的實驗室條件。”卡里·克里斯坦森(Kaare Christensen)開玩笑說,他是歐登塞的南丹麥大學的一位專門從事人類衰老研究的遺傳流行病學家。克里斯坦森從異卵和同卵雙胞胎的研究中發現,大約25%的長壽可歸因于遺傳因素。而且,他懷疑這種遺傳貢獻有一種明確的年齡依賴關系。“在60歲以前,遺傳因素在我們研究過的人群中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因素,”克里斯坦森說,“但是60歲以后,遺傳因素的影響會增加,而且在非常高的年齡則似乎變成最強的因素。”換句話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環境對于大多數人是否能活到70歲是關鍵的決定因素,但是70歲之后能否長壽就日益取決于他們的基因了。

然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并不是對于每個想長壽的人而言都是必須的。許多研究衰老的專家現在相信那些百歲老人擁有有益的遺傳因素能保護他們歷經生命中的衰老變遷。唯有超過了一定年齡——當不太幸運的人的健康開始衰退時——這些遺傳因素才顯現出來。
紐約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的老年醫學專家尼爾·巴爾齊萊(Nir Barzilai)是這個領域的重要研究者。他對一大群德系猶太人進行了很多年的跟蹤研究,試圖理解是什么使極其高齡者與他們的同輩區別開來。“我們研究了2 500人,年齡分布在60歲到112歲之間,其中年齡在95歲以上者有將近600人。”巴爾齊萊說。他的目標是找出那些在最老的人群里比在那些只活到平均壽命的人身上更常見的基因組變量。“大多數基因型在頻率上并不發生改變,因為它們與壽命無關,”他說,“因此,那些頻率確實會發生變化的基因型要么因為它們殺死人類而下降,要么因為它們促進長壽而上升。”
有人可能會期望這些“長壽基因型”是完美切合健康的,即沒有與增加疾病風險有關的變量。但是若干研究結果表明事實并非如此。例如,“萊頓長壽研究”發現一群90多歲老人的基因組與一群作為控制組的年輕人的基因組一樣,可能包含導致癌癥、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同樣的風險因素。這意味著長壽基因組中的其他變量以某種方式使它們的主人免受那些潛在的有害基因的影響——克里斯坦森在家族研究中也觀察到了這種影響。“在丹麥,我們發現長壽者的孩子與其他人相比罹患癌癥的概率要小25%。”對巴爾齊萊而言,像這種模式表明了極其高壽者的基因組可能為臨床醫學研究者理解健康如何隨著時間惡化提供指導。“真正控制我們的衰老速度的,”他說,“是保護機制和保護基因。”
搜尋開始
對于大多數具有遺傳因素的疾病而言,搜尋起作用的基因是以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WAS)的方式進行的。這本質上是一種對個體變量——單核苷酸多態性(SNPs)的摸底調查——這在具有感興趣的性狀的個體上和在控制組的個體上,從統計上而言是差不多相同的。但是,為了避免給研究者帶來錯誤的有利結果,研究者為目標結果設置了一個很高的門檻。而且,要發現罕見因素或是作用不大的因素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在一個大樣本研究中可能呈現為噪音。“一個單一的遺傳變量或者甚至是一組遺傳變量有足夠大的影響在全基因組關聯研究中脫穎而出,獨立地與長壽有關,是非常不可能的。”波爾斯說。
為了避開這個問題,波爾斯和他在波士頓大學的同事保拉·塞巴斯蒂亞尼(Paola Sebastiani)開展了一種不同的全基因組關聯研究。他們并不是關注個體的SNPs,而是關注群體的SNPs,尋找似乎在長壽個體中發揮協同作用的遺傳變量,這些遺傳變量受個體差異的影響很微弱。這些單核苷酸多態性群體可能后來會顯露對基因組的依賴性——一定是一起起作用的一組變量——這就建立了一個保護性的有利于長壽的生物環境。波爾斯和塞巴斯蒂亞尼發現了許多這種“指紋”,但是他們2010年的論文卻在一年后被《科學》雜志撤銷了,因為技術錯誤使他們的分析受到了質疑。波爾斯和塞巴斯蒂亞尼研究組與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的耶魯大學遺傳流行病學家合作解決了這些技術問題,并在2012年的《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上重新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波爾斯承認論文撤銷給他們的研究籠罩上了一層陰霾,但是他支持他的研究組的發現:一組281個單核苷酸多態性與至少130個在百歲老人身上似乎顯著富集的基因有關。“有一組遺傳變量一起很可能互相影響并與環境相互作用對這些極其長壽者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波爾斯補充道,“隨著研究對象的年齡越高,這個研究模型的準確性也變得越高。”

那些活到很老而仍然享受健康的人可能有遺傳優勢
這項研究中發現的若干基因在動物研究模型中也出現了。確實,動物研究的數據大體上在揭示人類遺傳變量與健康衰老的關系上比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WAS)更為有效。在人類研究中一個復現率最高的關聯基因是一個叫做E4的載脂蛋白E基因,它并不與長壽有關,而是與虛弱有關——不可理解的是這個遺傳變量極大地增加了罹患老年癡呆癥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但是,有些研究者單純地把它視為一個疾病風險因素,并不情愿稱其為一個真正的“衰老基因”。至于衰老基因,基因中的遺傳變量編碼了一個被稱為叉頭框O3A(FOXO3A)的調節因素——是人類身上與調節蠕蟲壽命的基因daf-16作用相當的基因——一而再再而三地與各種人群的壽命有關。“這個基因在漢族中國人、日本人、德系猶太人、南歐人和德國人身上都一再復現,”德國基爾的克里斯蒂安-阿爾布雷希特大學的健康衰老研究組的負責人斯蒂芬·施雷伯(Stefan Schreiber)如是說,“這意味著遺傳變量的起源一定非常古老。”FOXO3A是控制生長和新陳代謝活動的一組信號通路的一部分。在進一步支持新陳代謝通路對衰老的重要性的研究中,巴爾齊萊在德系猶太人中也發現了相似的結果。尤其是,他找到了在基因中編碼了參與類脂化合物代謝作用的降低功能性膽固醇酯酶轉運蛋白(CETP)和載脂蛋白 C3(APOC3)含量的兩種蛋白質的遺傳變量。“它們看起來發揮了長壽基因的作用——這些變量在60歲老人中的復現頻率是8%-10%,在百歲老人中的復現頻率則大概是20%。”巴爾齊萊說。
然而,百歲老人的研究困難重重。例如,這里有一個控制組的問題:百歲老人經歷了環境和生活的諸多變化,這些并不一定和現代人群相匹配。“如果你研究1910年出生的百歲老人,實際上你需要的研究人群是那些同樣在1910年出生并且50歲時去世的個體,而要做這種研究幾乎很少甚至根本沒有可獲取的DNA。”尼古拉斯·朔爾克(Nicholas Schork)說,他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圣地亞哥市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一位生物信息學家。另一方面,當代醫療手段和飲食的極大改善意味著成為控制組的人群中可能隱藏著秘密的百歲老人——那些有著普通的基因型在今天可以活到百歲高齡而在條件艱苦的年代本來很可能更早就去世的幸運者。“我打賭,控制組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將活到非常老,”波爾斯說,“但是實際上可能有比以前我們想象的還要多的人能活到100歲。”
超級老,超級健康
研究者們正在制定更加精明的策略來找出支持長壽的生物學因素。施雷伯的研究組就是開始關注 “超級百歲老人”——那些活到110歲高齡的稀有個體的研究者之一。“我們正開始研究極其長壽者,并且運用我們所有的基因組和基因研究工具以真正深入地進行探索。”施雷伯說道。他提到他已經成功運用這種方法研究克羅恩病:通過專注于研究那些在極小的年紀就患克羅恩病的孩子,他發現了若干致病的遺傳因素。
另一種方法是寄希望于發病率壓縮模型,關注那些“生物學意義上很年輕”的80多歲和90多歲的個體。朔爾克參與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威爾德利研究就是這種研究思路。“如果有些人80歲了還像50歲的人一樣健康,那么研究他們能夠為我們研究是什么原因使人們長壽提供線索。”他說。
至于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WAS),從人群中找出可能的長壽基因的困難一部分來自于科學家撒的網太廣了。考慮到長壽基因的大部分好處可能是在我們養育子女之后才發揮作用,那么這些遺傳變量很可能缺乏進行擴散的進化動力,而只是作為“傳家寶”從父母傳給孩子。這當然有事實依據——例如,卡恩的三個兄弟全都活到了100歲以上。因此,若干研究組和團隊工作,比如受到美國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美國國立老化研究所(NIA)支持的多國長壽家族研究項目,正在試圖更好地掌握這種家族遺傳關系。“我們正在研究長壽者密集的家族,我們用他們的配偶作為控制組,”克里斯坦森說,他是這個研究項目的研究者之一,“我們對這些個體進行了全基因組關聯研究,現在我們進入到測序階段。”
隨著測序技術變得越來越便宜和越來越強大,它有可能成為遺傳研究領域的一項關鍵技術。“我認為直到我們能分析和破譯我們的百歲老人的全部基因組序列,才會有重大進展。”朔爾克說。巴爾齊萊早就對這個方法感興趣了:他的研究組提議資助對百歲老人進行全基因組測序,卻未能得到NIH的支持,但是最終卻為他們贏得執政官基因組X獎奠定了基礎。這個競賽將獎勵能夠為百歲老人志愿者(被稱為“百個百歲老人”)進行最快最好最便宜的測序的基因測序團隊一千萬美元的獎金。這個測序努力繼續得到了來自巴爾齊萊和波爾斯的支持,這兩位科學家都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一百個人并不是一個足夠大的研究樣本,”波爾斯說,“但是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了不起的一步。”
但是,巴爾齊萊告誡不要把遺傳分析本身視為研究的終點。他想看到遺傳變量是如何轉化成生理影響的,比如一個人的新陳代謝指標的變化直接反映了他們的健康狀況。“譬如測量血液中的某樣東西,然后就能告訴我們疾病是否與之有關。”他說。他指出盡管在不同的基因中可能有很多遺傳變量,但是它們可能都產生延長壽命的相同結果。“我們的所有研究結果都與某種表型有關,”巴爾齊萊說,“功能性膽固醇酯酶轉運蛋白 (CETP)的表型是CETP的含量降低,載脂蛋白C3(APOC3)的表型是APOC3含量降低。它們兩者的表型則是膽固醇含量發生變化。”他進一步提出盡管在若干遺傳學研究中,FOXO3A的遺傳變量都與長壽有關,但是它們的生理影響還有待揭示。
幸運的是,還有許多其他的可能,對老人的健康進行縱向研究能提供與基因型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的表型數據。這包括了兩項從2000年開始在舊金山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進行的骨質疏松癥研究,其中一項關注男人,另一項關注女人。“那些研究對象中許多人已經去世了,因為他們活到了70多歲和80多歲,”波爾斯說。“但是他們碰巧與我們的百歲老人的孩子們差不多是同一時期出生的,而這些百歲老人的孩子們絕大部分都還活著。”
盡管有這么多困難,歐洲和美國的研究者們都還受限于缺乏對長壽研究的資助。例如,受到NIA支助的長壽研究聯盟,開展了許多關于人類老齡化的遺傳研究,卻僅僅依靠有限的并且在縮減的預算運轉著,朔爾克說。另一方面,這個領域從NIH前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 (Francis Collins)那里獲得了有力的支持。柯林斯是NIH的基因科學興趣小組背后的推動力量,這個小組把衰老設想成許多疾病之間的一個重要聯系。根據這個觀點,理解衰老可能指示了治療或者預防一些被證明除此以外很難克服的疾病的一個切入點,比如老年癡呆癥和心血管疾病。“你體內有比你實際得病還要多的疾病遺傳易感性——因此使一種疾病顯現或是保護你的遺傳機制就變得極為重要了,”施雷伯說,“研究長壽就是探究這種遺傳機制的一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