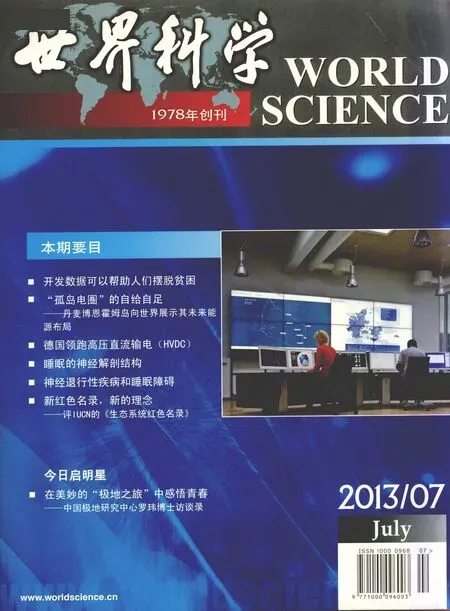情緒障礙在夜晚滋生
劉珈辰/編譯

唐·霍爾,PTSD患者,1968年參加越戰
●缺乏睡眠和情緒障礙之間的因果關系仍朦朧不解。但有一點清晰如晝:更好的睡眠能夠助益于心理健康。
在精神科醫生穆雷·拉斯金德(Murray Raskind)沒有窗戶的小辦公室中,幾份病人的個人檔案中有一張泛黃的照片,上面是一名年輕的軍人。他蜷縮在地上,靠著步槍支撐身體,看向照相機的眼神迷離無神。這是一名因戰斗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士兵肖像。
照片中的人叫唐·霍爾(Don Hall),參加了1968年越戰中非常殘酷的新年攻勢戰役。穆雷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接診他時,霍爾正被夢魘困擾,腦中夜夜如放電影一般回放昔日的戰斗經歷,他被這樣的日子折磨了近30年。“這是作戰創傷后應激障礙的標志性表現。”華盛頓西雅圖VA西北精神疾病研究、教育和臨床中心主管穆雷如是說,正是他發現了一種可以緩解這些噩夢的常見血壓藥物。
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癥狀包括憤怒和煩躁、感覺麻木和冷淡、注意力難以集中。“但是據我所知,老兵們最為擔心的問題是他們無法入睡,”拉斯金德說,“當他們經歷一個糟糕的噩夢重重的夜晚,第二天的情緒將非常低落。”
戰斗惡夢在創傷后應激障礙中的作用極具戲劇性,但睡眠異常幾乎與所有的情緒和焦慮癥都相關。抑郁癥常常會導致失眠,有時也存在睡眠時間過長以及起床障礙。躁狂發作期間,大部分人存在兩極化表現,高能量的狂熱憤怒與抑郁交替發作,看起來似乎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可以連續幾天只睡幾個小時。
睡眠干擾是如此常見以至于成為了這些疾病的診斷標準的組成部分。“情緒失調和睡眠障礙一直長期共存。”伯克利加州大學睡眠研究者馬修·沃克(Matthew Walker)說。
遇險信號
睡眠紊亂和精神疾病之間存在關聯已經非常確定,但因果關系仍不太清楚。睡眠障礙觸發這些疾病的發作,還是情緒和焦慮失控導致入睡困難?這兩者都可能存在。“這是一個雙向的通道。”沃克說。也有可能是其他一些潛在的問題在大腦中影響情緒和睡眠。
有充足的證據表明,睡眠和情緒兩者相互糾結根深蒂固。睡眠不佳的人相比睡眠很好的人更容易患抑郁。失眠往往作為抑郁癥發作的首發癥狀,也是治愈的最后一道標志。治療手段包括抗抑郁藥和心理治療,相對于同時患有失眠及抑郁的人來說療效不如僅患有抑郁癥的人顯著。
失眠往往是躁郁癥躁狂發作的一段序曲。同樣,睡眠過多也容易引起抑郁發作。一項研究發現,10%的病人在被剝奪睡眠時,可以引發躁郁癥早期癥狀:躁狂或輕躁狂。
躁郁癥患者和他們未患病的親屬更可能是夜貓子,他們被睡眠研究者稱為“睡眠相位延遲”。這些研究表明情緒失調者有可能存在引起睡眠中斷的生理節律組成。

伴隨著生理節奏的增強,有的患者表現出季節性模式,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精神病學家露絲·本卡(Ruth Benca)說。病人在春季和秋季展現出自殺行為的高峰期,這正是白晝時長變化最快速的時段。
但是,盡管呈現極其混亂的睡眠模式,其他一些躁郁癥患者可能擁有正常的生理節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大學的心理學家埃倫·弗蘭克(Ellen Frank)說。
睡眠與情緒障礙相關的問題超越了一般的反復論證。腦電圖(EEG)研究揭示,異常不僅在這些患者的睡眠多少、何時入睡,而且與他們的大腦在睡眠過程中的運行有關。躁郁癥患者與健康人相比,更容易表現出多種異常,如在淺睡時間更經常醒來。因此,他們在最深的、稱為慢波或δ波睡眠的睡眠階段停留時間最短。“無論出于何種原因,他們的大腦似乎并不能夠產生我們認為都與睡眠恢復有關的這些δ波。”弗蘭克說。
在另一項腦電圖研究中,露絲和她的同事們發現,患有抑郁癥的人沒有顯示出預期中入睡之前和之后與慢波睡眠有關的數據變化。大腦對聲音的電反應,被稱為聽覺誘發電位,通常是睡覺時比清醒時大,但那些患有抑郁癥的人不顯示這種趨勢。“抑郁癥患者相比對照組,不進行夜間和早晨的重新設定。”本卡說。
這一發現是驚人的,她補充說,因為這項研究的參與者沒有嚴重的失眠。但是露絲注意到,這些異常可能與白天的情緒障礙有關,也可能無關。也許只需除去白天的變量和干擾,就能夠全面揭示有情緒失調者的大腦功能與其他人有何不同。
負面形象
為了要理清這些關系,科學家們探測了睡眠和情緒狀態之間相關的神經基礎。第一批研究中,沃克和他的同事們進行了對健康成人的腦部掃描。其中一些人得到很好的休息,而其他人保持清醒35小時。那些保持清醒35小時的人觀看了中性乃至殘酷和不愉快的圖像,如肢解的尸體和患腫瘤的兒童。
“當你把一個健康大腦中的睡眠抽走,可以產生看起來和一些精神疾病沒有什么不同的大腦活動模式。”沃克說。情緒障礙也發現了類似的杏仁核的過度活動,沃克的實驗室未發表的數據表明,缺乏睡眠的大腦可以模仿出一些焦慮癥患者的活動進程。
荒謬的是,當一些抑郁癥患者減少了一晚上的睡眠,第二天癥狀會減輕,出現抗抑郁作用。它被認為是睡眠剝奪抑制了大腦前扣帶皮層的多余的活動,這是抑郁癥特有的特征。一旦他們能夠再次入睡,抑郁癥將又一次出現,所以睡眠剝奪并不是一個可行的治療。但這一發現推進了哪些類型的睡眠參與了這個進程的研究。
一些證據指向快速眼動(REM)睡眠。例如,三環類抗抑郁藥的工作機制被認為是擾亂REM睡眠。在某些情況下,一種抗抑郁藥的療效與它抑制REM睡眠程度相關,露絲說。但是這可能不是問題的全部。露絲的研究小組表示,在深睡眠階段干擾慢波產生的能力有抗抑郁的作用。
來自沃克實驗室的研究表明了這種影響可能的機制。他們發現,當健康但睡眠不足的人查看了一系列的中性或積極的影像,他們作出比睡眠充足的人更積極的圖像分類,他們還表現出更大的中腦邊緣大腦活動。這一大腦網絡被認為與獎勵有關,表明缺乏睡眠會增加大腦快樂中心的活動。這些結果與沃克早期關于他過度疲勞志愿者研究的負面形象相反:睡眠剝奪增加了研究者們所說的“情緒反應”。
隔夜療法
睡眠和情緒之間的因果關系尚未明確,但接受治療的含義是:讓人們睡得更好。“這些睡眠問題具有非常大的可修改性。”伯克利加州大學臨床心理學家艾莉森·哈維(Allison Harvey)說,“簡單但有力的修正行為可以對睡眠和情緒障礙產生相當驚人的改善。”
例如,弗蘭克和她的同事們已經開發出一種方法來治療躁郁癥,他們鼓勵患者保持規律的日常時間表:起床、吃飯、社交和睡眠。弗蘭克說,這種方法“似乎可以預防新的躁郁癥發作,可以更迅速地幫助人們走出抑郁癥。”這是特別重要的,她補充說,因為雖然藥物可以控制躁狂癥,但躁郁癥更不容易控制。
哈維和她的同事們已開始應用類似的理論治療抑郁癥。她未公布的數據表明,參與輔導的患者的睡眠狀態是不太可能有抑郁癥復發的。另一組表明,使用認知行為療法治療失眠,提高了治療的有效性。
沃克提及以“隔夜療法”模式控制睡眠。在大多數夢發生的REM睡眠階段,大腦停止產生去甲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是大腦的一種應激激素腎上腺素,所以其在REM睡眠時的缺失創建了一個舒緩神經的環境,使大腦能夠處理激動事件。“本質上,它解決了這些情感波動的刺激面。”沃克說。
正是這個過程出了差錯,他認為,PTSD患者有過多的去甲腎上腺素和過少的REM睡眠。有趣的是,治療創傷型噩夢時,穆雷發現,血壓藥哌唑嗪的反應區在大腦的去甲腎上腺素受體區。
服用哌唑嗪兩三周后,霍爾告訴穆雷在越南服役以來第一次睡了整個晚上。“我想,伙計,我不知道原來我是這樣一個很好的心理治療師,”穆雷回憶,“我肯定這是一種安慰劑效應。”但當穆雷的第二個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的越戰老兵患者服用藥物后,他的夢魘情況也趨于樂觀。此后,隨機試驗表明,哌唑嗪可減少創傷惡夢、改善睡眠,并在戰斗中減少創傷后應激障礙等癥狀。約70 000名美國越戰退伍軍人正在使用這一藥物。
穆雷的報告表明,只要霍爾繼續服用哌唑嗪,他的夢魘就可以被控制住。穆雷放在他的辦公室的另一張照片是霍爾最近的婚禮,人看起來老但非常平靜:一個良好的夜間睡眠的作用可以重繪心靈的肖像。“他看起來好了很多,他緊鎖的眉頭也已經展開了,”穆雷說,“注意眉頭的差別——這是哌唑嗪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