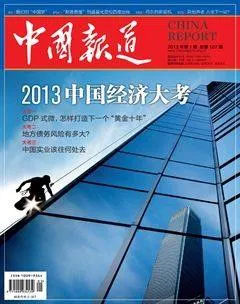收入翻番關鍵在于均衡的倍增
張茉楠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何時出臺備受公眾的關注,問題的關鍵在于“國民收入倍增”應是均衡的倍增,“倍增”的收入應是均衡的可支配收入。

根據數據顯示,城鎮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1985年時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時的9.2倍,而目前這一收入差已達到20倍之多。
近日,有最新消息稱,原計劃在2012年12月底出臺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將再度延期。收入差距擴大一直刺痛著公眾的敏感神經,而公眾對于改革方案的出臺更是望眼欲穿。關于收入分配的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十八大報告中,關于“兩個翻番”的介紹無疑是對國民信心的最大提振。其中,涉及居民收入方面,報告提出“要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確保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是中央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長量化指標,也被稱為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從定性目標到定量目標,尋求經濟增長與福利增長、財富增長與財富分配之間的平衡,其所具有的里程碑意義不言而喻。
中國版“國民收入倍增”
十年內國內生產總值(GDP)翻一番的目標并非遙不可及。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0年中國GDP為397983億元,翻番即達到79596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以2010年為基數,如果GDP在十年內保持7.1%的增速,基本能夠完成目標。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國民收入倍增”應是均衡的倍增,“倍增”的收入應是均衡的可支配收入。
根據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庇古的福利經濟學觀點,要實現更大的社會福利必須增加國民收入,同時在分配方面必須消除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在效率原則下,均等固然不可能實現,但均等化過程將必然裨益于居民收入的提升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
中國歷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訓,雖然絕對的平均主義并不切合實際,但是縮減貧富差距、實現國民收入合理分配已經成為一個現實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是指全體人民人均收入翻一番,而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只能力爭大多數人收入有大幅度增加。并且,尤其要保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幅高于高收入者,勞動報酬增速快于資本所得,徹底扭轉要素分配不公平問題,在市場內部實現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這也是為了落實“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的要求。
其實,包含實現“兩個同步”和提高“兩個比重”在內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人們最期盼的重大改革。不過,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初次分配的收入調節,還涉及二次分配的財富分配調節。
失衡的財富分配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近十年我國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目前,中國基尼系數為0.5以上,已超過了國際上慣例的警戒線。
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定量測定收入分配的差異程度。其值在0和1之間。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趨向不平等。按照國際一般標準,0.4以上的基尼系數表示收入差距較大。當基尼系數達到0.6時,則表示收入懸殊。
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調查數據也同樣驗證了我國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現狀。根據數據顯示,城鎮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1985年時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時的9.2倍,而目前這一收入差已達到20倍之多,貧富分化擴大造成中國社會“兩頭大、中間小”的塌陷。
應該講,當前中國財富分配失衡的程度要遠遠大于收入分配的失衡。中國財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長,是全球平均增速的兩倍。
事實上,如果真正按照市場經濟“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收入自然會有差距,絕大多數人對此坦然接受。人們不滿的主要是體制機制漏洞導致的不合理差距:市場準入機會不均等,壟斷部門坐享厚利,行政壟斷大量滋生“灰色收入”。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國民經濟的“蛋糕”越做越大,一方面市場化正在加速,另一方面原有的權力體系也更加強化,某種程度的政府干預、權力尋租、資源壟斷正成為固化的權力體系。馬克思曾經使用“超經濟強制”這一概念來描述政治權力濫用對分配關系的負面影響。在政治性權力介入經濟活動后,經濟活動就背離了一般的經濟運行規律,掌握政治資源的一方在宏觀經濟資源配置和微觀交易行為中獲得優勢地位,造成“權力統治財產”的現象。
固化的權力體系是中國經濟社會矛盾的直接誘因,分配失衡、資源錯配、價格扭曲……讓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信號失靈。我國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許多不合理的收入擴大因素,最為突出的是各種形式的壟斷。那些掌握著壟斷性特權、壟斷性資源的人迅速聚斂了大量的財富。行政權力本身也是一種公共資源。
相關測算顯示,2008年城鎮居民被統計遺漏的“隱性收入”高達9.26萬億元,其中5.4萬億元是“灰色收入”。
財富分配的失衡會比一般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危害更大,因為它不僅進一步擴大了不同收入階層在財富創造和財富積累上的差距,即所謂的“馬太效應”,并將通過代際之間的財富轉移,強化代際之間的“分配不公”。貧富差距越大,經濟將越發依賴資本積累和投資,而消費將被邊緣化,最終導致資產投資泡沫。
來自于《圣經·馬太福音》中的一句話,被社會學家羅伯特·莫頓采用,指任何個體、群體或地區,一旦在某一個方面(如金錢、名譽、地位等)獲得成功和進步,就會產生一種積累優勢,有更多的機會取得更大的成功和進步。此術語后為經濟學界所借用,反映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贏家通吃的經濟學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
如何改革?
如何避免分配失衡的“馬太效應”不斷累積?中國的確需要更大的制度性改革,不過所有的改革都是一種利益的調整,會觸及重重積弊,這絕對是一項復雜而艱難的系統工程。
提高勞動報酬比重,扭轉初次分配失衡。政府和居民、企業之間的收入分配造成的扭曲,可能是結構問題中非常重要的根源。當前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過程中,較強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稅收比的高比重;而當前企業的高利潤是源于很多企業的壟斷利潤。中國產業呈現出超重化工化和資本密集化,必然使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來越偏向于政府和資本,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
近十年來,我國宏觀經濟總量持續高增長,但是勞動報酬占GDP份額卻呈現下降趨勢。1997年至2007年我國勞動報酬占GDP份額從52.7%下降到39.74%,下降了近13個百分點。而2007年,美國勞動報酬占比為55.81%,瑞士為62.4%,德國為48.8%,南非為68.25%。2006年,韓國勞動報酬占比為45.4%,俄羅斯為44.55%,巴西為40.91%,印度為28.07%。我國不僅低于所有發達國家,在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也處于較低水平。因此,政府只有通過大幅減少宏觀稅負以及建立國企分配制度和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等措施,才能實現利益的重新分配。
要從根本上遏制尋租收入和壟斷性收入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只有起點公平和過程公平才能保證最后的分配公平。一直以來,金融、電信、電力等壟斷行業的高收入備受公眾詬病,并成為分配制度改革中非常大的一道阻力。在我國初次分配中,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已擴大到15倍。因此,必須加快壟斷行業收入分配改革,對部分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實行雙重調控,縮小行業間工資差距。
要在收入穩定增長機制方面,將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視為有機整體,強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國再分配機制的“逆向調節”問題較為突出,所以深層次改革不僅需要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入手,還要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包括“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和稅制的改革,實施“調高、擴中、提低”的戰略,以擴大中產階級的比重。
要強化稅收對貧富差距的調節機制。2011年,調高個稅起征點的稅收改革已經啟動,但這只是調整收入分配,還需要建立更加完備的財產稅收調節體系。發達國家主要依賴稅收對財富分配的糾偏機制,遺產稅、不動產稅、固定資產稅等對財富分配的調節稅收體系已經相當成熟,世界上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住房征收房產稅,把房產稅作為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重要工具。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房產稅在扭轉財富分配失衡方面將發揮更大的杠桿作用。
要通過財政支出的擴大提高社會整體的福利水平。與國際比較,我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長期偏低。社會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費是政府最主要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在30%左右。據統計,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各主要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的國民福利開支一般占本國政府總支出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而相比之下我國財政支出中的社保支出、醫療衛生支出、教育支出還有一定差距。
因此,政府和社會要提供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各種公共產品的服務來彌補貧富差距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要改變對公共產品提供的優先次序,加大教育制度、就業制度以及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構建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為低收入階層提供有效的向上流動的機會。

2008年部分發達國家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與我國的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