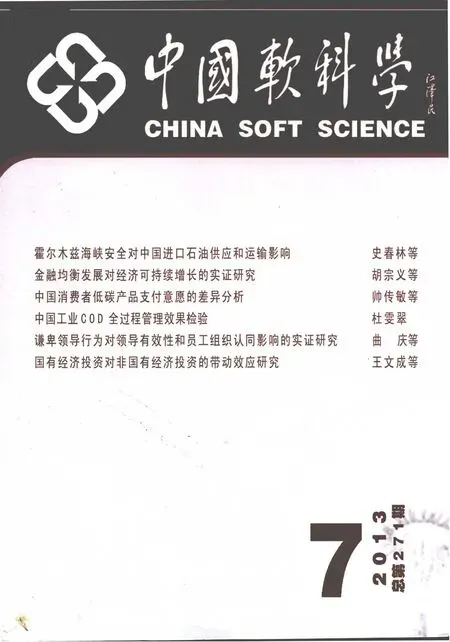考慮技術效率的碳排放驅動因素研究
檀勤良,張興平,魏詠梅,許倩楠
(華北電力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北京 102206;北京能源發展研究基地,北京 102206)
考慮技術效率的碳排放驅動因素研究
檀勤良,張興平,魏詠梅,許倩楠
(華北電力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北京 102206;北京能源發展研究基地,北京 102206)
利用距離函數和數據包絡分析法測度要素相對效率,在此基礎上構建了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該模型可以從13個方面來分析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因素。實證研究表明,7個因素導致中國碳排放的減少,尤其是能源強度的降低和能源利用技術水平的提高。其余6個因素導致中國碳排放增加,尤其是人均資本的變化和資本技術效率的降低。
碳排放;距離函數;數據包絡;因素分解
一、引言
二氧化碳排放對全球氣候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許多學者利用因素分解方法識別引起二氧化碳排放變化的影響因素,其中指數分解(IDA)和結構分解法(SDA)是兩種最常用的方法,被大量應用在碳排放驅動力的研究中,如表1。SDA以投入產出模型為基礎,因而數據的收集依賴于能否獲得投入產出表。事實上投入產出表不是每年都編制,因而SDA的應用收到了限制。IDA以指數理論為基礎,一般只需要部門數據,數據的收集相對于結構分解法比較容易;同時在分解過程中可以采用加法和乘法的形式,因而在應用中更加靈活。由于迪氏對數指數分解模型(LMDI)有效地解決了分解中的剩余問題和數據中的零值問題,因而得到了大量的應用。對我國碳排放進行因素分解的研究文獻見表1。

表1 碳排放因素分解方法及分解結果
近年來,一些學者利用距離函數和數據包絡分析法進行因素分解,由于這種方法建立在生產理論的基礎上,Zhou和Ang[1]稱之為基于生產理論的因素分解法 (PDA)。與SDA/IDA相比,PDA方法的具有3個突出的優點:一是可以反映多種投入和產出要素技術效率對碳排放的影響;二是該方法利用總量數據就可以進行因素分解,因而數據收集更加容易;三是擁有比較好的特性:可以通過因子互換檢驗 (factor reversal test)和時間互換檢驗 (time reversal test),并能有效地解決分解中的剩余問題和零值問題。而在指數分解法中,只有LMDI和refined Laspeyres指數兩種形式可以通過全部的3個特性的檢驗。Zhou和Ang[1]為能源投入和碳排放定義了一個投入距離函數,然后構建了包括一個投入要素 (能源)和兩個產出 (GDP和CO2)的數據包絡模型,利用數據包絡模型對投入要素和碳排放的技術效率進行測算。因而可以從7個方面來分析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因素和驅動程度。其分析結果說明,減排技術變化和能源利用技術變化是導致中國碳排放減少的主要因素,樣本期內 (2002-2004)分別導致碳排放減少11.66%和8.02%。而經濟增長和碳排放技術效率變化是導致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因素,分別導致碳排放增加34.71%和21.18%;碳排放強度和碳因素的變化分別導致碳排放增長5.4%和3.14%;能源利用技術效率沒有發生變化,因而對碳排放變化沒有影響。文獻 [2]為經濟產出 (GDP)定義了一個產出距離函數,并利數據包絡模型對相關技術效率進行測算,將引起碳排放變化的因素歸納為7分方面。基于我國1991-2006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分析表明:這7個因素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存在著較大的地區差異,對不同的省份具有不同影響力。但整體上看,經濟增長是碳排放增加的關鍵因素,導致碳排放增加 11.59%;勞動-碳排放比導致碳排增長1.64%。資本-碳排放比導致了碳排放減少了3.79%,經濟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導致碳排放分別減少1.03%和1.63%。該研究成果的突出優點是可以從區域的角度來詳細分析引起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因素。
本文在Zhou和Ang[1]的基礎上,在數據包絡模型中構建多投入-多產出模型。將GDP作為期望產出,將碳排放作為非期望產出同時引入模型,因為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是同時產生的,這樣更符合實際情況。投入包括能源、資本和勞動力。構建產出距離函數衡量GDP產出的技術效率,為能源投入、資本和非期望產出構建投入型距離函數,從而衡量其技術效率。這樣將影響碳排放的因素分解為13個方面,充分揭示不同投入/產出效率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為決策者提供更詳細的信息。在實證分析中,本文選擇2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分析,主要目的是從國際角度探討引起我國碳排放變化的主要驅動力,通過國際比較,為我國的能源政策制定者提供參考。
二、研究方法
(一)距離函數及要素效率測算
Shephard距離函數被廣泛應用于相對效率評價中。在時期t,首先定義一個生產可能集:St={(xt,kt,et,ct,yt):(xt,kt,et) 能生產出(ct,yt)}。其中,xt、kt和et分別代表勞動力投入,資本投入和能源投入,ct和yt分別代表CO2排放和國內生產總值 (GDP)。
St滿足以下3條性質:



對于非期望產出,定義一個投入導向距離函數:

i=1,2,…,N為決策單元,i'為被評估單元;s,t∈ {0,T}表示不同的時期。
(二)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
對于決策單元i,從時期0到時期T的CO2排放變化可以表示為:

以時期0的生產技術為參考,在式 (5)中引入投入和產出要素效率,則CO2排放變化可以分解為9個部分:

式 (6)將引起碳排放變化的因素分為九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潛在的碳因素變化 (PCFCH0i)。碳排放與能源消費的比值被稱為碳因素,在本部分中,利用碳排放效率對碳排放進行調整。從時期0到時期T,如果碳排放效率提高將導致潛在的碳因素變化加大,從而碳因素變化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將增大。相反,如果碳排放效率降低將導致潛在的碳因素變化變小,從而碳因素變化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也將減弱。第二部分,由于能源強度被能源使用效率調整,因而可以解釋為潛在的能源強度變化 (PEICH0i)。從時期0到時期T的能源消耗效率的提高將導致潛在能源強度變化加大,因此能源強度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也將加大。相反,從時期0到時期T的能源消耗效率的降低將導致潛在能源強度變化減少,從而能源強度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也將變小。第三部分為潛在單位資本產出變化 (PGGCH0i)。利用GDP產出效率對GDP進行了調整,從時期0到時期T的GDP產出效率的提高將導致潛在單位資本產出變化加大,因而資本產出變化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將加大。反之,從時期0到時期T的GDP產出效率的降低將導致潛在單位資本產出變化減小,因而資本產出變化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也將變小。第四部分可以解釋為潛在的人均資本變化 (PGPCH0i)。利用資本效率對人均資本進行了調整,從時期0到時期T,如果資本的效率提高,將導致潛在的人均資本變化加大,因而人均資本的變化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也將加大。相反,如果資本的效率降低,將導致潛在人均資本變化減小,因而人均資本的變化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也將減小。第五部分為人口變化(PCH0i),反映人口變化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第六、七、八、九部分是測量投入或產出效率變化的因素,可以分別解釋為碳排放效率變化 (CETECH0i)、能源利用效率變化 (EUTECH0i)、資本利用效率變化 (KUTECH0i)和經濟產出效率變化(TFPCH0i)。如果所有的投入、產出的效率都等于1,則式 (6)就是式 (5)。
式 (6)可以表示為:

如果用時期T的生產技術作參考,類似式(7),碳排放變化可以分解為:

根據F?re等[17]的思路,為避免時期選擇的隨意性,取式 (7)和式 (8)的幾何平均數,則碳排放變化可以分解為:


式 (9)可以表示為:

F?re等[17]利用距離函數將效率的變化分解為技術效率變化和技術變化。類似地,可以將式 (9)的最后四個Malmquist指數進一步分解為:

式 (11)右邊第一個因素測量CO2排放技術效率變化 (CEECHi),第二個因素為碳排放技術變化(CATCHi)。式 (12)右邊的第一個因素測量能源消耗技術效率變化 (EUECHi),第二個因素為能源使用技術水平變化 (EUTCHi)。式 (13)右邊的第一個因素測量資本技術效率變化 (KUECHi),第二個因素為資本技術變革 (KUTCHi)。式 (14)右邊的第一個因素測量GDP生產技術效率變化 (TFECHi),第二個因素為GDP生產技術變革 (TFTCHi)。
綜上所述,碳排放變化可以分解為13個因素,如式 (15)。這13個因素可以從五個方面反映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力:經濟效應、技術效應、效率效應、結構效應和人口效應。其中,經濟效應是指由于經濟增長導致碳排放的變化,用潛在的資本產出變化 (PGGCH)和人均資本變化(PGPCH)來反映。技術效應主要是指技術水平變化對碳排放變化的影響,包括能源利用技術水平變化 (EUTCH)、GDP生產技術水平變化(TFTCH)、減排技術水平 (CATCH)和資本技術水平的變化 (KUTCH)。效率效應主要是指由于效率改變導致的碳排放變化的影響,包括:能源使用技術效率變化 (EUECH)、資本技術效率變化 (KUECH)、碳排放技術效率變化 (CEECH)、GDP生產技術效率變化 (TFECH)和潛在的能源強度變化 (PEICH)。結構效應主要反映能源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用潛在的碳因素變化 (PCFCH)衡量。人口效應主要是衡量人口變化(PCH)對碳排放的影響。

三、實證分析
本文選擇包括中國在內的20個發展中國家作為研究樣本,由于樣本數據的可得性,樣本期為2004-2009。以能源消費、資本和勞動力作為投入,國內生產總值 (GDP)和CO2排放量為產出。數據來源于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為了使數據保持一致,價值型數據都以2000年不變價格折算。應用模型 (15),20個發展中國家2004-2009年期間碳排放因素分解結果如表2。

表2 20個發展中國家2004-2009年期間碳排放因素分解結果
首先,將20個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在2004-2009年碳排放平均增長22.17%。其中,肯尼亞、中國、印度、玻利維亞和巴拿馬碳排放增長比較快,增幅均超過40%。多米尼加、洪都拉斯、斯里蘭卡和菲律賓的碳排放只有微小的增加,而贊比亞的碳排放有所降低。總體上看,導致碳排放減少的驅動因素包括5個:潛在的資本產出變化 (PGGCH)、潛在的能源強度變化 (PEICH)、減排技術水平 (CATCH)、GDP生產技術水平的變化 (TFTCH)和碳排放技術效率變化 (CEECH)。這些因素導致碳排放減少的比例分別為:14.08%,5.24%,4.4%,1.79%,0.84%。結果表明,20個發展中國家整體上的技術水平在提高,尤其是GDP生產技術水平,從而資本產出水平大幅度提高,能源強度有了明顯的降低。相反,潛在的人均資本變化 (PGPCH)、潛在的碳因素變化 (PCFCH)、人口變化(PCH)、資本技術效率變化 (KUECH)、資本技術水平變化 (KUTCH)、生產技術效率變化(TFECH)、能源使用技術效率變化 (EUECH)和能源利用技術水平變化 (EUTCH)8個因素是碳排放增加的驅動因素,分別導致碳排放增加比例 為:14.11%、 8.36%、 8.17%、 6.75%、3.89%、3.77%、3.08%、1.58%。因而這些國家的技術效率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提高技術水平的同時,更應該注重追趕效應。
其次,由表2也可以對每一個國家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力進行國際比較,本文以中國為例。中國2004-2009年間CO2排放增加了49.74%,增長率在20個國家中僅次于肯尼亞,位列第二。相對于所分析的樣本國家,導致中國碳排放減少的因素有7個。
(1)潛在的能源強度變化 (PEICH)使得我國碳排放減少11.69%,是導致我國碳排放減少的最關鍵的因素。在菲律賓、秘魯、敘利亞、贊比亞和委內瑞拉5個國家中,潛在的能源強度變化起到了更明顯的減排效應,分別使這些國家碳排放減少了 23.49%,18.18%,13.81%,11.88%和11.87。說明這些國家潛在的能源強度有更明顯的降低。相反地,該因素導致智利、厄瓜多爾、伊朗、斯里蘭卡和危地馬拉5個國家碳排放增加,說明這些國家潛在的能源強度增加比較明顯。
(2)能源利用技術水平變化 (EUTCH)導致我國碳排放減少10.09%,說明我國潛在能源利用技術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值得關注的是,能源利用技術水平變化導致菲律賓碳排放更大幅度的減少 (17.83%)。但該因素導致12個國家的碳排放增加,尤其是,導致肯尼亞碳排放增加了20.01%,說明這些國家能源利用技術水平在下降。
(3)潛在的資本產出變化 (PGGCH)使我國碳排放減少了7.06%。該因素導致19個國家碳排放減少,其中,使16個國家碳排放減少幅度超過10%,因而是絕大多數國家碳排放減少的重要驅動力。我國潛在的資本產出水平雖然有一定的提升,但相對于這16個國家而言,提升的效果很有限。
(4)GDP生產技術水平變化 (TFTCH)使我國碳排放減少了4.33%。該因素導致16個國家碳排放減少,說明這些國家技術水平得到改善。其中,該因素導致7個國家碳排放減少的幅度超過我國,尤其是,該因素導致阿根廷和玻利維亞碳排放減少的幅度超過10%,說明這兩個國家GDP生產技術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
(5)潛在的碳因素變化 (PCFCH)導致我國碳排放減少3.83%。該因素導致11個國家碳排放減少,說明這些國家單位能源的碳排放減少,能源結構得到改善。其中,該因素分別導致贊比亞、智利、玻利維亞和菲律賓碳排放減少了15.1%、8.68%、7.33% 和 6.78%,因此這些國家能源結構得到了更明顯的優化。但該因素卻導致了其他9個國家碳排放的大幅度增加,增加幅度超過了16%,說明這些國家能源更加依賴化石能源。
(6)碳排放技術效率變化 (CEECH)使我國碳排放減少了1.99%。該因素導致10個國家碳排放減少,說明這些國家的碳排放技術效率得到改善。尤其是,對阿根廷、危地馬拉、伊朗和敘利亞4個國家有更明顯的減排效應,分別達到9.43%、7.31%、6.87% 和 3.18% 的減排效果,因此這四個國家的技術效率得到了更好的提高。同時該因素導致其他9國家碳排放輕微的增加,但印度的碳排放技術效率明顯的惡化,該因素導致印度碳排放增加了10.91%。
(7)GDP生產技術效率變化 (TFECH)對減少碳排放具有積極的作用,但驅動力較弱,導致我國碳排放減少1.66%。該因素對6個國家具有減排效應,但減排效果比較小,說明這些國家的生產技術效率得到了輕微的改善。但對于其余14個國家而言,該因素導致了碳排放的增加,說明大部分國家的生產技術效率在惡化,尤其是阿根廷和玻利維亞。
其他6個因素導致了我國碳排放的增加。
(1)潛在的人均資本變化 (PGPCH)是導致我國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的驅動力。該因素導致13個國家碳排放增加,而且驅動力很強。特別地,該因素驅動肯尼亞碳排放增加88.6%;驅動我國碳排放增加59.95%,是驅動力最強的兩個國家。說明這些國家潛在的人均資本增長比較快。相反,該因素導致7個國家碳排放減少,說明這些國家潛在的人均資本減少。
(2)資本技術效率變化 (KUECH)導致我國碳排放增加了10.78%。該因素導致13個國家碳排放增加,意味著這些國家資本技術效率在惡化,尤其是阿根廷等7個國家,該因素導致碳排放的增加超出了我國,這7個國家資本技術效率下降的程度比我國嚴重。相反,該因素導致了6個國家碳排放減少,說明這些國家資本技術效率提高了。
(3)資本技術水平變化 (KUTCH)導致我國碳排放增加了7.71%。該因素引起12個國家碳排放增加,說明這些國家資本技術水平在惡化。尤其是,委內瑞拉、智利、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肯尼亞5個國家,其資本技術水平下降的幅度超過了我國,引起的碳排放增加幅度超過了9%。但該因素引起了其他8個國家碳排放的減少,說明這些國家資本技術水平在提升。
(4)減排技術水平 (CATCH)引起我國碳排放10.59%的增加。該因素引起8個國家的碳排放增加,說明這些國家的減排技術水平在下降,尤其是中國和阿根廷下降的幅度超過10%。但該因素引起了其他12個國家的碳排放減少,說明這些國家的減排技術水平在提高。
(5)能源使用技術效率變化 (EUECH)使我國碳排放增加了5.53%。該因素引起了11個國家的碳排放增加,說明這些國家的能源使用技術效率在降低。尤其是,巴拉圭、巴拿馬、贊比亞、敘利亞、委內瑞拉、秘魯和菲律賓7個國家,其能源使用技術效率更加惡化,導致了這7個國家碳排放增加了10%以上。遠遠超過了我國。但對于其余9個國家而言,該因素對減排具有積極效果,說明這些國家能源使用技術效率在提高。
(6)人口變化 (PCH)使我國碳排放增加了2.73%。對于所有的樣本國家來說,人口增長都驅動碳排放增加,但其驅動力在中國是最小的,肯尼亞是最大的,該因素導致肯尼亞碳排放增加了14.04%。盡管該因素對我國碳排放增加的驅動力比較小,但由于我國城市化進程正在提速,城市人均能源消費比農村人均能源消費多1085.26千克標準煤[18],因此倡導低碳的生活理念也是我國節能減排的有效措施。
四、結論
本文利用距離函數和數據包絡分析法建立了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其突出的優點是可以分析不同投入和產出要素的技術效率變化和技術水平變化對碳排放的影響機制。該分解模型可以將影響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因素分解為13個部分,從而可以揭示經濟效應、技術效應、效率效應、結構效應和人口效應對碳排放的影響力。
本文選擇包括中國在內的2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實證研究,目的就是從國際視角來分析引起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因素。相對于所分析的樣本國家而言,驅動中國碳排放減少的主要因素歸納為3種效果:一是技術效應。我國能源利用技術水平和整體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促使了碳排放的降低;二是效率效應。主要表現為能源強度的下降、整體生產技術效率的提高、碳排放技術效率的改善;三是結構效應。可再生的清潔能源在我國得到了非常迅速的發展,因而能源結構的變化是導致我國碳排放減少的重要因素。
導致我國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可以歸納為4類:一是經濟效應: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的增長是導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動力。二是技術效應:資本的技術水平和減排技術水平不高是驅動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三是效率效應:資本的技術效率和能源使用技術效率導致了碳排放的增加。四是人口效應:人口的增長導致了碳排放的微小增長,其驅動力遠不如其他因素明顯。
這些導致中國碳排放增加的因素,也是今后我們應該加強的領域。因此今后我國節能減排的政策取向應該關注以下幾點:一是提升資本的技術效率和技術水平,這就要改變目前粗放的增長模式,不斷過渡到內涵發展的模式,提高資本的使用效率和技術水平,這對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的長效作用。二是提高能源使用技術效率和減排的技術水平,這種方式對于節能減排具有非常直接的效果。三是積極倡導低碳生活的價值觀。我國人口基數大,城市化進程快,低碳價值觀有利于降低人們生活用能,從而減少碳排放。
[1]Zhou P,Ang B W.Decomposition of Aggregate CO2Emissions:A Production-theoretical Approach [J].Energy Economics,2008,30(3):1054-1067.
[2]Li M.Decomposing the Change of CO2Emissions in China:A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 [J].Ecological Economics,2010,70(1):77-85.
[3]Zha D,Zhou D,Zhou P.Driving Forces of Residential CO2Emission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An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J].Energy Policy,2010,38(7):3377-3383.
[4]趙志耘,楊朝峰.中國碳排放驅動因素分解分析[J].中國軟科學,2012(6):175-183.
[5]Liu L,Fan Y,Wu G,et al.M.Using LMDI Method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China Industrial CO2Emissions From Final Fuel Use:An Empirical Analysis [J].Energy Policy,2007,35(11):5892-5900.
[6]徐國泉,劉則淵,姜照華.中國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實證分析:1995-2004[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6(6):158-161.
[7]王鋒,吳麗華,楊超.中國經濟發展中碳排放增長的驅動因素研究 [J].經濟研究,2010(2):123-136.
[8]宋德勇,盧忠寶.中國碳排放影響因素分解及其周期性波動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3):18-24.
[9]朱勤,彭希哲,陸志明,等.中國能源消費碳排放變化的因素分解及實證分析[J].資源科學,2009(12):2072-2079.
[10]趙奧,武春友.中國CO2排放量變化的驅動力與減排界域分析[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0(10):48-54.[11]Zhang M,Mu H,Ning Y,et al.Decomposition of Energy Related CO2Emission Over 1991-2006 in China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9,68(7):2122-2128.
[12]Yuan P,Cheng S.Determinants of Carbon Emissions Growth in China: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J].Energy Procedia,2011(5):169-175.
[13]朱勤,彭希哲,吳開亞.基于結構分解的居民消費品載能碳排放變動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2(1):65-77.
[14]Ang B W,Zhang F Q,Choi K.Factorizing Change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Through Decomposition[J].Energy,1998,23(6):489-495.
[15]Tyteca D.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Firms-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 Productive Efficiency Perspective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6,46(3):281-308.
[16]Tyteca D.Linear Programming Model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Firms-concepts and Empirical Results[J].Journal of Production Analysis,1997,8(2):183-197.
[17]F?re R,Grosskopf S,Norris M,et al.Productivity Rrowth,Technical Progress,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66-83.
[18]張馨,牛叔文,趙春升,等.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居民家庭能源消費及碳排放研究 [J].中國軟科學,2011(9):65-75
The Driving Force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Consideration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TAN Qin-liang,ZHANG Xing-ping,WEI Yong-mei,XU Qian-n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102206,China;Research Center For Beijing Energy Development,Beijing102206,China)
Based on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changes of inputs/outputs,we present a decomposition model by using distance functions an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The components driving the change of carbon emissions are decomposed into the contributors from thirteen factors specified in this paper.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seven factors decrease the carbon emissions,especially the change in energy intensity and energy utilization technical level.While the other six factors increase the carbon emissions,especially the change in capital per capita and capital technical efficiency.
Carbon emission;Distance function;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composition analysis
F407
A
1002-9753(2013)07-0154-10
2013-01-27
2013-03-28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173075);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NCET-12-0850);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20110036120013);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11JGA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基金。
檀勤良(1969-),福建福州人,華北電力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能源經濟與政策模擬。
(本文責編:海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