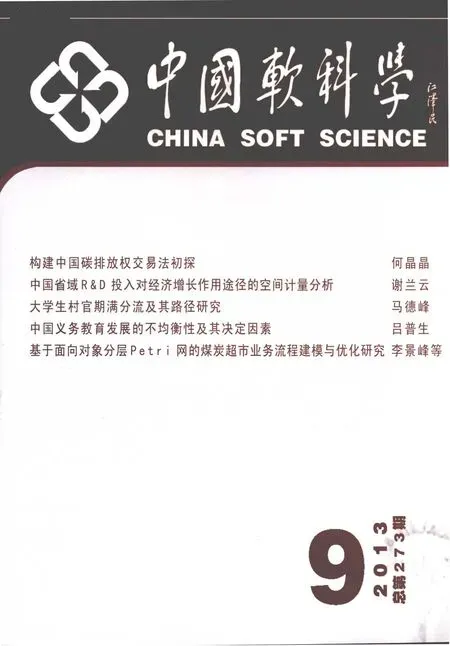中國省域R&D投入對經濟增長作用途徑的空間計量分析
謝蘭云
(東北財經大學 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中國省域R&D投入對經濟增長作用途徑的空間計量分析
謝蘭云
(東北財經大學 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本文利用我國各省份2000-2010年的面板數據,使用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研究了我國各省份R&D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途徑問題。本文首先建立了包含省份之間地理空間距離和經濟距離的空間權重矩陣,然后利用空間滯后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分別研究了R&D投入對各省份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各省份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空間相關性,從國家創新體系的角度來看,一個省份的R&D投入能夠通過四條途徑作用于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其中一條是直接影響,一條是間接影響,另外兩條是通過空間溢出形成的間接影響。
R&D投入;經濟增長;空間溢出;區域
一、引言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是有目的的研究與試驗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活動的結果,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證實了R&D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Griliches,1986[1];Aghion et al.,1992[2];朱 平 芳,1999[3]等),技術創新也由此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源泉。更進一步的,R&D產品又具有典型的公共品特征,其作用于微觀層面對區域性產業結構和總產出能夠表現出較強的外部性,并最終表現為產業的整體提升和區域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
此外,基于 Tobler地理學第一定律(Tobler,1979)[4],大量的 R&D研究較為一致性地認為,R&D投入所衍生的技術變化將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一個地區的R&D投入不僅會對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影響,而且還會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對周邊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影響(Bernardi,2007[5];項歌德等,2011[6]等)。具體到中國樣本,我國各省份由于初始資源稟賦、歷史文化條件、發展路徑和宏觀政策支持力度的差異,經濟發展表現出嚴重失衡態勢,并且這種失衡在我國長達近30年的高速增長過程中不但沒有表現出經典經濟增長理論所推論的收斂性傾向,地區差異反而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區域失衡在影響資源配置效率,造成整體經濟效率損失的同時,還衍生出諸多社會公平問題,引起社會矛盾沖突和嚴重的政治后果(胡鞍鋼等,1995[7];林毅夫等,1998[8])。考慮到美國經濟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前半葉的高速發展就部分得益于其地區間差距的縮小(Higgins,1988[9]),這實際上從理論和現實層面均提供了一個改變區域經濟失衡、保證經濟體均衡增長的現實路徑,即強調技術進步的溢出效應和后發技術優勢來彌補地區經濟增長的差異。
由此,在圍繞R&D投入和經濟增長而展開的研究中,關注R&D產品溢出效應對區域差異的影響并進而影響到整個經濟體增長表現的文獻越來越多,但是在中國問題的研究上,特別是在中國當前高度分權進而形成保護性市場分割的行政與市場架構下,一個省份的R&D投入到底會對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產生怎樣的影響,其在作用于區域內部經濟增長的同時,又是通過哪些途徑影響到相鄰區域經濟發展,市場保護會不會阻斷或限制技術溢出的實際過程?目前來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還不是很充分,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
當前進行知識溢出空間計量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研究空間距離對知識溢出 效 應 的 影 響 (Adams(2002)[10];Keller(2002)[11];符淼(2009)[12];孫建等(2011)[13]),另一方面是以專利作為R&D活動的產出成果,研究R&D活動產出的空間溢出效應(Jaffe(1989)[14];蘇方林(2006)[15];李婧等(2010)[16];項歌德等(2011))①Griliches(1990)[17]認為用專利表示技術的缺陷在于專利數本身并不體現專利的質量,也不體現專利在經濟增長中發揮多大的作用,且不是所有的發明都申請了專利,尤其是某些核心技術的擁有者為避免他人模仿而沒有注冊專利。。但是總體而言目前圍繞R&D投入對經濟增長空間溢出問題而展開的研究還存在著一定的不足。王家庭(2012)[18]分析了各因素對我國區域工業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其使用的是截面數據,這增加了結果的偶然性和隨機性。黃蘋(2008)[19]利用面板數據,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因變量,對R&D溢出與地區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空間計量分析,但其使用的是基于地理位置相鄰的空間權重矩陣,既沒有考慮到距離因素,也沒有考慮到經濟因素。本文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使用我國各省份2000-2010年的面板數據,以國內生產總值為被解釋變量,從地理距離和經濟距離兩個角度構建了空間權重矩陣,從國家創新體系的全局視角,利用空間計量理論和方法對我國各省份R&D投入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進行實證研究,從而為制定更合理的區域創新政策,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穩定發展提供更準確的依據。
二、模型的設定
(一)理論模型
Griliches(1979)[20]最早提出了利用知識生產函數研究R&D相關投入對產出的影響,此后Pakes和Griliches(1980)[21]等學者都利用知識生產函數研究過知識溢出的地理范圍問題。隨著空間計量 經 濟 學 的 發 展,Anselin(1997)[22]、Bode(2001)[23]等人利用空間計量模型研究了R&D知識生產和溢出的問題。本文依然延用傳統Cobb-Douglas生產函數的研究框架,引入R&D投入作為新的生產要素,考慮到R&D投入涉及到資金和人員投入兩個方面,改進后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形式如式(1)所示:

其中,A表示科技進步系數,代表了除物質資本、勞動投入和R&D投入之外的所有其它影響產出的因素,K表示資本要素的投入,α表示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L表示勞動要素的投入,β表示勞動投入的產出彈性,RD表示R&D資金投入,γ表示R&D資金投入的產出彈性,H表示R&D人員投入,λ表示R&D人員投入的產出彈性。將式(1)兩邊取對數,得到式(2):



設a=LnA,則一個地區的C-D生產函數可表示為式(4):

其中 i表示地區,t表示時間,yit、kit、rit分別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的勞動力人均產出、勞動力人均擁有資本、R&D活動人員人均擁有R&D資金。α、γ分別表示勞均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R&D活動人員人均R&D資金投入的產出彈性。改進后的C-D函數將原本分攤在資本和勞動要素上的科技創新要素的影響從函數中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第三要素來反映R&D投入對產出的影響。將式(4)轉換為經濟計量模型為式(5):

其中μit表示隨機誤差項。
(二)空間計量模型
空間計量經濟學的概念最早是由Paelinck在1974年提出的,此后經過眾多學者的不斷豐富,特別是Anselin等的不斷拓展,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研究體系。在利用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分析時一部分學者使用了截面數據展開,如 Anselin等(1997)、蘇方林(2006)、吳玉鳴等(2008)[24]等;但一維數據的空間模型雖簡便易行,卻僅僅用樣本考察期內某一年數據進行估計,一方面忽視了創新產出和投入之間時間上的滯后效應,另一方面也使得數據信息沒有被充分利用,增加了結果的偶然性和隨機性。由此相關研究拓展到了基于面板數據進行的分析,如 Funke M. 等(2005)[25]、黃蘋(2008)、李婧等(2010)、項歌德等(2011)等。本文基于面板數據進行空間計量分析,將包含更多的數據點,帶來更大的自由度,提高模型分析的精確度。
空間面板計量經濟模型就形式而言主要分為兩種:空間滯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和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其中空間滯后模型也稱為空間自回歸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SAM),主要探討各變量在一地區是否有擴散現象(溢出效應),其模型形式為式(6):

空間誤差模型主要用于度量鄰近地區關于因變量的誤差沖擊對本地區觀察值的影響程度,其模型形式為式(7):

其中,Y為因變量,X為n×k的外生解釋變量矩陣,ρ為空間自回歸系數,反映了樣本觀測值中的空間依賴作用,即相鄰區域的觀測值WY對本地區觀測值Y的影響方向和程度,W為n×n階的空間權重矩陣,λ為空間自相關系數,反映了樣本觀測值中的空間依賴作用,即相鄰區域的誤差Wε對本地區因變量的影響方向和程度,ε、μ均為隨機誤差項向量。由于這兩個空間計量模型都反映了地區間的空間影響,因此本文分別利用這兩個模型進行研究。
由于本研究重點考察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是否會受到來自其它地區R&D投入的影響,因此在式(5)的基礎上引入一個新的解釋變量WLnR,用于衡量其它地區R&D投入對于本地區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則式(5)的空間滯后模型為式(8),空間誤差模型為式(9):

二、變量與數據
(一)數據來源① 本文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網(www.sts.org.cn)和中經網數據庫(www.cei.gov.cn)。
由于我國公開的統計數據中關于各省R&D投入的數據是從2000年開始的,所以本文的樣本期確定為2000-2010年。在模型中,總產出使用各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并利用各地區的GDP價格指數進行平減處理后得到,勞動要素的投入量使用年底職工人數。R&D人員是指統計年度內參與研究與試驗發展項目研究、管理和輔助工作的人員投入。對于物質資本存量的測度,本文采用Goldsmith(1951)的永續盤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PIM),其基本公式為式(10):

其中 Kt為第 t年的實際資本存量,Kt-1為 t-1年的實際資本存量,Pt為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It為第t年的名義投資,δt為第t年的固定資產折舊率。
本文在計算以2000年為基年的資本存量時借鑒了張軍等(2004)[26]計算資本存量的方法,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適當的調整,如將重慶數據從四川分離出來,同時由于張軍等在進行計算時,采用了當時10%的資本增長速度,而本文的研究期間是2000-2010年,此期間的資本增長速度已經提高了1倍,因此本文使用我國各省份2000年固定資本形成額除以20%計算得到各省份2000年的固定資本存量。對于當年固定資產投資額本文選取各省份固定資產形成額數據,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使用各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在折舊率的選取時,本文沒有使用張軍等(2004)在計算各省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時采用的9.6%的折舊率,也沒有像王小魯等(2000)[27]大多數學者一樣采用5%的折舊率,而是利用全國各省份2000-2010年的折舊額進行匯總,形成全國各年份的資本折舊額,然后除以以2000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價格指數,得到不變價格的折舊額,最后利用全國的資本數據計算出2000-2010年全國的資本折舊率,取各年折舊率的平均值,得到7%的折舊率。
關于各省份R&D資本存量的計算也使用永續盤存法,參照 Griliches(1980[28],1998[29])、Goto and Suzuki(1989)[30]的方法,t期的 R&D 資本存量可以用過去所有時期的R&D支出現值與t-1期的R&D資本存量現值之和來表示。其計算公式為式(11):

其中R表示R&D資本存量,E代表 R&D支出,δ為R&D資本存量的折舊率。具體各指標的選取方法和計算參見謝蘭云(2010)[31]。
(二)經濟增長的空間相關性研究
在將空間相關性考慮到研究中進行實證分析之前,必須先進行空間檢驗。如果檢驗結果表明存在空間相關性,則將空間效應納入模型分析框架中,采用空間計量模型進行研究;反之,則可以直接利用一般估計方法,如OLS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
檢驗區域間空間相關性存在與否的方法有多種,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s I。Moran`s I主要用于全域空間相關性分析,其定義為式(12):

利用相關數據分別對我國各省份2000-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及其對數計算Moran`s I指數及其正態統計量的Z值,得到的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2000-2010年中國省域GDP及其增長率的Moran`s I指數及其Z值
表1的計算結果表明我國各省份之間無論是國內生產總值,還是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其Moran`s I指數都大于0,Moran`s I的正態統計量Z值均大于正態分布函數1%水平下臨界值1.96。這說明我國省份之間的經濟增長在空間分布上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空間依賴性),在地理空間上存在集聚現象,相鄰地區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著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忽略這種空間溢出效應將造成模型設定的偏差和計量結果的非科學性,因此,有必要使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進行相關問題的研究。
(三)空間權重矩陣的設定
空間權重矩陣的設定是進行空間計量分析的重要環節,正確的設定可以更準確地衡量這種空間溢出效應。從已有的進行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文獻可以看出,空間距離矩陣的設置方法通常有兩種,第一種是根據地區i和j之間的地理鄰接性進行定義,即:

Anselin(1995)[33]最早采用了這種設定方法,蘇方林(2006)、黃蘋(2008)、鄧明等(2009)[34]等也采用了這種方法進行空間距離矩陣的設定,這種設定方法雖然簡單,但是并不能真實反映區域創新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系與影響;第二種是基于距離的空間權值矩陣的設定方法,該方法假定空間相互作用的強度取決于地區間的質心距離或者區域行政中心所在地之間的地理空間距離,如Keller(2002)[35]、Bernardi(2007)、符淼(2009)等就使用了這種方法。
按照鄰近經濟學的觀點,經濟事物的空間聯系不僅表現為地理鄰近,更重要的是表現為組織鄰近(Organizational Proximity),即基于某一類共同或類似基準的鄰近(李婧等,2010)。因此一個地區的知識溢出對另一個地區的影響要從兩個角度進行考慮,其一是知識溢出的可能性,其二是接收知識溢出的可能性。空間依賴性指出空間上距離相近的地理事物的相似性比距離遠的事物相似性大,這種空間依賴性反映了現實中存在的空間交互作用,形成了區域間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創新的擴散和知識的溢出等,所以地理位置接近的區域較易產生知識的溢出。但另一方面,即使區域間出現知識溢出,接受溢出的一方也需要具有一定的能力才能夠將這種溢出轉化為自身的發展能力,它取決于接受溢出的一方對知識的吸收消化能力,這要受到多種要素的制約,比如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本積累、產業結構特征、社會環境甚至風俗習慣等。CASE(1993)[36]在分析美國州政府之間的政府支出溢出效應時,認為除了地理空間距離外,經濟發展水平距離也影響著這種溢出效應,因此他最早定義了一個經濟發展距離空間加權矩陣,將其引入空間計量經濟研究中。許簫迪等(2007)[37]經過實證研究表明經濟差距與知識溢出效應成反比,企業或地區之間經濟差距越大,越不利于知識吸收和相互間知識溢出。林光平等(2006)[38]、王火根等(2007)[39]等也在研究中建立了基于地區經濟發展的空間經濟距離權重矩陣。因此本文設定的空間權重矩陣由兩部分構成:空間地理距離矩陣和空間經濟距離矩陣,它既反映了知識空間溢出的可能性,也反映了這種溢出被吸收的可能性。
空間計量實證經驗表明,權重并非和距離倒數成正比關系。相關研究發現,很多空間關系的強度隨著距離的減弱程度要強于線性比例關系,因此經常采用平方距離的倒數作為權重(王遠飛等,2007)[40]。因此本文采用第二種空間距離矩陣的設定方法,并設定平方距離的倒數作為權重,如式(14)所示:

其中,dij①區域i和區域j的空間地理距離dij的計算是利用各省份省會城市的地理坐標計算其空間距離得到的。表示區域 i和區域 j的空間地理距離。
影響區域間經濟距離的因素有很多,一般來說,如果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那么其相應的人力資本積累也比較豐富,人力資本水平高可以增強對知識、技術的吸收能力以及對其它信息的獲取與運用能力,進而轉化為創新產出,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形成一種雙向的正反饋。李婧等(2010)的研究表明經濟距離權重與人力資本權重在專利模型中的估計結果相似,因此可以將問題簡化,用一個指標來建立經濟距離矩陣。反映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一般選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但是由于本文研究R&D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果選取人均GDP會與被解釋變量GDP之間存在嚴重的相關性,影響模型的估計精度,所以本文采用項歌德等(2011)在研究中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衡量區域經濟差距的指標,如式(15)所示:

其中Incomei和Incomej分別表示區域i和區域j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各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數據為各地區2000-20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WGij和WEij均為對角線數據為零的對稱矩陣,分別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使其各行的和為1,然后利用式(16)進行距離權重矩陣的設定。

在進行權重系數 α的設定時,本文利用式(17),分別對α進行從0到1、每次變化步長為0.1的測試。

其擬合結果如圖1所示。
從圖1的擬合結果可以看出,t統計量在α的變化過程中始終顯著,擬合優度在α到達0.3之后開始下降,因此本文選取α=0.3作為空間權重矩陣中地理距離矩陣的權重,即在空間權重矩陣中,地理距離矩陣的比重為30%,經濟距離矩陣的比重為70%。由此可見,R&D空間溢出效應的影響因素是以經濟發展水平的類似性因素為主導的,地理距離的影響要弱一些,這與李婧等(2010)、項歌德等(2011)的研究結果是相同的。地區之間距離近只是提供了知識溢出的可能性,要將這種可能性轉化為必然性,則要取決于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相似性。對于發達地區而言,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力資本積累能夠不斷地吸收外部的知識溢出,并產生更多的內生技術進步,促進區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落后地區由于在資金及人力資源等方面的不足,使其在對先進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等方面都受到限制,不能很好地吸收其它地區的知識溢出。因此,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力資本積累水平是影響區域技術創新的關鍵因素。

圖1 α變化的t統計量與擬合優度變化圖
三、實證研究
(一)模型估計結果
在進行面板空間計量分析時,首先對控制個體差異的變截距面板模型進行形式識別,Hausman檢驗的結果支持取固定效應模型。同時,“當截面的單元是總體的所有單位時,固定效應模型是一個適宜的模型”(吳玉鳴,2007)[41],因此,本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
研發活動的特點決定了R&D投入并不能馬上發揮作用,但其具體的滯后期數從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共識。如朱平芳等(2003)[42]在研究中選擇滯后4期,蘇方林(2006)選擇滯后1期,鄧明等(2009)選擇滯后2期等。本研究在R&D投入滯后期選取時,采用的原則是既要保證R&D投入變量在回歸中的作用是顯著的,又要盡可能使模型的自由度最大。在此利用Matlab軟件①在進行空間面板回歸時主要參考了Elhorst和LeSage等人提供的代碼(Http://www.spatial-econometrics.com)。,分別對模型(8)、(9)中的 LnR和WLnR進行了從滯后0期到滯后4期的空間回歸分析,回歸的結果顯示當LnR變量滯后一期時,無論是在SLM模型還是在SEM模型中都表現為最顯著,同時也發現WLnR變量滯后一期時,在SEM模型中表現最顯著,但無論滯后幾期該變量在SLM模型中均表現為不顯著。由此本文不僅確定了在樣本期內LnR和WLnR的滯后期均為1期,而且還發現本地區的R&D投入只會對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直接的促進作用,而不會對相鄰區域的經濟增長產生直接的促進作用②由于在SLM模型中WLnR滯后一期的回歸結果不顯著,本研究試圖將變量從模型中刪除,但是多次模擬的結果表明,如果去掉這個變量,無論是SLM模型,還是SEM模型的各項指標的估計精度均出現了下降,于是決定繼續將此指標保留在模型中。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雖然A地區的R&D投入不會直接對B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作用(SLM模型),但它會通過其它途徑以空間溢出的形式間接作用于B地區的經濟增長(SEM模型)。。其回歸的結果如表2所示③為了和空間溢出效應的模型進行對比,在此列出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的普通面板數據的回歸結果。。
從回歸的結果可以看出,使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的R2和對數似然值LogL都小于其它兩個模型,其LnK和LnL的系數均大于其它兩個模型,說明在沒有考慮空間溢出效應時,模型的回歸結果夸大了本地生產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從調整后的R2、LogL、LR等統計量來看,SLM模型和SEM模型都具有很好的擬合優度,表明這兩個模型都較好地描述了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過程。

表2 空間面板計算分析的結果①本研究分別使用無固定效應(no fixed effects)、地區固定時間不固定效應(spatial fixed effects)、時間固定地區不固定效應(time period fixed effects)和地區與時間均固定效應(spatial and time period fixed effects)對模型進行了估計,但只有地區固定時間不固定效應模型的各項解釋變量系數基本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調整后的R2最優,明顯優于其它模型的估計結果,這個結論與李婧等(2010)的結果完全一致。這里列出的就是使用地區固定時間不固定效應進行回歸的結果。
(二)模型結果分析
無論是SLM模型還是SEM模型,從總體來看均表明各地區經濟增長主要還是依賴于資本的拉動,勞動要素的貢獻比較小,這也印證了我國“強資本、弱勞動”的要素格局。
在SLM模型中,地區研發投入在滯后一期后對本地區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相對來說作用不大,本地區研發人員人均R&D資金投入每增加1%對本地區勞動力人均GDP的拉動作用為0.05%。SLM模型的自相關系數ρ的回歸結果為0.405,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概率檢驗,這充分說明中國省份間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與其空間距離越近,且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相近地區的經濟增長,而且經濟發展水平越接近,影響越大,存在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WLnR-1的值約等于零,且不顯著,說明本地區的研發投入只對本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直接的拉動作用,對其它相鄰地區的經濟增長沒有直接的空間溢出效應。
在SEM模型中,WLnR-1的系數為0.157,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可能是由于與SLM模型相比,SEM模型中沒有了相鄰地區GDP的直接影響,而這種影響間接地由相鄰地區研發投入的空間溢出效應表現出來,所以相鄰地區R&D投入對本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間接的促進作用;空間誤差系數λ的值為0.855,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概率檢驗,這說明我國省域之間的空間外部性主要是通過誤差沖擊的空間傳遞實現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省份的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和相互依賴性。
四、省域R&D投入對經濟增長作用途徑的分析
本文利用空間計量經濟理論和模型對中國省域R&D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不僅受到本地區資本、勞動力、研發資本投入和研發人員投入因素的影響,而且受到來自與其地理位置相近,且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其它地區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同時還受到來自這些地區R&D投入的間接影響。在空間距離權重矩陣的構成中,地理距離的權重為0.3,經濟距離的權重為0.7,因此當A、B兩個省份同時與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C的地理距離相近時,對于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A省,其經濟增長無論是從C高水平經濟增長中受到的直接影響,還是從C較高的R&D投入中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得到的間接影響都要高于與C省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的B省。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地理距離相鄰僅提供了知識溢出的可能性,而經濟發展水平相似才是這種知識溢出能否實現的決定因素。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人力資本積累就豐富,無論是R&D資金投入還是R&D人員投入都會相對較高,其“干中學”的能力也會較強,相鄰地區的知識溢出才能被更好地吸收、消化,并轉化為其自身的創新能力,形成內生性技術進步,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形成一種不斷加強的正向循環。
根據上述實證研究結果,并結合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本文總結出中國省域R&D投入對本地區及相鄰地區經濟增長影響的路徑圖,即從國家創新體系角度出發的一個省份R&D投入對整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路徑圖,如圖2所示。
圖2說明作為我國國家經濟體系和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一個子系統,每一個省份研發投入都可能通過四條途徑作用于國家經濟體系,其中一條是直接途徑,三條是間接途徑。
①直接影響途徑:A地區R&D投入→A地區經濟增長。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A省份的研發投入會對本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雖然這種作用在樣本期內與資本和勞動力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相比要小許多,但是隨著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不斷深入,今后我國的經濟發展將更多地通過研發活動促進技術進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集約化”經濟發展,因此今后研發投入對經濟增長的直接作用將會越來越重要,其影響也會不斷增強。
②間接影響途徑1:A地區R&D投入→A地區創新產出→A地區經濟增長。根據相關研究,A省份的研發投入會提高本省的創新產出(如專利),有些創新產品可以直接作用于生產過程,如新產品的發明可以直接促進經濟增長;有些創新產品則會促成新資本升級,如更先進的機器設備的應用會提高生產的技術水平和效率;在研發活動中勞動者也可以通過“干中學”來不斷地積累經驗和知識,這有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研發投入通過這些不斷物化到物理設備和提高人力資本的方式,逐漸內化到各生產要素中,形成更先進的生產力,促進本地經濟增長。

圖2 我國國家創新體系中省份間R&D投入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路徑圖
③間接影響途徑2(空間溢出效應):A地區R&D投入→A地區經濟增長→B地區經濟增長。本文的研究結論表明A省的R&D投入可以直接促進本省的經濟增長,A省的經濟增長又會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影響相鄰B省的經濟增長。因此一個地區的研發投入能夠間接地促進相鄰地區的經濟增長,存在空間溢出效應。
④間接影響途徑3(空間溢出效應):A地區R&D投入→A地區創新產出→B地區創新產出→B地區經濟增長。相關研究表明A省的R&D投入能夠促進本省的創新產出,而創新產出具有空間溢出效應,能夠對相鄰B省的創新產出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B省創新產出又會促進B省的經濟增長。因此一個地區的研發投入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對相鄰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間接的促進作用。
五、政策建議
本文在吸收其它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國家創新體系的角度,使用我國2000-2010年各省的面板數據,利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對我國各省份R&D投入對整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途徑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一個地區的研發投入不僅可以促進本地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可以通過間接途徑促進其它地區的經濟增長,這個結論對于我國提高自主研發水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首先做為一個整體,每一個省份都是國家創新體系的一部分,從系統論的角度看,任何一個子系統的研發投入對整個系統來說都可能產生1+1>2的效果。因此,各省份在提高研發效率的前提下,加大研發活動資金和人員的投入,對于促進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意義重大。
其次,相對于各省份而言,每個省份的地理位置是無法改變的,但是它可以通過努力改變70%的經濟距離,在提高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時,為促進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對于落后地區來說,要在短期內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是不現實的,因此可以通過分階段逐步提高來縮小與發達地區的經濟差距,促進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相鄰地區要比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的相鄰地區產生知識溢出的效應大,因此欠發達地區可以首先選擇與其相鄰但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并不是特別大的省份從各個方面進行更多的合作,加強技術和人員的交流,通過發揮其自身的優勢形成產業集聚或區域集聚。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可能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極”,通過它的吸引力和擴散力在提高自身規模的同時,帶動其它部門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當這種發展形式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這個經濟體就可以將目標瞄準經濟更發達的省份或經濟體,進行更大范圍的合作,進入經濟跳躍發展的第二階段。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地區自身也必須通過加強本地區的基礎教育水平,提高國民的整體文化素質,進行各種以提高勞動者技能為目的的職業教育,同時加強與經濟發達地區合作,在“干中學”中加強人力資本的積累,也可以通過各種政策吸引外地人才,增加自身吸收外部知識溢出的能力,達到縮小經濟差距的目的。
對于經濟發達地區,可以借助于其自身的優勢,有目的地加大科技研發活動的力度,一方面可以通過研發活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這些研發活動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促進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因此,經濟發達地區加強科技研發投入,增加有目的的研發活動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說是一個雙贏的行為。
[1]Griliches Z.Productivity,R&D and Basic Research at the Firm Level in the 1970'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1):141-154.
[2]Aghion P,Howitt P.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J].Econometrics,1992,60(2):323-351.
[3]朱平芳.全社會科技經費投入與經濟增長的關聯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9,(3):28-31.
[4]Tobler W R.Lattice Tuning[J].Geographical Analysis,1979,11(1):36-44.
[5]Bernardi Cabrer-Borras,Guadalupe Serrano-Domingo.Innovation and R&D spillover effects in Spanish regions a spatial approach[J].Research Policy,2007,(36):1357-1371.
[6]項歌德,朱平芳,張征宇.經濟結構、R&D投入及構成與R&D 空間溢出效應 [J].科學學研究,2011,(2):206-214.
[7]胡鞍鋼,王紹光,康曉光.中國地區差距發展報告[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
[8]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地區差距分析[J].經濟研究,1998(6):3-10.
[9]Higgins B.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Essays in Honor of Franciois Prerroux[M].Boston:Unwin Hyman,1988.
[10]Adams J.Comparative Localization of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Spillovers[J].Journalof Economic Geography,2002,2(3):253-278.
[11]Keller W.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92(1):120-142.
[12]符淼.地理距離和技術外溢效應——對技術和經濟集聚現象的空間計量學解釋[J].經濟學季刊,2009,(7):1549-1566.
[13]孫建,齊建國.中國區域知識溢出空間距離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1,(11):1643-1650.
[14]Jaffe A.Real Effects of Academic Research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79):957-970.
[15]蘇方林.中國省域R&D溢出的空間模式研究[J].科學學研究,2006,(10):795-800.
[16]李婧,譚清美,白俊紅.中國區域創新生產的空間計量分析——基于靜態與動態空間面板模型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10,(7):43-55.
[17]Griliches Z.Patent Statistics as Economic Indicators:A Survey[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90,28(4):1661-1707.
[18]王家庭.技術創新、空間溢出與區域工業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12,(1):55-61.
[19]黃蘋.中國省域R&D溢出與地區經濟增長空間面板數據模型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8,(8):749-753.
[20]Griliches Z.Issues in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Productivity Growth[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0):92-116.
[21]Pakes A,Griliches Z.Patents and R&D at the Firm Leve:l a First Look[A].Z.Griliches.R&D,Patents and Productivity[C].Chicago:University Press,1984.
[22]Anselin L,VargaA,AcsR J.Localgeographical Spillovers between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High Technology Innovation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7,(42):422-448.
[23]Bode E.Is Regional Innovative Activity Path-Dependent?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Germany[A].Kiel working paper 1058 [C].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ics,2001.
[24]吳玉鳴,何建坤.研發溢出、區域創新集群的空間計量經濟分析[J].管理科學學報,2008,(8):59-66.
[25]Funke M,Niebuhr A.Regional Geograph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illovers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West Germany[J].Regional Studies,2005,(39):143-153.
[26]張軍,吳桂英,張吉鵬.我國省際物質資本估算:1952-2000[J].經濟研究,2004,(10):35-44.
[27]王小魯,樊綱等.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跨世紀的回顧與展望[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28]Griliches Z.R&D and Productivity Slowdow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70):343-348.
[29]Griliches Z.R&D and Productivit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30]Goto,Akira and Kazuyuki Suzuki,R&D Capital,Rate of Return on R&D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of R&D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9,(71):555-564.
[31]謝蘭云.中國省份研究與發展(R&D)指數及其存量的計算[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0,(4):65-71.
[32]Anselin L,SpatialEconometrics:Methods and Models[M].Dordrecht,KluwerAcademic Publishers,1988.
[33]Anselin L,Varga Acs.Local Geographic Spillovers between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High Technology Innovatio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5,(42):422-448.
[34]鄧明,錢爭鳴.我國省際知識存量、知識生產與知識的空間溢出[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5):42-53.
[35]Keller W.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92):120-42.
[36]Case,Rosen,Hines.Budget Spillovers and Fiscal Policy Interdependence:Evidence from the State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3,(52):285-307.
[37]許簫迪,王子龍,譚清美.知識溢出效應測度的實證研究[J].科研管理,2007,(9):76-86.
[38]林光平,龍志和,吳梅.中國地區經濟收斂的空間計量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4):14-21.[39]王火根,沈利生.中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空間面板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12):98-107.
[40]王遠飛,何洪林.空間數據分析方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41]吳玉鳴.中國區域研發、知識溢出與創新的空間計量經濟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2]朱平芳,徐偉民.政府的科技激勵政策對大中型工業企業R&D投入及其專利產出的影響[J].經濟研究,2003,(6):45-53.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Impact of Chinese Provinces'R&D Investment on Economic Growth
XIE Lan-yun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Dalian 116025,China)
In order to analysis the pathways of Chinese provinces R&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the paper uses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e's panel data between 2000 and 2010.The paper redefines spatial weight matrix including 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factor.Meanwhile,it researches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R&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SAM and SEM,and finds that the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has an obviously spatial correlation.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a province's R&D investment can affect the whole natio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four ways,the first way is direct affect,the second is indirect way,and the other two ways are indirect affect based on spatial spillover.
R&D investment;economic growth;spatial spillover;region
F752.67
A
1002-9753(2013)09-0037-11
2013-04-05
2013-08-26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規劃項目“中國區域自主創新影響因素評價與政策選擇”(12YJA790151);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我國研發投入與產出域值效應及其非線性關系的實證研究”(12BJY013);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效率的測度及其影響因素研究”(11YJC790119);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遼寧加快培育以創新驅動為核心的新優勢研究”(L12AJL003)。
謝蘭云(1970-),女,河北阜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科技創新、區域經濟、經濟計量分析。
(本文責編:瑞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