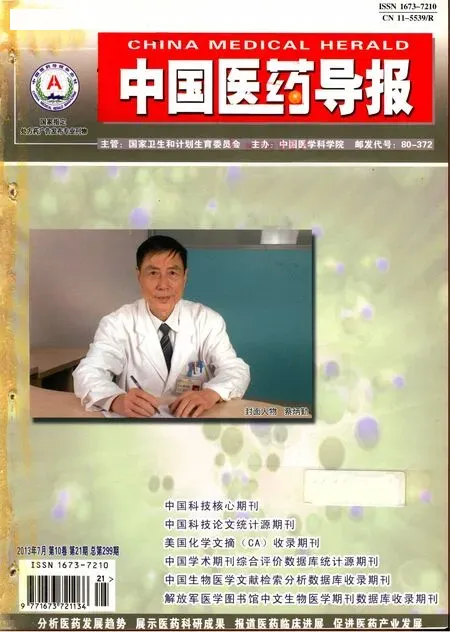針刺結合紅外線照射治療頸肩綜合征C o x比例風險分析
鄧榮華 畢京峰 劉曾敏
1.北京市豐臺區興隆中醫醫院,北京 100171;2.解放軍第三〇二醫院,北京 100039
頸肩綜合征是以頸椎關節失穩、頸肩部及周圍肌肉、韌帶勞損、頸肩部疼痛不適、頸肩部活動受限等一系列臨床表現的癥候群[1],是由于頸椎的急慢性損傷、退變(椎間盤突出、骨質增生等)或頸、項部軟組織病損,卡壓頸脊神經,導致其所支配的頸項部及肩周活動障礙等情況的綜合征。此類患者主要以頸椎退行性改變為主,如頸椎骨質增生,椎間隙變窄,椎間孔變小,周圍軟組織充血水腫,產生無菌性炎癥,引起頸肩背部的肌肉痙攣,肌群失去平衡[2]。頸肩綜合征是中、老年人的常見病及多發病,也是針灸科最為常見的病種之一。本課題組采用回顧性研究方法,對針刺結合紅外線照射治療頸肩綜合征患者的效果進行了分析評價,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所有臨床信息均來自2010年3月~2012年12月在北京豐臺區興隆中醫醫院(以下簡稱“我院”)針灸科診治的頸肩綜合征患者病歷記錄。
1.1.1 納入標準
1.1.1.1 明確診斷為頸肩綜合征 診斷標準為:①有慢性勞損或外傷史、頸椎先天性畸形、頸椎退行性變、長期低頭工作者或習慣長時間看顯示屏者,往往呈慢性發病。②頸項、肩臂疼痛,頸項僵硬不適,疼痛向前臂放射,頸項活動時疼痛加劇。③可分別在胸鎖乳突肌乳突端、第7頸椎、第1胸椎棘突旁、斜方肌下方肩井穴處、肩脾骨內緣等部位出現壓痛。④X線片檢查可有不同程度的頸椎增生、頸椎生理曲度異常改變,或頸椎無明顯異常變化[3]。
1.1.1.2 治療方法 至少符合如下兩種中的一種,①單純針刺組:針刺取穴,至少包含患側頸段夾脊穴、天柱、風池、肩井、肩外俞、天宗、曲池、合谷、后溪穴位。操作方法按常規操作,施平補平瀉法,留針20 min以上。②針刺加紅外線照射組:針刺取穴同單純針刺組,并紅外線照射頸段夾脊穴、天柱、風池、肩井30 min以上。
1.1.1.3 治療效果 達到“好轉”及“痊愈”標準,符合療效判斷標準“好轉”以上要求。痊愈:頸、肩腳及后背部疼痛等癥狀消失,頸部活動自如;好轉:頸、肩臂及后背部疼痛消失,可有肩背酸痛重感或頸部轉到近極限時頸背部有輕微疼痛,頸部活動不受限;無效:頸、肩臂及后背部疼痛,頸部活動受限等癥狀無明顯改善[4]。
1.1.2 排除標準
①伴隨其他影響療效判斷的疾病,如中風(中臟腑)患者等;②除上述治療方法外,還應用其他治療方法的患者,如口服止痛藥物者等。
1.2 患者信息采集
內容包括年齡、性別、從治療到“好轉”的間隔時間。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錄入Excel表,經核對無誤后借助SAS 9.1.3統計分析軟件,應用生存分析方法進行統計分析。分析變量“生存時間”的定義為:從治療到“好轉”的間隔時間。
1.3.1 對針刺組及針刺加紅外線照射組的人口學資料進行分析
提供性別比例、年齡的最小值、最大值、均數、標準差。為分析組間的均衡性,對性別比例應用χ2檢驗進行統計分析;對于兩組年齡,按如下標準進行統計分析:①首先進行正態性及方差齊性分析,如果年齡不符合正態性,則對年齡取對數,再進行正態性檢驗;如果仍不符合正態性,則對年齡取秩,然后應用秩和檢驗進行統計分析;②在兩組年齡或年齡的對數符合正態性的情況下,如果符合方差齊性,則應用獨立樣本t檢驗進行統計分析;如果不符合方差齊性,則應用獨立樣本t'檢驗進行統計分析。
1.3.2 采用Kaplan-Meier法進行單因素統計分析
以“從治療到‘好轉’的間隔時間”為分析變量,對針刺組及針刺加紅外線照射組的“生存率”進行估算,并對生存曲線進行比較。提供生存曲線圖、四分位數生存時間及95%可信區間、均數及標準差。
1.3.3 應用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進行多因素回歸分析
以“從治療到‘好轉’的間隔時間”為因變量,以組別、年齡、性別為自變量,采取逐步回歸法進行回歸分析,探索多因素條件下對“生存率”有影響的相關變量。由于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要求連續自變量必須符合正態性,因此,在回歸分析之前,首先對年齡進行正態性檢驗,如果不符合正態性,則對年齡取對數,再進行正態性檢驗;如果仍不符合正態性,則對年齡取秩,然后利用“秩”進行趨勢分析。分析結果提供參數估計、標準誤、χ2值、風險比及風險比的95%可信區間。
1.3.4 Cox比例風險回歸過程中的取值定義
性別:女=0,男=1;組別:針刺加紅外線照射組=0,單純針刺組=1;年齡經正態性檢驗后,按連續計量數據或“秩”引入模型。
2 結果
2.1 兩組一般資料情況
共有174例患者符合本研究納入標準并不符合排除標準,兩組性別、年齡分布比較見表1。

表1 兩組一般情況比較
表1顯示,兩組性別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年齡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上述結果表明,兩組在性別、年齡兩個協變量上的基線是均衡的。
2.2 兩組生存情況分析
由圖1可以看出,兩組生存曲線無重疊交叉,可以進行生存曲線比較。表2結果顯示,針刺加紅外線照射組的生存時間均數、中位生存時間(50%生存時間)均較單純針刺組短,生存曲線的Log-Rank檢驗、Wilcoxon檢驗及-2Log(LR)檢驗均顯示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0.01),提示兩組生存曲線顯著不同,針刺加紅外線照射組的“生存率”小于單純針刺組。由于本研究中,“生存率”反應的是“從治療到‘好轉’的間隔時間”,因此,可以認為,針刺加紅外線照射組達到“好轉”的時間明顯短于單純針刺組,即針刺加紅外線照射組對頸肩綜合征的治療效果優于單純針刺組。

表2 兩組生存情況比較
2.3 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統計分析結果
根據本研究的設計要求,在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統計分析過程中,針刺加紅外線照射組取0,單純針刺組取1,年齡經正態性檢驗后,按連續計量數據引入模型。本研究中,經對年齡進行正態性檢驗,該變量符合正態性(P>0.05),直接將原始連續變量引入模型。
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和組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性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年齡和組別對治療效果有顯著影響,而性別無顯著影響。結果中,年齡和組別的參數估計均為負值,提示年齡、組別與“生存風險”呈負相關,即年齡、組別的數值越大,“生存風險”越小。在Cox比例風險回歸中,“生存風險”與“生存時間”呈負相關關系,即“生存風險”越小,“生存時間”越長。因此,本研究結果提示,年齡、組別與“生存時間”呈正相關關系。見表3。

由于本研究對“生存時間”的定義為“從治療到‘好轉’的間隔時間”,上述結果可以解釋為兩個結論:①年齡越大,“從治療到‘好轉’的間隔時間”越長,年齡越小,則“從治療到‘好轉’的間隔時間”越短,提示年輕的患者更容易獲得“好轉”的效果;②由于在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統計分析過程中,本研究將針刺加紅外線照射組定義為0,單純針刺組定義為1,組別與“生存時間”呈正相關可以理解為,隨著組別數值的增高,“從治療到‘好轉’的間隔時間”將更長,即單純針刺組“從治療到‘好轉’的間隔時間”較針刺加紅外線照射組更長,提示針刺加紅外線照射組更容易獲得好轉的結果。
3 討論
頸肩綜合征屬于中醫的“痹”證范疇,是由于風、寒、濕、熱等邪氣閉阻經絡,影響氣血運行,導致肢體筋骨、關節、肌肉等處發生疼痛、重著、酸楚、麻木等癥狀的一種疾病[5]。《素問·痹論》指出:“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類證治裁·痹證》:“諸痹……良由營衛先虛,腠理不密,風寒濕乘虛內襲。正氣為邪阻,不能宣行,因而留滯,氣血凝澀,久而成痹”。因此,中醫學確立了袪邪通絡的根本治則。
頸肩綜合征是針灸科的常見病種,也是針灸治療的優勢病種。多個文獻報導針灸或針灸配合其他療法治療頸肩綜合征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療效。主要的治療方法包括,①單純針刺法:王薇等[6]應用頰針治療頸肩綜合征,獲得了總有效率93.3%的良好療效。張學梅等[7]通過比較運用溫通針法與常規針刺治療頸肩綜合征的療效差異,發現溫通針法治療頸肩綜合征療效優于常規針刺治療。②針刺加傳統治療方法:李麗紅[8]運用手法和體針拔罐相結合治療頸肩綜合征,并以單純性體針拔罐組為對照,發現手法和體針拔罐相結合組的療效明顯優于對照組。吳玉輝[9]針藥并用治療頸肩綜合征106例,取得了顯效83例(78.3%),好轉21例(19.8%),無效 2 例(1.89%)的良好療效。徐樹立[1]應用針刺、推拿、放風箏治療頸肩綜合征124例,發現治療組具有療程短、見效快的顯明特點。王秀珍等[10]應用針刺結合走罐法治療頸肩綜合征126例,總有效率達到100%。③針刺加現代物理療法治療方法:鄒娟芬[11]應用短針淺刺配合TDP治療學生頸肩綜合征50例,取得了良好的療效。艾宙[12]以電針配合溫和灸治療頸肩綜合征60例,并與頸肩部電腦中頻治療52例對照,觀察兩組臨床療效,發現1個療程后電針配合溫和灸治療組痊愈率為68.33%,對照組痊愈率為26.92%,兩組療效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④其他:潘莉萍[13]基于針灸理論,應用干擾電向量方法治療頸肩綜合征,總有效率達到74.4%。陳慶松等[14]應用丹參聯合中頻電療法治療頸肩綜合征28例,結果發現,顯效16例,有效8例,無效4例,總有效率達86%。

表3 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統計分析
《醫學入門》曰:“凡病藥之不及、針之不到,必灸之。”《扁鵲新書》認為:“痹病走注疼痛,或臀、腰、足、膝拘攣,兩手牽急,于病處灸五十壯。”提示針、灸聯合治療痹病將可能取得更佳的臨床療效。由于灸法會產生較多煙霧,對患者本人及其他同室患者的呼吸會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不利于在針灸科公共場所廣泛地開展。因此,許多灸法內容近年來已經逐漸被紅外線照射所替代。
紅外線治療作用的基礎是溫熱效應,紅外線透入組織較深,穿透深度可達10 mm,能直接作用于皮膚的血管、淋巴管、神經末梢及皮下組織,在紅外線照射下,組織溫度升高,毛細血管擴張,血流加快,代謝增強,血液循環改善,細胞的吞噬功能增加,消除腫脹,促進炎癥消散,降低神經系統的興奮性,有鎮痛、解除橫紋肌和平滑肌痙攣以及促進神經功能恢復等作用。在治療中應用紅外線照射加針刺法,不僅可以發揮針刺的疏通經絡、祛風散寒、利濕止痛的作用,還充分發揮了紅外線照射的疏風散寒、溫陽勝濕、宣痹止痛、消炎的作用,從而達到良好的療效。李成東等[15]應用紅外溫針治療急性痛風性關節發作126例,結果發現紅外溫針可安全有效治療急性痛風性關節發作。李霞等[16]應用針刺加遠紅外照射治療原發性痛經46例,總有效率達到95.7%。筆者認為針刺配合遠紅外照射可溫通胞脈,使寒邪得散,氣滯得行,補脾胃,益氣血,氣血充足,胞脈得養,則沖任自調。
我院針灸科應用針刺配合紅外照射治療頸肩綜合征已有多年歷史,為闡明其療效,本研究以單純針刺組為對照,回顧性分析了針刺配合紅外照射對頸肩綜合征“好轉”時間的影響。為消除性別、年齡等混雜因素對分析結果的影響,將性別、年齡作為協變量引入Cox比例風險模型之中,研究發現年輕患者較年老患者能夠明顯地縮短“好轉”時間,針刺結合紅外線照射方法較單純針刺法也能夠明顯地縮短“好轉”時間,提示年輕、針刺配合現代醫學的紅外線照射能夠顯著地提高頸肩綜合征的臨床療效,減輕患者痛苦。
由結果表3可以看出,組別的風險比為0.003(95%CI為 0.001~0.007),而年齡的風險比為 0.561(95%CI為0.506~0.622)。在Cox比例風險回歸分析中,風險比是一個獨立的概念,其所代表的意義即是暴露組與非暴露組的風險率之比,即流行病學中的相對危險度(RR)。本研究中,年齡的風險比為0.561,提示年齡每增加1歲,“好轉”的可能性將減少到0.561倍,減少近44%;組別的風險比為0.003,提示單純針刺組較針刺加紅外照射組“好轉”的可能性減少到0.003倍,減少99.7%,進一步說明年輕及針刺加紅外照射將極大地提高頸肩綜合征的臨床療效。
本研究成果的確立,將從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個角度為患者帶來福音:一方面,針刺加紅外照射將極大地減少“從治療到‘好轉’的間隔時間”,縮短患者療程,減輕患者病痛,從而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健康勞動力,產生顯著的社會效益;另一方面,由于紅外照射價格便宜,再考慮患者治療過程中的交通費用及誤工時間,針刺結合紅外線照射方法將明顯地降低患者的醫療費用,提高經濟效益。
本研究的主要不足之處在于,對“好轉”時間具有重要影響意義的“病程”因素因在研究過程中信息采集不完善而未引入模型之中。這主要由于多數病歷對“病程”的描述不精確,往往應用模糊時間進行描述,從而無法進行科學的統計分析。
綜上所述,針刺加紅外線照射治療頸肩綜合征,相對于單純針刺組,能夠顯著地縮短“好轉”時間,減輕患者痛苦;另外,年齡也是影響療效的重要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年齡越大,“好轉”時間越長。
[1]徐樹立.針刺、推拿、放風箏治療頸肩綜合征124例[J].中國醫藥指南,2010,8(13):239-240.
[2]鄧忠明.水針刀療法治療頸肩綜合征療效觀察[C].中國針灸學會微創針刀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微創針刀學術研討會,2009.
[3]粟漩,巫祖強.電針肩井穴為主治療頸肩綜合征84例療效觀察[J].中國針灸,2001,21(12):713-714.
[4]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186.
[5]周仲瑛.中醫內科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3:481.
[6]王薇,方曉麗,宋志靖.頰針治療頸肩綜合征45例[J].甘肅中醫,2010,23(2):53-54.
[7]張學梅,王芬.溫通針法治療頸肩綜合征療效觀察[J].上海針灸雜志,2009,28(11):645-647.
[8]李麗紅.手針療法為主治療頸肩綜合征療效觀察[J].針灸臨床雜志,2004,20(12):40-41.
[9]吳玉輝.針藥并用治療頸肩綜合征106例[J].青島醫藥衛生,2004,36(5):353.
[10]王秀珍,亓永花.針刺結合走罐法治療頸肩綜合征126例[J].中醫藥臨床雜志,2010,22(3):258.
[11]鄒娟芬.短針淺刺配合TDP治療學生頸肩綜合征50例[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11(2):139.
[12]艾宙.電針配合溫和灸治療頸肩綜合征臨床觀察[C].廣東省針灸學會第九次學術交流會暨“針灸治療痛癥及特種針法”專題講座論文匯編,2004.
[13]潘莉萍.干擾電向量方法治療頸肩綜合征的臨床觀察[J].中國中醫骨傷科雜志,2007,15(7):72.
[14]陳慶松,曹漢明,錢紅星,等.丹參聯合中頻電療法治療頸肩綜合征 28 例[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09,18(8):897.
[15]李成東,高良,游國師,等.紅外溫針治療急性痛風性關節發作126例[J].內蒙古中醫藥,2008,27(12):38-39.
[16]李霞,高昱.針刺加遠紅外照射治療原發性痛經46例[J].陜西中醫,2006,27(10):1272-1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