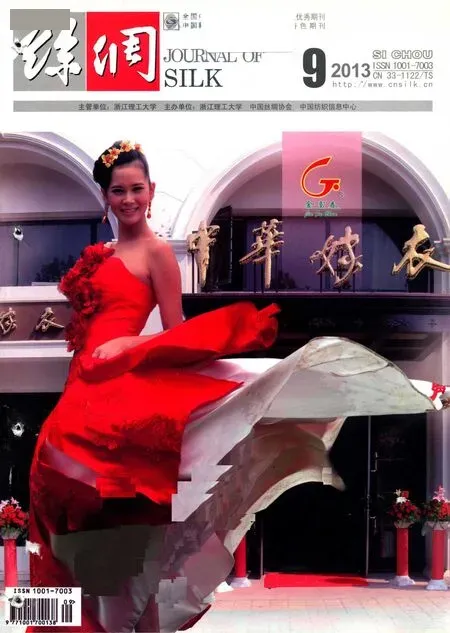解讀唐朝服飾寶花紋中的和合文化
薛再年,鄭清璇,梁惠娥
(江南大學 a.紡織服裝學院;b.傳統服飾文化與數字化創新實驗室,江蘇無錫214122)
在和合文化作用與影響下形成的和合之花——寶花紋,是中國唐朝服飾植物紋樣中彰顯文化底蘊和藝術特色的紋樣典范。根據《寶相花紋樣小考》的論述及探究,“寶相花”一稱最早始于北宋,且趙豐教授在《唐代絲綢與絲綢之路》等相關著作中也認為“寶花和寶相花雖有發展上的因襲關系,但它們分別是對花卉圖案發展史上兩個不同階段的稱呼。寶相花的名和形最早見于北宋《營造法式》”,因此在唐朝服飾上的相關植物紋樣稱為“寶花紋”更為妥切。唐朝服飾中的寶花紋是一種提取了各種植物花卉素材并將各種素材和合在一起的植物紋樣,它是一種兼容并蓄的植物紋樣藝術,并對以后寶相花紋及其他植物紋樣的發展與變化產生了深刻影響。作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和合果實,寶花紋成為和合文化凝聚滲透在唐朝服飾中的典型紋樣。
1 唐朝服飾上的寶花紋
寶花乃是唐代對團窠花卉圖案的一種稱呼[1],一般認為寶花是從隋唐時期開始出現的。寶花及發展到后期的寶相花紋是中國傳統服飾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紋樣之一,且被廣泛運用到藻井、銅鏡、金銀器皿、建筑、陶瓷等裝飾領域。而作為服飾上的寶花紋更多的是被運用到服飾面料的工藝裝飾上,如染織、刺繡等。唐朝最為典型的服飾面料是絲織品,在相關絲織品植物紋樣的研究中寶花紋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內容之一。同時,由于受到世界范圍內紡織文化的影響,唐朝絲綢的染織技藝得到空前的發展,如新的絲絨、緙絲技術,斜紋、緞紋組織的變化,以緯錦替代經錦提花,提花機的更新及織物染料的增加等,這使得唐朝絲織面料上寶花紋的表現形式更加多樣,花紋更加豐腴飽滿,表現內容更加寫實,裝飾效果與光澤較之前也更好。對于唐朝服飾,紅色是唐朝女子服裝中最受矚目的色彩。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朝寶花錦均為明艷的紅色,并將寶花紋通過提花變化組織顯現出來,以此展現出唐朝雍容華貴的服飾特色。在敦煌出土的織錦中也有一件紅地寶花紋錦(圖1)[2],其寶花層次豐富,顏色艷麗多彩,顯得華麗富貴。與用于其他領域的寶花紋一樣,服飾上的寶花紋也是中心對稱的造型,并由中心向外做層層發散的裝飾。它是唐朝最富時代特征的團花形式,它以花卉組成圓形的窠狀圖案,其寶花造型綜合了各種花卉的特點,發揮想像,使花葉交錯,花苞開放,層層相疊,顯得非常端莊華麗,將唐朝社會鼎盛繁榮的景象,顯露無遺[3]。

圖1 紅地寶花紋錦圖案復原Fig.1 Reproduction of red samite with floral medallion pattern
2 和合文化在唐朝服飾寶花紋中的滲透與表現
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和合,和合思想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認同的人文精神。和、合二字始見之于甲骨文和金文。和的初義是聲音相應和諧;合的本義是上下唇的合攏[4]。所謂和合的“和”,指和諧、和善、祥和,指多種不同的事物之間要保持一定的平衡;“合”指相合、符合、融合,是指對立的雙方彼此又有密切相連不可分離的關系。概而言之,和合連起來講,指在承認“不同”事物之矛盾、差異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統一于一個相互依存的和合體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過程中,汲取各個事物的優長而克其短,使之達到最佳組合,由此促進新事物的產生,推動事物的發展[5]。和合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靈魂”,并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學、藝術和風俗習慣之中。和合文化在唐朝服飾寶花紋中的滲透主要通過寶花紋的題材、結構布局及審美意蘊的和合,使組成寶花紋的內部要素及外部要素處于一個和合的統一體中,以此達到該紋樣藝術的和美境界。

圖2 大窠聯珠寶花紋錦及其圖案復原Fig.2 Samite with floral medallion in large nest roundel and its pattern reproduction
2.1 中外題材的兼容之和
寶花紋是集中幾種紋樣的組合形式,早期以蓮荷形態演變而來,之后牡丹花成為寶花紋的原形。在它的取材中既有代表來自印度佛教的蓮花形象,又有來自地中海一帶的忍冬和卷草,還有中亞盛栽的葡萄和石榴[1]。這源于唐朝統治者的開明,以及對各國文化所采取的開放的博采態度。中國的傳統文化、異域文化和宗教文化在這段時間得到了全面、廣泛的交流與傳播。這種文化的交流整合促使唐朝寶花紋等植物紋樣表現出兼容并蓄的氣魄,它們在傳統服飾植物紋樣的基礎上又表現出異域的風采和新的活力。由此可見,和合文化“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思想在寶花紋題材創新中的滲透并不是簡單地將異質要素的羅列和機械的組合,而是要由“和”創生新的事物,所謂“以同裨同,盡乃棄矣”,當所有的要素以一定方式結合后就會凸顯新的性質。寶花紋的題材雖然吸取并受到外來紋樣的影響,但唐朝的寶花紋又有不同于外來紋樣的地方,表現的題材由雄健的禽獸、人物變為富麗的花朵,其母體花瓣吸納借鑒了外來的植物紋樣,同時也吸收和合了本土的牡丹、芍藥、薔薇等花形,取它們的長處,在此基礎上再與其他紋樣和合成具有特定寓意和藝術氣息的復合花瓣,整體外形造型圓潤,使紋樣更顯富貴溫和性質,從而形成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特色和審美思想的紋樣題材和本土的服飾紋樣特色。圖2是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緯錦織物殘片[6],織物上的寶花紋是作為聯珠團窠之間的賓花紋樣,它以柿蒂花為花心,四周延伸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牡丹花葉,四角又延伸出具有西域特色的垂有葡萄紋的藤狀枝蔓。在這件織物殘片上,寶花紋盡管只作為輔助的賓花,卻也在題材的兼容復合中表現得十分富貴豐碩。
2.2 有序對稱的結構之和
和合文化講求在陰陽的辯證運動中所呈現出的和諧、有序、對稱的圖景,講求整個宇宙世界的和諧合理與對稱有序,這種有序對稱性與均衡在寶花紋中得到了高度的統一。寶花紋除了結構布局發展變化的規律性、規則性外,還突出地表現在總體結構的對稱性上。寶花紋是一種團窠花卉紋,它以“十”字或“米”字為構成基架,多以圓形輻射為基型(圖3),也有以正方形或正菱形為基型(圖4),造型以中心對稱為主,即以圓心為中心向外做層層放射狀對稱排列布局的裝飾,使得整體外形接近正圓。寶花紋的花瓣、蓓蕾及枝葉組合則以這種構成基架和構成基型為基礎,做疏密適度、變化有致的有序對稱布局。寶花紋內部裝飾的邊飾紋樣也大都成對稱式分布,且構成骨架統一規整,由此形成一種靜態的和合美。這種有序性還表現在寶花紋樣的色彩構成上,在設色方法上寶花紋運用退暈方法,以淺套深逐層變化,色彩華麗而端莊,總體上形成了構圖飽滿卻不刻意,色彩豐腴而不呆板,整體構圖渾然一體的“和花”之美,比自然形象的花更美、更富麗。

圖3 寶花紋圓形輻射基型Fig.3 Circular radiation-based type of floral medallion pattern

圖4 寶花紋菱形輻射基型Fig.4 Diamond radiation-based type of floral medallion pattern
2.3 形與意的意蘊之和
中國古代傳統的審美判斷和美學思想所追求的是“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即在于得心源而使象深化,寓精神于象外以表達情操,是物境與心境的和合關聯。寶花紋的審美意蘊在于形與意的和合屬性。中國的藝術表現形式大都偏重“寫意”,寶花紋雖然用真實的花卉植物進行寫實,卻又作了一定的寫意變化,即組成寶花紋的花卉植物并非完全模擬現實,而是在自然真實花卉的基礎形式上通過發揮想像力對其形式進行理想的夸張、變化與組合。寫意變化后的花形似某花但又非真實原型,葉子里長出蓮花,牡丹花里生出小石榴,都是在“意”的指揮下對各種奇花異草濃縮后產生的新生命[7]。和合文化的審美意蘊還注重對“象外之象”即對“兩重意”的進一步發展,是重合、重內的產物,為“和”的思想所制約。在中國傳統文化與審美思想中,花具有美好的象征,也常常是人格風范的象征。寶花是自然界不存在的花,最初是以佛教的蓮花為造型基礎發展變化而來。蓮花是“佛教之花”,在大藏經上被稱為寶蓮華,因此常賦予蓮花神圣的含義,以此比附清、靜、圣、潔。之后,寶花以牡丹花為母體,牡丹的雍容華碩成為大唐盛世的主流,“國色天香”奠定了牡丹在唐朝的地位,寫盡了唐朝的輝煌與雍容華貴的氣勢。這種變化反映出寶花向更加世俗化的方向發展,其宗教色彩減弱,經過藝術加工,在吸取眾花形象特征的基礎上形成多種復合花瓣花卉的融合紋樣,這種綜合性的花形是當時人們創造的一種理想紋樣,成為富貴、美滿和幸福的象征。圖5的寶花織錦無論是內環的柿蒂花葉[6],外環內層的折枝花紋,還是外環外層的花苞式寶花,都經過了理想的藝術處理與變形,整體紋樣以俯視的圓形平面紋樣呈現,具有很強的幾何裝飾味,無論是暈繝的色彩還是整體飽滿的花形都表現出唐朝人對理想美與圓滿美的追求。

圖5 中窠寶花紋錦及其圖案復原Fig.5 Samite with floral medallion in middle nest and its pattern reproduction
2.4 整體和諧的構思之和
和合文化是對變動不居的宇宙世界整體穩定性的探尋,講求異質要素有序、有機的結合及內外環境的和諧與共生,這樣才能形成真正的“和”。它所表現出的是一種整體趨于穩定的和合的過程,這種整體的和諧觀體現在服飾上的寶花紋中則是要按照唐朝人的審美所需,將具有形式美和內容美的寶花紋在服飾面料上進行整體布局與構思,并根據服飾面料的材質、底色、幅寬及所對應的服飾部位進行和諧的排列與組合,使整體紋樣渾然一體,并與服飾面料和諧共生。由寶花構成的四方連續形成的植物紋樣在面料上形成韻律統一,整體感強的裝飾風格,或者在寶花紋樣間飾以其他紋樣使整體紋樣的裝飾性更強(圖6)[3]。1968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381號墓出土的鵲繞寶花錦(圖7)[8],圖中飽滿的寶花紋周圍環繞著繁花與鵲鳥、還有蜂蝶與祥云,它由大紅、粉紅、白、墨綠、蔥綠、黃、寶藍、墨紫等八色絲線織成,使花卉的形態生動自然。該紋錦紋樣內容繁復,整體構圖卻和諧有序、章彩奇麗,使得該織錦上的紋樣充滿情感色彩與生活情趣,整體服飾紋樣形成和合的構思之美。

圖6 寶花構成的四方連續紋錦Fig.6 Samite with square consecutive pattern composed of floral medallion

圖7 鵲繞寶花錦Fig.7 Samite with magpies around floral medallion
3 結語
通過從傳統和合文化的思維角度對唐朝服飾上的寶花紋進行研究與分析,其題材、結構、意蘊與構思滲透著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底蘊,該紋樣將人文、藝術、精神和合共生為一個有機整體,內容美和形式美融為一體,其雄渾的民族氣勢和兼容并蓄的氣魄使該服飾紋樣創造出嶄新豐富的題材內容和形式,在審美藝術中強調具備唐朝特有的風骨與神采,共同組成了唐朝服飾上瑰麗而和諧的植物裝飾紋樣。由文化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服飾紋樣進行剖析有助于人們從本源上對傳統服飾紋樣進行深刻的理解與把握,包括對紋樣形制的把握和對紋樣內涵與神采的理解,同樣,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傳統服飾紋樣猶如有源之水,其紋樣的發展與變化將會擁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1]趙豐.唐代絲綢與絲綢之路[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176,177.ZHAO Feng.Silk and Silk Route in the Tang Dynasty[M].Xi'an:Sanqin Press,1992:176,177.
[2]王樂,趙豐.敦煌絲綢中的團窠圖案[J].絲綢,2009(1):45-47.WANG Le,ZHAO Feng.Mission-nest pattern on silk of Dunhuang[J].Journal of Silk,2009(1):45-47.
[3]薛雁,吳薇薇.中國絲綢圖案集[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51,67.XUE Yan,WU Weiwei.Collection of Silk Patterns of China[M].Shanghai: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1999:51,67.
[4]郜得方.淺談我國的和合文化[J].中外企業家,2009(11):257.GAO Defang.Simple discussion on Chinese Harmonious culture[J].Chinese & Foreign Entrepreneurs,2009(11):257.
[5]蔡方鹿.中華和合文化研究及其時代意義[J].社會科學研究,1997(6):67-74.CAI Fanglu.Chinese harmonious culture research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J].Social Science Research,1997(6):67-74.
[6]趙豐,齊東方.錦上胡風:絲綢之路紡織品上的西方影響(4-8世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85-186,194-195.ZHAO Feng, QI Dongfang. New Designs with Western Influence on the Textiles of Silk Road from 4th Century to 8th Century[M].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1:185-186,194-195.
[7]蔣雪涵.唐文化的交流、積淀、整合對唐織錦紋樣的影響[J].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5):61-63.JIANG Xuehan.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accumulation,exchange and conformity on the design of brocade in the Tang dynasty[J]. JournalofJiangsu Radio & Television University,2005(5):61-63.
[8]趙豐.絲綢藝術史[M].杭州: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2:213.ZHAO Feng.A History of Silk Art[M].Hangzhou:Zhejiang Institute of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199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