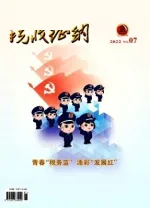撥開運費疑云揭開虛開真相
楊德玲 王雅努
任何人的知識和常識都有局限性,而高速發展的互聯網正是將個人優勢、單位信息和動態資訊大量融合的廣闊平臺。因此,利用互聯網的海量信息資源,發現企業偷逃稅行為,必將成為稅務稽查工作的新路徑。日前,大連市國家稅務局第三稽查局的檢查人員,充分利用網絡信息查出一起虛開運費發票案。
牛刀小試 網絡牽出的疑點
作為老牌的糧食進出口公司,大連某進出口有限公司既保留了傳統的經營項目,又延續了一貫的工作作風——人員信息細致、財務報表清晰、購銷事項明確……點點滴滴無不滲透著企業的規范、嚴格。
完整的企業信息,加之財務人員積極配合,使稅務機關的檢查工作開展得異常順利。就在工作接近尾聲時,檢查人員發現該公司銷售費用中記錄,企業于2011年連續發生了兩筆416萬元運費。
作為一家年收入15.9億元的大型企業,其銷售費用的比例并不高,400多萬元的運費也屬合理范疇。但是比照企業歷年不足10萬元的運費發生額,這并不顯眼的416萬元運費,又似乎格外醒目。
面對檢查人員的質疑,財務人員給出了相當完整、合理的答案。由于近年來,公司進出口大豆等常規作物利潤微薄,因此聘請了一支專業團隊謀求經營轉型,在該團隊的籌劃下,去年公司首次進口了8000噸棉花,而這兩筆運費,正是將棉花由港口運至倉庫的費用。因是首次開展此項業務,故與歷年數據沒有可比性。同時,財務人員還提供了棉花進口的采購合同、報關手續、運輸協議等一系列資料,以證明業務的真實發生。
面對財務人員的誠懇說明和一套較完整的證據鏈,疑問本應解開,但檢查人員在整理審理資料中《運費分析表》時發現,416萬元運費、8000噸棉花,平均520元/噸,似乎過高?于是,檢查人員利用互聯網查詢棉花運輸路線的運費報價,果然,運費報價均價僅為80多元。疑點若隱若現。

霧鎖運費 晦澀專業的解釋
對于檢查人員查詢的運費報價,財務人員驚訝之余,找到具體業務負責人。負責人的解釋簡明扼要,一是第一次開展此項貿易,不了解行情;二是起運地、目的地均在外省,且棉花到岸后急于運出,因此,議價能力較弱;三是棉花運輸特殊,運價本來就高;四是幾筆運費發票均為稅務局代開發票,已由當地稅務機關審核并正常納稅,沒有復核必要。
對于棉花經營的外行而言,以上解釋似乎合情合理,但仔細琢磨,似乎又不能足以說明這筆高出一般報價五倍多的運費。同時,作為大連的進出口公司,為何要跨省進口棉花、異地存儲,豈不麻煩?詢問業務負責人時,他給檢查人員補上了一節經營課。
原來,棉花存儲、銷售都有一定條件,而該企業目前存儲棉花的地點市業內認可的棉花集散地,相關配套完善、棉花買賣集中,而企業就近報關、統一存放、集中售賣,正是棉花批發的最優之選。針對業務負責人的解釋,檢查人員專門上網查詢、咨詢相關部門,并查詢了企業兩筆運費的資金流向,所有信息均證實了該負責人的解釋。難道真的是檢查人員過于敏感,判斷失誤?
幾番溝通、查證無果,看似一切正常,除了那份稅務機關代開的發票。經驗證發票是真的,但為何是不可抵扣的運費發票?根據增值稅暫行條例規定,購進或者銷售貨物以及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支付運輸費用的,按照運輸費用結算單據上注明的運輸費用金額和7%的扣除率計算的進項稅額可抵扣。企業此筆運費發票,本可按7%抵扣稅款,可企業為何白白浪費了本該享受的抵扣額?不懂稅法、開錯了,業務負責人又一次給出了言簡意賅的解釋。一名資歷較深的業務員卻屢犯淺層次的新錯誤,在這兩筆發票的問題上,類似似是而非的解釋,似乎多了些?
一聲嘆息 未了的難解之題
面對一組模棱兩可的信息,檢查人員決定到企業存放、售賣棉花的場所一探究竟,于是,固定信息、整理資料、說明疑點、提交申請。在得到異地協查批準后,檢查人員取得該公司當地負責人的聯系方式,便直奔運費發生地。
當地負責人帶領檢查人員查看棉花倉庫,通過對倉庫租用協議、出庫登記薄等現場資料,與公司財務賬簿信息的比較,證實棉花存儲、銷售情況真實。至此,對棉花購銷業務真實性的懷疑徹底排除,于是,重點展開對運費的核查。
在對運費的核實過程中,開具發票的運輸公司情緒抵觸,在簡單、含糊地向檢查人員說明運費發票確由其提供且業務真實發生后,便以各種理由推脫,不肯接受檢查人員的繼續詢問。
運輸公司的反常態度,引起了檢查人員的警惕,于是,一方面繼續向當地負責人了解運費過高的詳情,另一方面,在當地了解棉花進口業務的具體業務流程和細節等信息。
幾經打探、詢問,檢查人員發現經銷商們對棉花進口環節刻意回避,似乎在共同守衛著一個不愿為外人所知的秘密。而在持續的溝通中,該公司當地負責人也反復強調運費所列金額真實發生,公司誠實經營,并未偷逃國家稅款。究竟是怎樣的隱情,讓所有人諱莫如深?
結合實地了解的信息,檢查人員在網絡上查詢棉花進口流程,一項項分析、排除,終于,一個細節驚醒了檢查人員——棉花進口配額。原來為顯示棉花進口對國棉沖擊,我國規定棉花進口需要申請配額,而對于申請不到配額的小企業,則需額外付款購買其他企業使用不完的配額。
那么,國家分配的低稅率進口指標,是否可以作為商品售賣?而作為第一年開展此項業務的公司,大連某進出口有限公司又是否申請到了這項配額?為何在整個檢查過程中,該公司的所有人對進口配額,只字未提?
再次約談公司當地負責人時,檢查人員沒有直接詢問該公司的配額事項,而是在表明協查即將結束,以降低其警惕性后,迂回了解具體業務詳情,終于,證實了棉花進口必須擁有進口配額,而該公司并無此配額。于是,檢查人員當即向其展示已掌握資料,并說明相關法律政策和責任。
在與公司溝通后,公司當地負責人向檢查人員坦承了事情真相。原來由于第一次進口棉花,該公司并不清楚進口配額的要求,而在已簽訂采購合同、倉庫租用協議、相關資料并支付定金后,才發現配額問題。由于無配額的進口稅率極高,不得已經人介紹購買配額指標。因為配額指標不允許買賣,沒有發票列支,于是賣方聯系貨運公司,制作了相關資料,并提供了這兩筆運費發票。
面對檢查人員開出的補稅罰單,該公司業務負責人無奈地說,“我公司一直都是誠信經營,其實我們也不想這樣,這兩筆運費列支的都是我們實實在在花的錢,一分都沒多開。其實,當初要這不能抵扣的運費發票,也就是不想占國家便宜,可錯了還是錯了,到底讓你們給查出來了。唉!”
一聲嘆息,令檢查人員心中沉重,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和國稅發【2009】114號文,該公司不按規定取得發票,理應補稅。但是,在貿易全球化的今天,因政策限制給企業帶來的無奈和費用無法列支,是否可通過稅務機關更靈活、更完善的服務來逐步減少這種無奈?讓想走出去的企業可以擁有更寬廣的經營活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