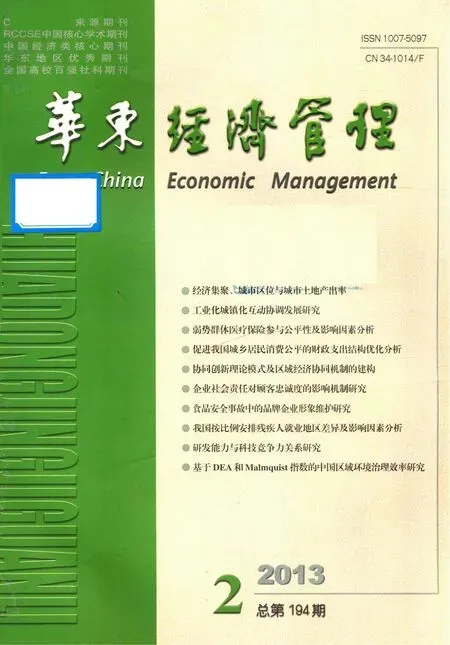經濟集聚、城市區位與城市土地產出率——來自江蘇省的數據
趙 凱,蔣伏心
(南京師范大學 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一、引 言
城市土地產出率是指單位面積城市用地上非農生產活動的產品數量或產值,是經濟密度在產出上的體現。作為衡量城市經濟效率的指標之一,城市土地產出率一方面反映了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或空間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約經濟效益。已有研究表明,經濟集聚對城市經濟增長及其效率的促進作用具有顯著性。藤田和蒂斯(1996,2002)更將經濟集聚看做是經濟增長的地域對應物,他們還認為,區域一體化和國際一體化的主要效應就是增加空間經濟的效率[1]。Ciccone和Hall(1996)[2]則最早使用經濟密度來表示經濟集聚程度,并首次利用美國各縣的數據實證檢驗了密集經濟活動的產出率效應,結果發現就業密度提高1%將帶來勞動生產率6%的增長。他們還指出,密集經濟活動會促進經濟效率的提升;同時,經濟密度較大的地區更有利于專業化的實施,這也會提高當地的生產率。
城市土地產出率取決于城市用地上經濟活動的密度和要素使用的效率。經濟密度對城市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已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明(如,Ciccone and Hall,1996[2];Cicco?ne,2002[3];陳良文和楊開忠,2007[4],2008[5];劉修巖,2009[6];豆建民和汪增洋,2010[7])。經濟密度越高,知識外溢、勞動力池、專業化投入品等集聚效應更強,從而生產率越高(陳良文和楊開忠,2007[4])。而要素使用效率,即要素產出率被認為是經濟增長和城市土地產出率提高的核心。通常情況下,企業為追求其利潤最大化,會傾向于將企業區位選擇在要素產出率較高的城市。新企業帶來資本增量的同時,對勞動力也存在一定的需求,這就會吸引城市外資本和勞動力向城市聚集,從而使該城市的人口規模得以擴張。企業和勞動力向城市地域的集中在提升城市經濟密度的同時,又必然引致對城市建設用地的大量需求,這會促進城市用地規模的擴張。因此,城市經濟效率的提升也會間接地表現為城市集聚經濟的提高和城市規模的擴張(Henderson,2003[8])。Akihiro Otsuka等(2010)在考察集聚經濟對生產率的影響時,進一步指出經濟集聚的增強和市場準入的提高通過改進生產效率來促進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9]。
顯然,由集聚效應所引起的城市規模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經濟效率的提升。Sveikauskas(1975)[10]較早利用城市化集聚經濟效應的檢驗模型驗證了城市規模對生產率的正向作用。陳良文和楊開忠(2007)[4]對我國城市集聚經濟效應的研究也發現,城市規模對城市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正。但是,城市規模的急速擴張在一方面支撐了城市經濟總量的增長;另一方面,人口的不斷聚集,勢必引起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公用設施服務質量的下降以及隨著集聚規模的增加而導致城市公共決策效率的降低、公眾交易費用的增加(江曼琦,2003)[11]。而城市用地規模的過度擴張在導致耕地資源損失的同時,往往伴隨著高速的投資增長,這會造成物質資本的過度累積,從而引起資本產出率的降低,并可能抑制城市土地利用整體經濟效益的提高。豆建民和汪增洋(2010)[7]的分析亦顯示,城市用地規模的過度擴張會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產生負影響。再以江蘇省為例,1996-2010年間,江蘇省城市建成區(地級以上)面積增長了212%,市區非農產業產值實際增長了529%,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城市地均GDP只增長了102%。
在復雜的城市經濟系統中,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因素必定是多方面的。城市經濟的發展總是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轉換,高端的產業結構有利于提升投入要素的產出效率。而已有實證研究表明,地理區位是影響中國城市經濟增長效率和差異的首要因素(李培,2007[12])。良好的城市區位條件往往伴隨著便利的交通、大量信息的聚集、較高的對外開放程度以及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制度措施,這無疑會大大降低這些城市內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運輸成本、信息搜尋成本、交易成本,從而提高其市場潛力,并促進城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進而引致了更大規模的集聚和城市體系的出現。政府由于控制著城市土地的供給,可以通過改變城市土地的配置效率來影響城市土地產出率。而在市場化進程中,較為完善的市場機制可以引導資源在不同產業和地區間進行更為有效的配置,從而拉動城市經濟增長。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補充經濟增長所需資本;二是外商直接投資具有知識溢出效應,進而影響東道地區的經濟增長效率。
本文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江蘇省13個地級市1996-2010年的數據考察經濟集聚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與已有同類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不同:首先,已有關于經濟集聚的大多數研究一般利用區位熵、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空間基尼系數、E-G指數等指標來衡量經濟集聚程度,而本文借鑒Ciccone和Hall(1996)定義的經濟密度概念[2],利用經濟密度來衡量城市經濟活動的集聚程度。為了更為全面地反映經濟密度對城市集聚經濟的影響,本文還引入了資本密度、外資密度等指標。其次,我們認為經濟集聚具有“區位鎖定效應”和“區位指向”,前者是指經濟集聚一旦在某個地區率先形成,便會鎖定這一區位,并通過累積循環效應形成自我強化;后者則表示集聚經濟明顯的地區往往對應著良好的區位條件。因此,本文將地理區位納入影響城市土地產出率的控制變量,以探測城市集聚效應在不同區位條件上的表現,這也是先前的文獻所未予考慮的。最后,本文選取省域范圍而非全國或較大區域作為上層區域來進行實證分析。江蘇作為我國最為發達省份之一,目前正處于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對江蘇城市經濟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在我國特殊的行政區劃體制下,對省域范圍內城市土地產出率的研究,其結論和建議更具有可借鑒性和可操作性。
二、模型設定和數據說明
(一)模型的設定
本文參考 Ciccone和Hall(1996)[2],Ciccone(2002)[3]構建的基于空間外部性的經濟集聚效應模型,并通過對模型的改造得出本文所需的計量經濟模型。
首先,假定各城市中勞動力和資本是均勻分布的,并根據傳統的C-D生產函數定義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函數式為:

其中,qi表示i城市單位面積城市用地上的產出,即表示單位面積上投入的勞動力,Hi為該面積上的平均人力資本水平;ki表示單位面積上的物質資本存量;Ωi表示該城市的全要素生產力水平,并反映了希克斯中性的技術進步;α表示單位資本和勞動力獲得的報酬,且0≤α≤1;β和1-β分別表示單位資本和勞動力投入的份額,且0≤β≤1。
其次,將空間外部性納入生產函數中,這里的空間外部性是指密集經濟活動(一般用經濟活動密度來衡量)對當地經濟效率所帶來的促進作用(劉修巖和殷醒民,2008[13])。假定空間外部性是由該城市的生產密度Q/A所推動,并進一步假定該城市中生產密度的單位面積產出彈性(λ-1)/λ不變,于是有:

上式中,當且僅當λ>1時,密集經濟活動才產生正的空間外部性。將帶入(2)式右邊,得到:

其中,αλ是城市土地產出率對要素投入的彈性,表征了要素集聚效應,αλ>1說明要素集聚有利于城市土地產出率的提高,αλ<1則說明要素投入的增加產生了集聚不經濟。Ω是全要素生產率水平,這里考慮城市用地規模、政府管制、經濟結構、外商直接投資、城市區位等對生產率的綜合影響,于是令,其中G表示政府干預經濟的力度;A為城市用地規模;F為利用外資密度;I為該城市的經濟結構特征;X為區位變量,用來說明城市間的相對地理位置;C為不可觀測和預知的其他影響因素。原式等價于:

如前所述,Hi表示i城市單位面積上的平均人力資本水平。已有研究多采用受教育水平來反映人力資本水平,而針對本文的實證分析,受教育水平的統計數據在時間和截面上均不能完全獲得。已知人力資本是勞動工資的決定因素,工資水平反映了人力資本的報酬率。假定勞動工資完全由市場原則所決定,那么工資的差異就完全體現了人力資本的差異。朱平芳、徐大豐(2007)在利用勞動工資和物質資本存量估算中國195個城市的人力資本水平時,發現單位人力資本與最低工資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14]。并且人力資本對行業工資回報具有正向作用(張原和陳建奇,2008[15]),較高的平均工資水平對應著較高的人力資本結構(張車偉和薛欣欣,2008[16])。顯然,勞動工資水平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力資本水平。于是設Hi=,wi表示平均勞動工資,γ是人力資本水平對于工資的彈性,(4)式轉化為:

對方程(5) 兩邊同時取對數,并設:σ=αλβ,ψ=αλβγ,ξ=αλ(1-β),

則有:上式便是本文將要進行回歸分析的計量模型。其中,ci、μt、εit分別是指i城市的常數項、不隨時間變動的誤差以及時變誤差。
(二)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以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城市市區為研究對象。由于部分城市在1996年進行了行政區劃調整①,因此本文選取的時間序列為1996-2010年,所有樣本數據均來自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江蘇統計年鑒以及中經網統計數據庫。根據計量模型選取了城市土地產出率q、資本密度k、勞動密度n、人力資本水平w、政府干預水平G、城市經濟結構I、城市用地規模A以及城市區位X等指標。這里對各項指標的數據搜集與處理作如下說明:
本文一致采用單位城市用地面積上的投入和產出表示經濟集聚程度,城市用地規模用城市建成區面積表示。
城市土地產出率(q)等于單位面積城市建成區上的非農產業的產值(二、三產業產值之和),為了反映城市土地產出率隨時間的變化情況,這里以1996年②為基期對非農產業的產值進行了價格平減。
資本密度(k)等于地均物質資本存量。將各城市歷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用江蘇省歷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進行平減,得到實際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再通過資本產出比計算出基期(1996年)的資本存量,物質資本折舊率采用張軍、吳桂英等估算的0.096(張軍、吳桂英等,2004[17]),最后利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出各城市除基年外的物質資本存量,再除以建成區面積,得到資本密度。
勞動密度是指有效勞動密度。為保持統計口徑的一致,這里由城市年均在崗職工人數與城鎮個體從業人員的加總除以建成區面積而得。
根據前文所述,勞動工資反映了人力資本的報酬率,因此本文使用勞動工資數據來反映城市人力資本水平,同時也考察了勞動收入差異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
政府干預水平由城市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并利用第二次產業與第三次產業之間從業人員的比值來表征城市的經濟結構。

由于在本文的計量分析中,虛擬變量因其非時變性不能參與到截面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在不減弱變量的解釋力度,同時不引入新變量的原則下,本文基于經濟距離的概念簡單構建了區位變量的表達式,以期能反映區位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之所以選擇上海作為參照物是因為:上海優良的經濟地理位置毋庸置疑;其城市經濟發展具有非常突出的集聚特征;作為長三角地區的首位城市,上海對周邊地區具有較強的輻射力。
三、實證分析
(一)江蘇省城市土地產出率的現狀
由表1可以看出,2010年江蘇省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地區差異非常明顯,產出率最高的常州是最低的連云港的4.15倍;而城市建成區規模最大的南京,其地均GDP僅為72943.78萬元,在江蘇13個地級市中排名第9位;蘇北城市土地產出率普遍偏低,地處長江下游一帶的蘇南及蘇中城市相對較高,上游的南京和鎮江相對較低;與長三角的主要城市相比(見表2),江蘇省的平均水平明顯低于上海市,最高的常州也相差約4億元,而蘇南的平均水平與杭州、寧波等城市相當。

表1 2010年江蘇省城市土地產出情況表

表2 2010年上海市、杭州市、寧波市城市土地產出情況表
(二)計量分析及結果
(1)單位根檢驗。本文采用eviews6.0作為分析工具,在進行模型回歸之前,對面板數據進行了單位根檢驗,以考察數據的平穩性。通過使用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四種方法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判斷序列是否存在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3)表明:lnq、lnk、lnn、lnw、lnA、lnI、lnf等變量的水平(level)序列為一階差分平穩變量;而lnG,lnX為平穩變量。

表3 面板單位根檢驗結果
(2)協整檢驗。本文采用Kao(Engle-Granger based)檢測方法對面板數據進行協整檢驗。結果(見表4)顯示Kao ADF統計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說明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這也說明方程回歸殘差是平穩的,可以對原方程進行回歸分析。

表4 協整檢驗結果
(3)面板估計模型的選擇。通常采用似然比檢驗(F檢驗)來判定混合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若檢驗結果拒絕原假設,則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然后用Hausman檢驗來判定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若拒絕原假設,則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檢驗結果(見表5和表6)顯示兩種檢驗均拒絕原假設,因此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

表5 F檢驗結果

表6 豪斯曼檢驗結果
(4)全部樣本的回歸分析結果。根據以上分析,本文選擇個體固定效應模型來進行計量回歸,并利用“截面加權”方法(GLS)以消除個體間的異方差性。為考察城市區位條件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以及不同區位條件下城市土地產出率及其影響因素的表現,本文將前文(6)式所呈現的計量經濟模型分解為不含區位變量的模型Ⅰ和含區位變量的模型Ⅱ。回歸分析最終結果見表7。

表7 經濟集聚對江蘇城市土地產出率影響的回歸結果
根據表7,首先分析要素集聚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兩個模型均顯示資本密度與城市土地產出率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且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這說明短期內資本投入的增強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提高具有促進效應,同時反映了這一時期城市經濟的增長機制主要由投資驅動。而勞動密度的回歸系數相對較小,且顯著性水平在兩個模型中僅分別為5%和10%,說明相對資本密度及其他因素來說,勞動集聚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相對較弱,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資本及其他要素對勞動的替代作用,同時,有效勞動的集聚不足也可能導致勞動密度與城市土地產出率之間的這種弱相關。勞動密度與資本密度的回歸系數之和反映了城市經濟集聚效應,由表7可知,其值位于0~1之間,這一結果并不表示經濟集聚效應不存在,而是說明經濟集聚過程中產生了明顯的集聚不經濟,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集聚規模的不合理導致了要素使用的低效。具體原因可能有兩方面:一是資本和勞動呈現出過度集聚,導致集聚成本(土地租金、工資費用、擁擠成本、社會成本等)的增加,從而引起凈要素產出率的下降;二是許多經濟活動的開展具有一定的“門檻”要求,低于一定規模的集聚難以獲得顯著的集聚經濟。
人力資本水平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人力資本的增加能夠促進城市土地產出率的提升。由于本文利用工資數據來反映人力資本水平,這一結果也表明勞動收入與城市土地產出率之間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城市用地規模與城市土地產出率之間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其負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為1%,說明隨著城市用地規模的擴大,城市土地產出率在降低,這也表明了城市用地存在明顯的過度擴張。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為吸引投資而加速開發區建設,導致工業建設用地過度增長,同時,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的擴展和調整致使一些產出率較低的部門搬遷至土地價格相對較低的郊區,一定時期內也會使城市用地規模與城市土地產出率之間呈現負相關。
經濟結構對城市土地產出率有顯著的正影響,表明現階段江蘇城市經濟增長主要靠工業推動。由于本文采用第二、三產業從業人員比值來表示經濟結構,計量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現階段城市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整體較低,說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相對經濟增長有所滯后。政府干預水平的影響顯著為負,說明地方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并不利于城市土地產出率的提升,其原因可能是政府主導型的投資低效導致了過高的資本產出比(林民書等,2008[18]);而外資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只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表明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所帶來的城市土地產出率增長并不明顯。
區位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亦顯著為正,且顯著性水平為1%,說明良好的經濟地理位置有利于城市土地產出率的提升。在模型Ⅱ中,區位影響的系數與資本密度相當,說明在只考慮要素投入與空間區位時,良好的區位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較高的城市土地產出率。對比模型Ⅰ與模型Ⅱ的個體截距項(見表8),在加入城市區位變量之后,滬寧沿線城市的自發產出率(產出函數的截距)普遍變小,而蘇北一帶的城市則普遍增大。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對滬寧沿線城市來說,區位條件貢獻了一定的自發產出率,而蘇北一帶的城市區位卻削弱了一定的自發產出率。于是在考慮城市區位條件之后,因城市區位而增加或削弱的自發產出率被分配到區位變量的影響中,這就導致了截距項的變化。由此可以看出,江蘇省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地區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城市區位的差異。

表8 回歸結果中的截距項
5.不同區位城市的回歸分析。為考察不同區位條件城市的城市土地產出率與其影響因素的關系,本文根據前述的步驟和方法分別對滬寧沿線城市和其他城市進行回歸分析(見表9)。由模型Ⅱ的結果可以看出,區位對所有城市都有顯著的正影響,而滬寧沿線城市的區位影響明顯大于其他城市,這一方面驗證了前文所述江蘇省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地區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城市區位的差異,另一方面說明滬寧沿線城市的經濟發展受中心城市(上海、南京、杭州)的輻射影響較大;勞動密度對非滬寧沿線城市的影響很不顯著,說明這些城市可能存在有效勞動集聚不足,即有效勞動集聚水平比較低;而相比于滬寧沿線城市,其他城市資本集聚的作用力更為顯著;政府干預對兩組城市的負影響均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小范圍內市場化水平相對較高;人力資本、經濟結構、城市用地規模等因素在滬寧沿線城市的影響力明顯大于其他城市,而外資密度對滬寧沿線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在其他城市卻不顯著,說明外資集聚對滬寧沿線城市的土地產出率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在其他城市則可能存在集聚不足。

表9 江蘇省不同區位城市的回歸分析結果

續表9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在Cicoone集聚效應模型的基礎上構建計量分析模型,通過引入人力資本、城市區位、經濟結構、城市用地面積、政府干預水平、外資投入密度等因素,以江蘇省13個地級市1996-2010年的面板數據考察了經濟集聚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首先,經濟集聚與江蘇城市土地產出率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相對于勞動集聚,資本集聚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而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以及勞動向低生產率部門的轉移使得勞動集聚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較低。資本產出率和(或)勞動生產率的降低直接導致了經濟集聚效應的減少。
其次,城市用地規模的擴張與政府干預并不利于城市土地產出率的提升,而經濟結構的優化和人力資本的增強則對城市土地產出率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外資集聚與城市土地產出率之間有一定的正相關。
第三,城市區位對提升城市土地產出率具有積極作用,而其他因素對城市土地產出率的影響具有明顯的區位特征。城市區位對江蘇省滬寧沿線城市的土地產出率的貢獻遠大于其他城市,資本集聚對非滬寧沿線城市的作用力則更為明顯。
根據以上結論,針對江蘇省城市土地產出率的提升和地區發展差距的縮小,本文建議:(1)發展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是提高江蘇省城市土地產出率,尤其是滬寧沿線城市土地產出率的有效途徑,這是由滬寧沿線城市現階段的資本產出情況、人力資本水平、經濟結構以及良好的城市區位所共同決定了。而其他城市則應加強傳統工業經濟的發展。(2)應加快市場化進程,逐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以提升資本產出率并控制城市用地規模的過度擴張。非滬寧沿線城市還應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從硬件上縮短與滬寧沿線城市的距離,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3)強化區位優勢是滬寧沿線城市提升土地產出率的有力保障,應克服行政區劃的限制,強化區域內城市空間經濟的聯系;同時,要促進優勢產業的集聚和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化。非滬寧沿線城市要積極吸收滬寧沿線城市的經濟輻射,在承接發達城市的產業轉移的同時要通過增強自身人力資本積累、工業經濟集聚來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還應加強中心城市的建設,通過培育內部經濟中心來帶動自身經濟的發展。
注 釋:
① 1996年7月19日,地級泰州市成立;1996年,宿遷市脫離淮陰市的管轄,升格為地級市;2000年12月21日,淮陰市更名為淮安市。
② 由于統計口徑和行政區劃的調整,1996年以前江蘇省部分城市的相關數據無法獲得,于是這里無法對其進行常用的1990年(或其他常用年份)價格進行平減。
[1]藤田昌久,蒂斯.集聚經濟學:城市,產業區位與區域增長[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499-506.
[2]Antonio Ciccone,Robert E Hall.Productivity and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1996,86(1):54-70.
[3]Antonio Ciccone.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Europ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J].2002,46(2):213-227.
[4]陳良文,楊開忠.生產率、城市規模與經濟密度:對城市集聚經濟效應的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07(2):113-119.
[5]陳良文,楊開忠.經濟集聚密度與勞動生產率差異——基于北京市微觀數據的實證研究[J].經濟學(季刊),2008,8(1):99-114.
[6]劉修巖.集聚經濟與勞動生產率——基于中國城市面板數據的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J].2009(7):109-119.
[7]豆建民,汪增洋.經濟集聚,產業結構,與城市土地產出率——基于我國234個地級城市1999—2006年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財經研究,2010(10):26-36.
[8]J Vernon Henderson.Marshall’s scale economi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3,53(1):1-28.
[9]Akihiro Otsuka,et al.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Ja?pan:Productive efficiency,market access,and public fiscal transfer.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J].2010,89(4):819-840.
[10]L Swikauskas.The Productivity of Cit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J].1975,89(3):393-413.
[11]江曼琦.城市空間結構優化的經濟學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3-89.
[12]李培.中國城市經濟增長的效率與差異[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7):97-106.
[13]劉修巖,殷醒民.空間外部性與地區工資差異:基于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經濟學(季刊),2008,8(1):77-98
[14]朱平芳,徐大豐.中國城市人力資本的估算[J].經濟研究,2007(9):84-95.
[15]張原,陳建奇.人力資本還是行業特征:中國行業間工資回報差異的成因分析[J].世界經濟,2008(5):68-80.
[16]張車偉,薛欣欣.國有部門與非國有部門工資差異及人力資本貢獻[J].經濟研究,2008(4):15-25.
[17]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經濟研究,2004(10):35-44.
[18]林民書,張志民.投資低效與經濟增長:對中國資本存量和無效投資的估算[J].河南社會科學,2008(5):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