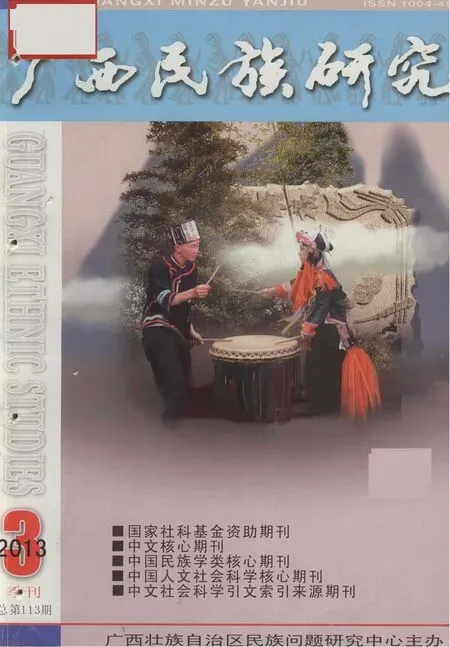轉型期侗歌傳承場域的多維走向與價值位移*
張澤忠 韋 芳
田野調查發現,轉型期侗歌藝術傳承場域衍化模式的總體趨勢是傳統意義上的傳承場域聚合要素①侗歌藝術傳承場域的時空聚合要素,指侗歌藝術傳承、發展、演變的構成因素或組成要素:(1)侗族歌謠藝術的主要內容和形式;(2)侗族歌謠藝術的演唱時間和地點;(3)侗族歌謠藝術的傳承人 (歌師、歌者與受眾);(4)侗族歌謠藝術的虛擬空間 (網絡)傳播及仿像性表演、展演;(5)侗族歌謠藝術的經典性歌論:“養心”論。陸士斌:此是筆名或編校出錯。綜合各方信息,其真名應為陸干斌,男,原是廣西象州縣高中歷史、政治教師,退休后為象州縣“象文化”研究會會員。曾發表學術論文多篇。發生了多維走向與價值位移的改變。顯然,這是一個頗具現代性特征的“場所化”與“去場所化”②人類學家馬克·奧格 (Marc Auge,1995)認為,“場所化”開始的同時,“去場所化”即如期而至,只是由“場所化”到“去場所化”有一個轉換點的增殖以及據以和社會空間、世界進程打交道的臨時“場所”的不斷涌現與擴散。轉換過程所帶來的變化。
一、民間性與精英性
現代性視角中的民間性,一是指傳統傳承場域以自發性、自足性和自信性等聚合方式構筑持守自我品格、品質的規整性特性,二是指傳承人 (歌師、歌者與受眾)這一聚合要素具有多數性、普通大眾性和一般性等特征。相對民間性而言,精英性主要指侗歌藝術傳承人 (指歌師及歌者,受眾不包括在內)及其演唱方式向精英化轉變所表現出來的特殊性。從侗歌藝術傳承場域的主體性角度來看,民間性指侗歌演唱活動“存活”于民間和大眾,其演唱主體是民間的和大眾的,欣賞主體也是民間的和大眾的,因為傳統社會侗歌藝術演唱活動大都屬于民間自發性表演和展演。以踩堂“哆耶”③“哆耶”(duol yies/th?ε323jiε33),亦稱踩堂“哆耶”,是一種集歌舞樂為一體的源于人類原始社會早期藝術樣式。參見侗族文學史編寫組編:《侗族文學史》,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8頁。注音格式說明:在“duol yies/th?ε323 jiε33”中,前者為侗文,后者為國際音標讀音。下同。(duol yies/th?ε323jiε33)為例,亦可看出侗歌藝術演唱活動的這一特性。踩堂“哆耶”是一種集體的歌舞活動,發起人邀請眾人參與,歌者與聽者在且歌且舞中位置不斷地變換,這種全民參與性和角色互換性保證了踩堂“哆耶”的民間性特質和品格。然而民間性在向精英性衍化后,侗歌藝術傳承場域演唱主體和欣賞主體大都是“精英”的,或者有一方是“精英”。“精英”的隊伍也發生了變化,不是以往人們所認為的那些出類拔萃的人群。轉型期的“精英”,一是相對民間自發性即普通民眾而言,二是指群體的特殊性和非一般性。后者 (即特殊性和非一般性群體)包括歌師、學者、政府人員、歌舞活動經紀人,等等,他們的能量主要體現在知識文化和技術水平上,或者體現在權力或資金的投放與市場運作上。不過,不管是傳統社會或現代轉型期,“精英”主體仍指歌師群體。傳統社會中,歌師既是侗族文化傳承的精英,又是普通大眾中的一員。進入現代社會以后,歌師身份發生了變化,有的成為文化館干部,有的成為鄉鎮文化站職員,然而他們在傳承場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擔當的責任,與民間歌師沒有多大區別。不同的是,轉型期歌師的身份明顯向“精英化”衍化,包括民間歌師在內,有的身價、地位與普通民眾不盡相同,有的可以說已經躋身于純粹意義上的精英隊伍。
調查表明,現代轉型期精英隊伍的主體是學者、政府官員和民間文化市場運作中的經紀人。20世紀90年代以來,侗族社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涌現出大批的學者型精英人才,他們土生土長,吸收母體文化的滋養,接受高等教育和掌握漢民族文化知識,因此,他們往往能從更廣闊的社會背景和視角對本民族的文化進行審視和研究。他們是侗歌藝術傳承場域中當之無愧的精英。而侗族地區政府職能部門官員,由于文化產業運作的原因,也擠入了傳承場域精英行列,原因是他們直接管理侗族地區的行政事務,較普通大眾和學者有更大的話語權。經紀人則來自于民間,是市場經濟時期的新型人才;在民間,經紀人意味著掌握財權,在文化資源市場化運作過程中他們擁有資金投放和財力基礎話語權,是一股推動侗歌藝術繁榮和市場化操作的生力軍。
實踐表明,轉型期侗歌藝術傳承場域衍化過程中涌現出來的現代型文化精英,其話語權及領軍位置并不是生而有之,他們原本是民間普通民眾之一員 (從酷愛侗歌藝術這一意義上說,政府職能部門官員除了行政話語權之外,其基礎性身份可認同于熱心侗歌藝術傳承的民間普通民眾),在經過一定的人生歷練后轉變為藝術精英。當他們投身侗歌藝術傳承場域并有所作為時,往往以他們所善長的技能,或以他們的知識文化、權力和財富以及市場操作能力去影響侗歌藝術的繼承與流布。由此可見,緣于轉型期傳承渠道的多樣性,以及傳承活動過程中各項聚合要素發生變異和衍化這一契機,侗歌藝術傳承場域民間性與精英性特征發生了諸如同質疊加、異質同構等相互交叉和精彩紛呈的趨勢特征。
二、神圣性與世俗性
與民間性和精英性的現代轉型相對應的是,神圣性與世俗性也發生了變化。應該說,神圣性遭遇了挑戰,世俗性有所抬頭,這已成為侗歌藝術傳承場域現代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另一傾向。與民間性與精英性一樣,神圣性與世俗性是一組互為關聯對應的概念。當我們對神圣性作界定時,發現這一特色濃郁、意味厚重的概念,旨在傳遞民族情感訴求中的帶有崇高性和神秘性的公共情懷。確切地說,這里所說的神圣性,指侗歌藝術傳統傳承場域時空聚合要素的自我表征 (Representation)①表征,指原有的形態無法描述與表達,用新的符號形態與方式再度表達。英國學者霍爾在《表征:文化意象與意指實踐》中的解釋是:表征指“用語言向他人就這個世界說出某種有意義的話來,或有意義地表述這個世界”,“從根本上說,表征一方面涉及符號自身與意圖和被表征物之間的復雜關系,另一方面又跟特定語境中的交流、傳播、理解和解釋密切相關”。參見[英]霍爾編,徐亮、陸興華譯:《表征:文化意象與意指實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11月,第15頁。行為,源自世俗性 (民間的詼諧性)又超越世俗性②指特定場域中時空要素的神圣性,譬如時空要素的非均質性 (Homogeneous)、間隔性和可逆性,如節慶日侗胞在“薩壇”旁、鼓樓里演唱《大歌·女神薩歲歌》時,蒼穹 (空間存在)仿佛回復到遠古,時間存在仿佛從平常序列中逆出或間斷,倒流到“當初薩歲七千里路下界來”這一神圣時刻,這時你、我沒有尊卑等級之分,只有一個和諧、平等對話的“干道” (gaeml daol,kaem55tao55,即“我們侗人”)在共同體驗元初宇宙圖景的再度現實化所帶來的愉悅、歡樂和神圣。,從而具有充分表達民族公共情感的圣化品格特性;特性的品質內涵意味著崇高性和神秘性。換言之,侗歌藝術傳統傳承場域聚合要素所具備的神圣性,指神圣性情懷的自我表征行為,源自于民族集體的原發性體驗和對宇宙時空的非均質性(Homogeneous)體驗,這種體驗來自于民間和世俗,又超越民間和世俗,其崇高性、神秘性品格、品質內涵使侗歌藝術傳統傳承場域模式烙上了圣化特征和宗教意味色彩。具體說來,非均質性體驗,指傳承場域時空聚合要素與非傳承場域時空聚合要素彼此之間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和時空上的間隔或中斷,正因為這樣,崇高性、神圣性與世俗性的區別及差異才成為可能。
事實表明,現代轉型期,民間性與神圣性、精英性與世俗性共同構筑了侗歌藝術傳統傳承場域的存在樣式。值得強調的是,這里所說的神圣性,特定意義上與超越性相對應,而世俗性則與現實性相對應;此外,世俗性應該說與神圣性一樣系舶來的概念,社會學中指西方文藝復興以來文化藝術從中世紀宗教桎梏中逐漸擺脫出來所呈現的一種現實性與平民性傾向。我們正是在現實性與平民性的這一意義上,對“神圣性遭遇了挑戰、世俗性有所抬頭”這一問題作當下性的詮釋與分析。我們擬從如下方面展開問題討論:
其一,關于侗歌藝術傳統傳承場域的品格、品質特征問題。分析認為,傳統傳承場域的品格、品質特征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盡管神圣與世俗是一對矛盾對立的概念,但兩者并非水火不相容,恰恰相反,它們往往統一在同一對象上。可以這么說,侗歌藝術傳統傳承場域要素構成及其所顯現出來的情狀特征由兩方面構成:一者持守神圣,二者擁抱世俗。前者如前所述,在傳統傳承場域里,侗歌藝術的品格崇尚宗教性情懷和審美性體驗,因而它是神圣的,其特點是追求一種超越性,因為宗教意味也好,詩意性與審美性也好,都倚重于對精神性的追求與超越。
后者之所以歸屬于世俗,原因是在傳統社會里侗歌藝術的表演或展演全然是一種全民性的民俗活動。從這一意義上說,侗歌藝術是一種生態性的文化樣式,崇尚的是一種人文深度的生存方式,它實實在在地與現實社會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它就是生活本身。從這一角度說,侗歌藝術傳承場域當然隸屬于世俗。總之,在傳統社會里,侗歌藝術傳承場域的神圣性與世俗性合二為一,融為一體。
其二,關于轉型期侗歌藝術傳承場域的品格、品質特征歸屬于神圣性還是世俗性的問題。田野調查表明,轉型過程中的侗歌藝術傳承場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神圣性與世俗性依然是矛盾同一體中的兩個方面。不同的是,矛盾對立的兩方面發生了裂變,從而使侗歌藝術的表演、展演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品格、品質特征,或崇尚神圣,或取媚于世俗。這是一種帶有對規整性和根本性品質、品格 (飯養身,歌養心)的裂變。當侗歌藝術的表演或展演從民俗活動中分離出來,變成一種純粹性的審美活動時,它是神圣的;當侗歌藝術的表演或展演與市場化運作活動聯系得過于緊密時,其市場功利目的掩蓋了侗歌藝術的審美性和詩意性,那么它就降低品位而取媚于世俗甚至低俗,因而它是世俗的。誠然,兩者又可以發生互化,即神圣化趨向世俗化,世俗化趨向神圣化。這里所說的世俗神圣化,與民間自發性試圖向精英化靠攏極其類似;不盡相同的是,世俗神圣化注重的是侗歌藝術傳承場域的內在品格、品質的追崇,民間自發性向精英化靠攏注重的是表演或展演活動主體的文化地位或話語權與財富目標 (經濟效益)如何得以體現及實現。因此,精英性未必就是神圣性,民間性不見得就是低俗和鄙陋。
結論是,現代轉型期侗歌藝術傳承場域的價值定位與取向發生了位移和變化,位移和變化的過程由原來的對超越性與詩意性的追求,衍化為時下注重對現實性與世俗性的關注。
三、民間精英化與神圣世俗化
以下,擬結合侗歌藝術傳承場域時空聚合要素的變化,對現代轉型期民間精英化與神圣世俗化衍化模式及其交叉性、互滲性形態特征作簡略的描述、梳理與分析。
(一)表演、展演場所的衍化
調查發現,轉型期侗歌藝術表演、展演場所實現了由實到虛的轉變,其轉變軌跡與侗歌藝術發展的三個階段——作為生產活動產物的原始文化時期、作為觀念形態產物的古代文化時期、作為審美對象產物的泛歷史文化時期——相對應,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室外演唱 (田間地頭、山坡草場演唱)。這一階段的侗歌演唱場所一般在田間地頭,因為人們的勞作多發生在田間地頭、山坡草場,男女之間的情感也多在勞動中逐漸培養起來,所以這一階段的情歌、勞動歌相應地在田間、地頭得以表演或展演。
第二階段,室內演唱 (火塘、月堂、鼓樓演唱),尤其是侗歌大歌、琵琶歌向來以室內演唱為主。這與許多少數民族的山歌風俗有所不同:場所由山坡上移到了寨子的鼓樓或火塘、月堂。如下圖例,可說明一二:

(左)鼓樓里的琵琶彈唱 吳景軍/攝

(右)鼓樓里的大歌對唱 張清澍/攝
侗歌藝術演唱場所由室外移至室內,與侗族傳統社會制度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在侗族傳統社會里,鼓樓被當成侗族制度文化的象征,是村寨的心臟,是人們聚集的中心地;因為如此,它最終成為培育侗歌藝術的園地及中心場所,為人們唱歌、跳舞度過勞動之余的閑暇時日提供了可能。由于場所的可能性,這就為侗歌藝術發展的第二階段 (作為觀念形態產物的古代文化時期)——侗歌藝術離開勞作的直接需要而進入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且充當精神統治工具——提供了保障。另外,相對鼓樓的公眾性和莊嚴性來說,吊腳樓里的火塘行歌或月堂坐夜,譬如男女青年的情歌對唱,其教化功能是通過審美性來實現,因而變化了的演唱場所依然充盈著詩意性顯得溫馨和富有魅力,這一時期的侗歌藝術系作為泛歷史文化時期審美對象的產物而出現 (審美性從發端到成形經歷了三個階段)。實際上,表演或展演場所的改變或衍變,經由作為原始文化時期生產活動的產物和作為古代文化時期觀念形態的產物以及作為泛歷史文化時期審美對象的產物三個階段后,所有的場所共同創造了侗歌藝術的“黃金時代”。[1]
現代轉型期的第三階段,突出的特點是表演或展演場景的虛擬性 (舞臺、校園、電視、廣播、電腦、網絡、多媒體音像制品)。前兩個階段,侗歌藝術表演或展演場景實實在在地凸顯于現實生活和生產活動過程中,全然民間化和世俗化。而第三階段,表演或展演場景已然由“實”趨向“虛”,其表現形態為:或舞臺化,或平移于主題公園、校園,遠離了民眾的生活實際;或“活態”場景為虛擬世界所取代,譬如,與實際生活隔膜的電視、廣播、電腦、網絡、多媒體音像制品的出現。當然,侗歌藝術走向虛擬舞臺、主題公園、校園、電視、廣播、電腦、網絡以及為多媒體音像制品取代,未必不是侗歌藝術傳承場域現代化變革應走的一條新路子。因為,當舞臺、校園、電視、廣播、電腦、網絡、多媒體音像制品等精英化傳承因素經由民間化后,必定趨向大眾化。
實際上,轉型期侗歌藝術表演、展演場所由實到虛的轉變過程,是一個頗具現代性變化特征的“場所化”與“去場所化”(Non—places)的轉換過程。從理論的角度看,人類學家從未忽視社會文化“場所”的偶然性,認為因特殊性“場所”而形成的“場所化”規律,體現在行為文化寄居其中的社會空間或虛或實的變化:即“場所化”開始的同時,“去場所化”即如期而至,只是由“場所化”到“去場所化”有一個轉換點的增殖以及據以和社會空間、世界進程打交道的臨時“場所”的不斷涌現與擴散。看得出來,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這一理論說旨在說明“去場所化”一方面可以理解為是一本“被無休止地重寫”和“涂改得一塌糊涂的稿本”,一方面“可以被解釋成一種意識形態,其立場的歸屬并不比傳統的‘空間’少;而固定性、社會關系和文化常規 (群體、神和有機體)可以被認為不斷地在這個世界上重構自身。但去場所化要達到的目的是推翻一個地方正常的單一性;因此場所和去場所化代表了相對的形態 (指意識形態、立場歸屬、文化常規等),前者從未被完整建構過,后者從未完全達到過。去場所化的可能性和經驗從未被完整建構過,結果是,任何場所都不完全是它自己,都沒有與其他場所徹底分離,也沒有任何場所是另一個場所。”[2]378“去場所化”理論說是由馬克·奧格 (Marc Auge,1995)提出來的,這里引述的目的是為了說明轉型期侗歌藝術表演、展演場所由實到虛的轉變過程,有如人類學家所描述的“場所化”與“去場所化”的轉換過程。即第一、二階段的室外、室內演唱和第三階段的場景虛擬性,可理解成侗族社會的行為文化、歌唱場景“不斷地在這個世界上重構自身”,其結果是“場所化”和“去場所化”“都不完全是它自己,都沒有與其他場所徹底分離,也沒有任何場所是另一個場所”。作此描述的目的是為了提醒人們關注這一由“場所化”到“去場所化”的轉換點所帶來的變化。譬如,變化中據以和社會空間、世界進程打交道的臨時“場所”是如何地涌現與擴散的,而我們該如何予以關注,并加以總結和研究。
(二)歌者、受眾及表演、展演內容的變化
2004年8月,貴州黎平篙鎮晚寨田野調查所獲數據表明,寨子里三四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幾乎人人會唱歌、人人愛唱歌,而三四十歲以下年輕人能唱歌的,男青年只有1人,女青年過半數。晚寨是一個比較偏遠的寨子,歌唱傳統保持較完好,但已是這樣一種狀況;而廣西三江獨峒寨作為一個正走向城鎮化的開放地區,情況則不容樂觀,除五六十歲以上和三四十歲以上有半數會唱歌以外,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只有二成會唱歌。尤其嚴重的是,侗歌在三十歲以下這一代年輕人中已經失去了市場。原因是年輕人忙于生計 (外出打工)而遠離侗歌藝術傳承場域,最終荒廢了學歌唱歌;即使不出遠門,閑暇時聚在昔日作為歌謠藝術活動中心的鼓樓、月堂或火塘,其場景、情形不再是“年老的教歌,年少的學歌,年輕的唱歌”。
又譬如,傳統流傳下來的神話、故事、傳說,靠講古者傳承下來。講古一般在鼓樓講。調查發現,現在鼓樓里把國內奇聞趣事也當講古來講。如講布什、伊拉克,講海峽、講阿扁 (陳水扁)、講機器人、講克隆人。而月堂或火塘,昔日是行歌坐夜的地方,如今電視屏幕里的內容取代一切。
案例表明,民眾已經在關注“團寨”(Duans xaih/thuan11ai33,指聚族而居的自然村寨)社會以外的事,關注世界性體育賽事,關注國家、民族整體利益得失,認知觸角已然由鄉民社會的文化“小傳統”,向都市大眾文化“大傳統”拓展。[3]251可見,傳統社會的“年老的教歌,年少的學歌,年輕的唱歌”的對侗歌藝術的單一性需求,已發展為包括“去場所化”在內的、不比傳統“空間”少的、從內容到形式都得以擴展而帶來的變化和衍化。
(三)衍化模式的交叉性與互滲性
轉型期,兼容與整合,變遷與再地方化,即衍化模式的交叉性與互滲性,是傳承場域聚合要素民間精英化與神圣世俗化的又一表現特征。調查組重點考察的獨峒寨,表面看,當下的侗歌藝術表演、展演活動一般按傳統習慣、習俗來開展,如“月也”(weex yuev/w31yie53,寨子與寨子間的集體做客)、“月地瓦”(weex deih wakv/we31tei33w k53,意為“種公眾地”,即種產權系族群共有的公用地)、鼓樓講古、演侗戲、講款活動、行歌坐夜等,都與傳統生產、生活方式有直接的關系,可看出是典型的農耕文明形態下衍生出來的文化產物。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獨峒寨社會—經濟在轉型的同時,民眾的文化生產和消費理念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具體表現在,原來民間自發組織的活動減少,由政府部門介入的活動增多。如2004年“十·一”黃金周,獨峒寨的生態文化旅游系列活動以政府為主和民間組織參與相結合的方式來開展,以這種形式舉辦的傳統活動項目除了“月也”、“月地瓦”、“多耶”、“吃百家宴”之外,還舉行諸如當下流行的“卡拉OK賽”、球類競技賽等活動。傳統社會的文化活動、歌舞表演或展演,場所相對固定。演侗戲、蘆笙踩堂、青年男女行歌坐夜,場所相對固定。現代化過程中傳統活動項目的秩序化開始向無序化轉變或衍化。
案例說明,轉型期侗歌藝術表演、展演場域已然發生聚合模式的交叉性與互滲性衍化的變化。變化的特點可用這樣的形態特征來歸納概括:即侗歌藝術表演者、展演者包括受眾,已由傳統的普遍性、多數性、民間性,衍化或變化為當下的少數性、精英性 (指非民間的自發性,即指政府職員的職能性和民間發起者的組織作用性)。譬如,傳統侗歌藝術作為一種審美化生存方式被整個社會集體所接受和傳承,其情形是人人學唱歌、人人會唱歌,然而現代轉型期社會生活的豐富性和開放性,致使精神消費有多渠道的選擇,人人學歌、聽歌和唱歌的熱情已發生不可抵御的當下變化或衍化,侗歌藝術的表演或展演,逐漸成為少數精英階層在操作或把玩,傳承場域及流布渠道因此變得相對狹小和不順暢。
與此相對應的另一種情形是,與侗族族群自身的由傳統的普遍性、多數性、民間性的變化或衍化為當下的少數性、精英性不同的是,大環境意義上的受眾 (包括侗族族群自身的受眾)反而由少量的、精英的變成多數的、民間的和世俗的。相當一段時期,了解侗歌藝術的外族人只限于專家、學者和音樂人士,普通民眾接觸、觀賞侗歌藝術表演、展演的機會極為有限。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侗歌藝術傳播媒介種類繁多,傳播范圍廣泛,由此,更多的族外民眾有機會了解侗歌藝術并學唱侗歌。比如受眾這一層面,過去以侗族自身聽眾為主,如今全國各地包括國外都有喜愛侗歌藝術的受眾。這部分受眾有普通民眾,有精英型的學者,有音樂人。可見,侗歌藝術傳承場域衍化模式的不確定性、交叉性及互滲性衍化特征已然形成,并日益凸顯。
(四)傳播媒介的多樣性
侗歌藝術的傳播媒介有多種類型及方式:一是口耳相傳,即口傳心授。侗歌是一種口頭藝術,其媒介是言語及音樂,其特點是直接性、易變性、完整性和創造性。二是紙質材料的運用。凡有漢文化功底的歌師都會使用紙質材料來幫助記憶。這是侗歌藝術得以傳承的另一個重要保障。調查發現,歌師采用的是“漢字記侗音”的方法記錄歌詞。漢字讀音與侗語不能精確地一一對應,紙質材料只能保存歌詞的大致讀音。每個歌師選用的漢字記音符號有所不同,相互間不易于交流,只能方便歌師自身的使用。因此這種媒介的使用具有不完整性和相對穩定性。正是這一點,歌師對記憶力的要求被放在技能訓練最重要的位置,而紙質材料則只起到輔助性的記憶作用;這樣,侗歌藝術口耳相傳過程中的個體性、獨特性和創造性亦得到了保證。三是借助多媒體材料、網絡與電視。隨著多媒體技術的應用和電視、網絡技術的普及,侗歌藝術多媒體音像制品應運而生,并推上了市場,網絡因此有了專門介紹侗歌藝術的網站,電視里也不時轉播侗歌藝術表演或展演的場景。相對于紙質材料,多媒體材料能儲存更多的信息,保存更為久遠,傳播范圍更廣,更方便使用,具有可復制性、可轉換性。然而正因為具有這樣的優勢,演唱者對記憶力的要求降低了,其獨特性、創造性也降低了,演唱活動也往往出現千篇一律的格局及場景。
三種傳播媒介中,口耳相傳中的“口”與“耳”,為每一個社會成員必備的身體要件,因此,口耳相傳模式既具備個體性和獨特性,民間性和大眾化亦得以體現。第二種方式是使用紙質材料,其前提條件是歌者必須具有漢文化功底,這部分演唱者相對普通民眾而言,屬于精英階層。因此,使用紙質材料,是民間化向精英化邁進的第一步。第三種方式是借用多媒體材料、網絡與電視,開始屬于精英階層所擁有,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變成或衍化為普通民眾所能接受的承傳方式。
(五)內容、形式、格調的衍化
侗歌藝術種類繁多,內容包羅萬象,有自然知識、勞動知識、神話傳說、歷史故事、英雄敘事詩、倫理道德訓誡,等等。然而由于社會歷史的原因,發展過程中,侗歌藝術的階段性受重視情況有所不同。如前所述,作為生產活動產物的原始文化時期和作為觀念形態產物的古代文化時期,對應于農耕文明時期,因此侗歌藝術種類及內容大都反映傳統農業社會的勞動生產、神話傳說、歷史故事、英雄敘事詩。而現代轉型期所創編的侗歌藝術及其表演或展演方式,更多地反映、表現改革開放后新農村社會生活,傳統侗歌藝術則側重于對審美品位較高的曲目的傳承,譬如對情歌及大歌中的聲音大歌 (嘎梭,al suoh,a55suo44,大歌的一種,類似美聲演唱的歌,如大歌精品《蟬歌》)尤其青睞。對此,另擬專題論述,這里著重關注侗歌藝術的內容、形式及格調的衍化問題。
田野調查發現,現代轉型期侗歌藝術的傳承、流布有了新的衍化和變化,表現在傳統侗歌藝術比較重內容,當下流行的侗歌藝術則重形式輕內容。這里所說的衍化或變化,不是說形式對傳統侗歌藝術來說不那么重要,而是說現在傳承場域聚合要素中的作者、演唱者、受眾等在創編侗歌、演唱侗歌、欣賞侗歌時關注重心已由傳統的重內容輕形式,轉向現在的垂青形式淡漠內容。
傳統侗族社會,歌師對侗歌藝術的創新,多指對侗歌內容的改編或創造,較少指對侗歌藝術的音樂形式比如曲調的創新。原因在于,一是傳統歌師一般漢文化水平相對較低,沒有相關的音樂知識,難以對侗歌曲調等音樂元素進行改革或創新。另外,從受眾的角度看,曲調的頻繁改動或變換,也不適合和不易于口傳心授,加之舊有的欣賞習慣偏向或偏好于接受傳統遺存下來的帶有原汁原味的曲調,因而受眾對新鮮東西的出現要求不高。二是侗歌藝術演唱者和受眾一般把關注目光放在歌詞的內容美和語言的生動美上,形式美往往次而求之。
然而當下精英人士卻極力倡導侗歌藝術改革,試圖為侗歌藝術的繁榮、發展尋找一條新路,嘗試過程中,常常把創新的重點轉移到對傳統曲調等音樂形式的“刷新”上。田野材料表明,目前有關人士對侗歌曲調的創新基本摸出了路子,創作或改編過的侗歌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是由單一、齊整走向豐富、多樣,二是由隨意、疏落走向嚴謹、規范及精細。
創新實踐中,音樂人士發現,傳統侗歌種類曲調變化不大,旋律簡單,目的是為了適應口耳相傳的傳承方式;由此,他們另辟蹊徑走出一條新路子,即借助樂譜記錄曲調、媒體音像材料刻錄等手段,為侗歌曲調的花樣翻新創造條件。另外,創新隊伍中的創作者 (包括受眾)一般受過漢文化教育,具備相關的知識以及音樂素養,創作或改編出來的侗歌,形式精美、花俏,品種、花樣繁多,為侗歌藝術的傳承、流布注入了新鮮血液。總結起來,在傳承渠道多樣化的趨勢下,侗歌藝術方法創新上有如下兩方面特色:
1.高雅化
即由俗到雅。這一點在校園傳承中表現尤其明顯。侗歌原本來自于民間,創作者、受眾大都土生土長,因此不管創作者還是接受者,都要求曲目或歌詞通俗化,符合大眾口味。當侗歌藝術搬上舞臺、搬進校園后,精通音樂的精英人士認為傳統曲目或歌詞土里土氣,因此理所當然地進行改造和改編。目前校園里尤其是高等學校侗歌班所教授的侗歌曲目,從眾多傳統歌曲中選擇較典雅的部分,為適應演唱場景需要大部分經過了改編或調整,而改編或調整的標尺定位在高雅化上。事實上,經過篩選、改編過的侗歌確實屬于精品創作并流傳于國內外大型舞臺上,然而這些作品或產品卻逐日疏離了民間自發性根基,鄉土化、民俗化特色僅僅作為調料、點綴,讓人多少還能看出侗歌藝術的身影。
2.俗化
即由雅到俗。這一點在侗歌藝術市場化過程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傳統侗歌文本有其俗的一面,但因審美目標為經典歌論“飯養身/歌養心”(Oux xih sangx xenl,al sangx sais,ou31ji33sa?31j?n55,a55sa?31sai323)所規范,所以依然不失典雅之品位。傳統侗歌的創作和演唱實際上是由精英們 (一代又一代的歌師)來完成的,這就從源頭上保證了侗歌藝術的品質和品格。傳統侗歌的創作和演唱活動,注重“唱心頭”,講究審美性,因而保證了侗歌藝術的創作和演唱活動的自律性及品質、品格的純凈性。當下侗歌藝術市場化要求,聽命于市場指揮棒,加之如前所述的值得商榷的高雅化要求,以致造成一種混雜局面,即高雅化、市場化的同時,侗歌藝術的庸俗化露出端倪。
形式和內容的衍化或變化,必然帶來藝術格調的改變或“刷新”。總體來看,侗歌藝術一方面由大眾化走向了精英化,即民間精英化;另一方面則愈加世俗化,即“元敘事”中的經典性或神圣性遭遇現代性的挑戰甚或褻瀆,世俗化或低俗化逐日抬頭并有了市場。
(六)功能性衍化
傳統侗歌的功能大多是世俗性 (指民間性)和功利性 (指審美性及倫理性),特點是所蘊含的生產輔助性功能、宗教性功能、文化性功能、情感性功能與社會現實緊密相連。現代轉型期,這些功能性能量有所衰弱和萎縮。這與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變革有關聯。因為當人們不再拉木時,《拉木歌》就會失去演唱的機會,當行歌坐夜、宗教祭祀等民俗活動逐漸消失時,情歌、祭祀歌就會逐漸絕跡;當人們在課堂上更多地關注“大傳統”語境中的豐富多彩、系統化的科學知識時,處于主流文化邊緣、作為民族文化傳承載體的諸如歷史故事、英雄敘事歌和倫理歌的演唱機會自然減少。可見,轉型期侗歌藝術世俗性或功利性功能發生變化或衍化是必然的事。
總而言之,以“飯養身,歌養心”為規整性特征的侗歌藝術傳承場域,傳統意義上,持守“民間性”、彰顯“神圣性”,現代轉型期,則一方面對“民間性”、“神圣性”若即若離,一方面卻迫不及待地向現代性“精英化”與“世俗化”多渠道地演進,從而使原來處于本體性源頭、具有規整性特質的經典性歌論(“養心”論)發生了價值位移。實際上,如同馬克·奧格 (Marc Auge)所說的,這是一個“場所化”與“去場所化”(Non—places)轉換過程所帶來的頗具現代性變化特征的演變和改變。
[1]張澤忠.侗歌藝術歷史分期“背離”模式說[J].百色學院學報,2011(1).
[2][英]奈杰爾·拉波特,喬安那·奧弗林.社會文化人類學的關鍵概念[M].鮑雯妍,張亞輝,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
[3]張澤忠,吳鵬毅,胡寶華.變遷與再地文化——廣西三江獨峒侗族“團寨”文化模式解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