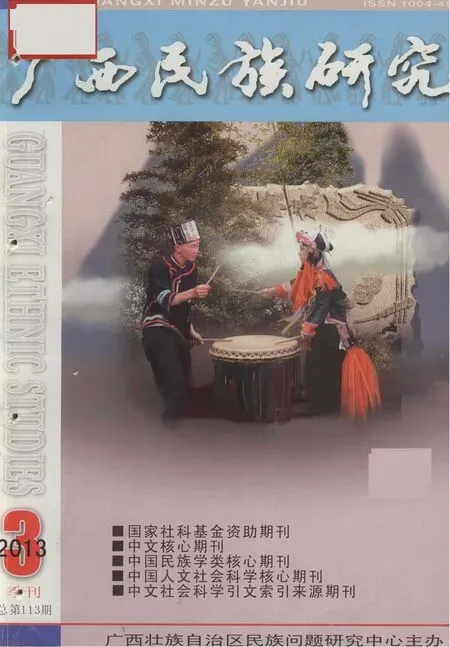近代北海港是“大西南門戶”嗎?*:再論近代北海港的經濟腹地
麥正鋒
一、引 言
廣西北海市①近代北海為廣東省所轄。素有“一城系四南”之稱,背靠大西南,面向東南亞,毗鄰越南,與海南島隔海相望。因具有獨特的地理區位,北海自古以來在國家經濟發展中有著較為重要的地位。上溯漢代,北海境內的合浦港是連接西南和中原地區的重要出海口,與泉州、廣州并列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近代以降,清政府于1876年與英國簽訂《中英煙臺條約》,同意北海對外開港通商,成為繼廣州之后華南地區的第二個通商口岸;時至當代,北海列入中國14個沿海對外開放城市之一,搭上改革開放的“早班車”。
地處邊陲的北海,在各歷史時期始終有機遇走在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的前列。尤其是自近代以來,北海一直被視為西南地區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環節,肩負著成為西南地區對外經濟交往的窗口和通道的歷史使命。近代外國力量欲滲透西南腹地而促成北海開港通商,當代中國為加速大西南的經濟開發而開放北海。然而,北海是否能擔當其在經濟格局中的角色?在近代,北海港作為我國西南地區的出海港口之一,它對西南地區的輻射能力有多大?這既是探究歷史真相的學術問題,同時也是關乎國家和地區發展戰略布局的現實問題。本文從經濟史的視角,對近代北海港口的經濟腹地進行再次探討,對認為近代北海港是“大西南門戶”的傳統觀點進行商榷。
關于北海港的歷史研究,一直以貿易作為研究的重點,李志儉 (1985)[1]、李富強 (1997)[2]、廖國一 (1998)[3]、吳小玲 (2003)[4]等學者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從不同的視角探討北海港的貿易發展史。此外,多種地方史志都設有專門章節敘述北海港的貿易史。①顧裕瑞,李志儉:《北海港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廣西航運史》編審委員會:《廣西航運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黃錚:《廣西對外開放港口——歷史·現狀·前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廣西壯族自治區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駐北海口岸辦事處:《北海口岸外貿志》,1992年印;陳錦光:《北海交通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勾勒出北海港貿易的發展主線,總結出北海港各歷史時期貿易的基本特征。而作為一個貿易港口,其經濟腹地是關鍵因素之一,但關于北海港經濟腹地的專題研究卻鮮見,相關的研究散見于上述研究成果當中。關于近代北海港口的腹地范圍,過去的研究大都泛指西南地區,并沒有較為明確的地域界限和歷史時段,較大程度地使人對近代北海港口貿易的歷史印記定格為“近代北海港是大西南的門戶”,時空范圍擴展至近代的全過程、西南地區的全境,這就無形中拔高了近代北海港對西南地區貿易的影響。缺乏史料實證的深度挖掘,研究者的家鄉情結以及為地方發展而造勢的媒體傳播都將使“近代北海港是大西南的門戶”的歷史觀流傳。只有在客觀認識歷史真相的基礎上總結經驗和教訓,才能更好地促進當代西南地區出海通道建設的發展。
本文的研究主要致力于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依據港口出口土貨主要來源地和進口洋貨主要銷售地來界定北海港的經濟腹地范圍,并且再對經濟腹地作出更為具體的劃分,區別核心腹地與邊緣腹地,②按照經濟地理學的解釋,腹地 (Hinterland)是指位于港口城市背后,為港口提供出口貨物和銷售進口商品的內陸地區。腹地分為核心腹地與邊緣腹地,前者指一港獨有的腹地,該區域內所需水運的貨物主要經由本港;后者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港口共同擁有的腹地,即數港吸引范圍相互重疊的部分,也稱交叉腹地。改變以往對腹地范圍的模糊定性。第二,突破“站在北海看大西南”的思維定勢,站在大西南的視角,通過對與西南地區 (本文僅指滇黔桂三省)關系密切的出海口進行比較研究,以此來觀測北海港對西南地區的影響力。第三,以往研究使用的史料缺乏足夠的數據,本文運用的史料以統計數據較為系統、具體的海關貿易報告為主體。
二、北海港與經濟腹地之間的商路網絡
近代北海港通過由主要市鎮及商路組成的商業網絡來銜接經濟腹地,形成以北海為“中心地”,欽州 (近代稱欽縣)、合浦、靈山、南寧、安鋪和玉林為內地中層市場的商業網絡結構。根據近代北海海關貿易報告和地方史料可以歸納出北海通往腹地的商路主要有 (自東向西):1.北海(水運)——安鋪 (沿九洲江)——高州、雷州 (接烏江)——玉林;2.北海 (水運或者陸運)——合浦 (沿南流江)——玉林;3.北海 (水運或者陸運)——合浦 (沿武利江)——靈山(入西江)——南寧;4.北海 (水運或者陸運)——欽州 (沿欽江)——靈山 (入西江)——南寧;5.北海 (水運或者陸運)——欽州 (陸運)——南寧 (沿左江、右江)——廣西西部、云南、貴州;6.北海 (水運)——欽州 (沿漁洪江)——十萬大山山區;7.北海 (水運)——防城(沿防城江)——十萬大山山區。其中又以第2條和第5條商路最為重要。
“北海 (水運或者陸運)——合浦 (沿南流江)——玉林”商路是溝通古代中原地區與北部灣地區的重要紐帶。南流江發源于廣西北流縣大容山中央塘,呈東北——西南走向,是北部灣沿岸最大的入海河流。南流江流域上的合浦港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之一,成為當時東南亞及印度半島諸國與我國交往的重要窗口,通常由合浦循著“三江一河一渠”進入中原地區,即沿南流江,越鬼門關,接北流河,溯桂江,過靈渠,入湘江,直抵中原。這條貫通南北、連結中外的“黃金水道”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近代。隨著南流江的流向變遷,其入海口的主要港址發生位移,至近代,合浦港為其南面的北海港所取代,北海港成為從雷州半島至北侖河口沿岸最大的商品貿易港口。北海港口貿易的貨物流轉通常是走水路或陸路經“廉州府治 (按:合浦),在北海之東北約七十里”[5]18,這里“風土人情,與北海無大差別。商務亦頗可觀,其進入口貨,俱籍北海為門戶”[5]18,是“北海最主要聯系”的商業網點。然后沿南流江北上到達“北海的另一個最重要的商業中心”[6]45玉林,南流江的三條支流福旺江、武利江和張黃江分別連接了小江圩 (今浦北縣)、北塞圩 (亦稱武利圩)和張黃圩。這些市鎮是南流江流域的商品集散地,承接北海與內地鄉村市場的貿易傳遞。
“北海 (水運或者陸運)——欽州 (陸運)——南寧 (沿左江、右江)——廣西西部、云南、貴州”商路是北海與滇黔桂三省進行商業活動的重要通道。欽州是連結北海與滇黔桂三省腹地的“一大樞紐”。民國《欽縣志》記載:“光緒初年、十幾年時,廣西西江未有小輪行走,南太泗鎮(按:廣西省南寧府、太平府、泗城府和鎮安府)欲辦省佛港 (按:廣州、佛山和香港)各貨,賴我欽為轉運,我欽地居東省 (按:廣東省)、邕寧之中,其時又值稻谷落花生豐收,谷米源源運出北海,麱油源源運上省佛。回頭采辦洋紗、布疋及各雜貨,由紅單船運到南太泗鎮。”[7]卷八成為連接北海與廣西內地的中樞,“欽埠與北海省佛商貨交通成一航行極大路線,常有大三桅帆船名紅單船”[7]卷十一往返欽州與北海兩地間。欽州是個內河港埠,“1000至1500擔載運量的舢板可以在這河中起卸,河面約寬60碼。貨物 (進口)如果打算運南寧的,則全部在欽州打包,再用人工擔運。欽州到南寧大約100公里,旅程一般六到八天。”[6]45從南寧接西江水系,沿左江進入廣西南寧府和太平府,可通龍州;溯右江上鎮安府和泗城府,進入云南、貴州兩省。[8]14、15
從北海的商路網絡來看,珠江水系是北海通向西南地區的最主要通道,但是北海與珠江之間沒有江河直接通達,西南地區的貨物若從北海出海則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通江達海”,需要水陸聯運才能完成全程運輸。水運是近代沿海港口通向內地最為重要的運輸方式,但北海附近的內河諸如南流江、欽江和防城江較短,縱深內陸范圍不廣,因此北海對內陸的貿易深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在近代我國沿海的通商口岸當中,北海是與西南地區空間距離最近的港口,但是西南地區的出海通道是多方向的,除北海港之外,廣東的廣州、廣州灣 (今湛江)和越南的海防都是西南地區的重要出海口。
三、口岸競爭與北海港腹地的變動
(一)北海港腹地范圍的短暫擴張
珠江水系是我國西南地區對外貿易的傳統商路。1851年,廣西爆發太平天國運動,局勢動蕩致使珠江商路廣西段受阻,西南地區的對外貿易路線因之發生改變。“西南地區——廣西梧州——珠三角地區”的珠江水路貿易路線被“西南地區——廣東北海——珠三角地區”海陸聯運的貿易路線所替代,北海港取代梧州成為聯接西南地區與珠三角地區的貿易中轉地。自此,“凡廣西之北流、郁林、南寧、百色、歸順州、龍州及云南、貴州之貨物,均由澳門用頭艋船載運來往”北海港。加之,北海港貿易稅收較低,“入口貨只抽棉花、洋藥,出口貨只抽紗紙、八角”,北海港的商業貿易“因此大為興旺”。[5]3港口的腹地開始延伸至廣西、云南和貴州三省。
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的簽訂使北海港成為當時中國大陸海岸線上由南至北的第一個通商口岸。然而,此時的北海港仍只是一個小港埠,“經濟商務發達情形,殊鮮令人注意,雖已次第開埠,然貿易狀況,則屬失望。”[9]210因為“在這新口岸開辟之初,國外商業界對此不感多大興趣,香港及其它地方有財力的商行均未委托代理行來促進貿易的發展”[10]21。
1879年英國派出大量人員對北海港進行勘探,繪制出精確的北海港海圖,并于1881年7月15日由英國倫敦皇家海軍向國際航海界公布。尤其是1883年,中英兩國簽訂了《煙臺條約》續增專款后,北海逐漸引起了眾多外商的關注,抵北海港經商者日漸增多,隨后德國和法國相繼在北海開設洋行。洋行的開設以及輪船航運的興起進一步促進了北海港口貿易的發展。
低稅率是北海港貿易繁榮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此階段貨物在北海進出“完納關稅每百兩約抽五兩”即可,而在越南海防則要“納關稅每值百兩約抽三十、四十、五十兩不等”,因此“自光緒十年之后凡往云南省之貨物俱由北海采辦”[11]。在此期間,棉布與棉紗是北海港主要的進口洋貨,占有較大的份額 (見表1),“北海口之棉貨其中有棉布一半、棉紗三分之二運往云南省。”[11]從中可以看出在北海港洋貨進口中,輸向云南的部分占據相當高的比例。

表1:1877~1890年北海進口棉紗與棉布貨值及其占洋貨進口凈值比例表單位:海關兩
在19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由于西南地區的傳統商路受阻,而取道北海暢通且實行低稅率政策,加之北海在西南地區率先開港通商,使得北海港在與西南地區的其他商埠競爭中占據了優勢,在爭取西南腹地中處于有利地位。北海港的腹地范圍首次擴展至云南和貴州,也是近代北海港對西南腹地影響最大的兩個時期。
(二)口岸競爭與北海港腹地的收縮
近代北海港的腹地范圍一直處于動態過程,邊緣腹地范圍的變動表現尤為突出。隨著西南和華南地區的通商口岸因開放數量不斷增長而逐漸密集分布,各口岸之間相互競爭劇烈,北海港的西南經濟腹地通常受到相鄰口岸之間的競爭而出現交叉重疊,北海港對西南經濟腹地的影響力不斷衰減。
清末的梁鴻勛在《北海雜錄》中對此有過一段概述:“自南關劃界后,則云南貨物往來,由港(按:香港)直附海防入河內上保勝而去。及龍州通商,該處貨物,亦由海防而上。此時入口之花紗呢羽,出口之錫板、八角,已漸減落,未幾梧州通商,而廣西南寧、云南來往貨物全無矣。未幾廣州灣租與法人,而高雷屬 (按:廣東省高州府、雷州府)之貨又無來往矣。”[5]6
梁氏提出了19世紀80年代以后西南地區的貿易路線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北海與西南腹地的貿易往來逐漸減少。首先是中法戰爭后,中法兩國于1885年簽訂《越南條約》,對中越兩國實行劃界,隨后位于中越邊境的云南商貿重鎮蒙自開辟為通商口岸,云南的對外貿易路線由北海出海轉向由越南海防出海;其次是中法兩國于1887年簽訂《續議商務專條》,開辟處在中越邊境的廣西龍州為通商口岸,廣西部分地區的貿易路線也改道從越南海防出海;再者是1897年中英兩國簽訂《續議緬甸條約附款專條》,開辟居珠江中游的廣西梧州為通商口岸,對北海的貿易打擊最為嚴重,廣西和云南的貨物大部分都是順珠江經梧州達廣州出海;最后是1899年中法兩國簽訂《廣州灣租借條約》將廣州灣(今湛江)租借給法國,毗鄰北海的廣東省高州和雷州兩地的貿易也“舍棄”北海轉向廣州灣。
從此形成了從中國珠江口至越南紅河口四個港口 (中國廣州、廣州灣、北海和越南海防)競爭我國西南經濟腹地的局面,眾港口的競爭格局對北海港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此西南地區經北海轉口的貿易逐漸由盛轉衰,北海作為西南地區出海通道的地位和影響受到較大的削弱。蒙自和梧州分別是越南海防和我國廣州通向我國西南地區的重要中轉站,從表2可知,由蒙自、北海和梧州三口岸請領子口稅單出入內地貿易數額比較中,北海與它們差距甚大,反映出越南海防和我國廣州在競爭西南腹地中的實力遠遠超過北海。①因廣州灣時屬法國租借地,不入中國海關貿易統計之列,缺乏此部分數據。

表2:1905~1930年梧州、北海和蒙自三口岸各口請領子口稅單出入內地貿易數額比較表單位:海關兩
1.北海港與云南蒙自口岸的競爭
從越南海防溯紅河而上經云南蒙自入境中國是西南地區的一條重要出海通道,蒙自的開埠加大了此通道的貿易量,越南海防因之受益。1887年,清政府與法國簽訂《續議商務專條》,開放龍州和蒙自為通商口岸。北海港的腹地受到很大影響, “原定是取道北海的,現在卻轉到取道紅河”。[6]36“凡外貨自東京至云南、廣西者納中國通商海關進口稅百分之七十,華貨自云南、廣西出口至東京者納通商海關出口稅百分之六十。”[12]105隨著云南和廣西陸路邊境口岸的開放,加之稅率的優勢,使原來由海運經北海進廣西和云南的土貨改道越南海防經廣西龍州與云南蒙自進入。
在北海開港通商前期,出口的錫全部來自云南省,關于它的確切數量記錄始于1884年,其數量的變化在反映北海與云南之間港腹關系的密切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從表3可看出1889年是一道分水嶺,此年正是云南蒙自正式開埠通商的第一年。據1893年北海海關貿易報告記載:“云南所產之錫近往年到本口者尚多,本年竟無,因皆系由蒙自取路安南出口耳。”[13]此后北海出口貨物中鮮見有錫礦。蒙自開埠之后,從蒙自出境順紅河達越南海防成為西南地區尤其是云南和廣西西部地區的主要出海通道。

表3:1884~1904年北海出口錫礦數量變化表 單位:擔
2.北海港與廣西梧州口岸的競爭
珠江是聯接廣州與西南地區的天然黃金商路,北海與廣州相比缺乏“先天”優勢。在北海關十年報告 (1882-1891)里記載:“去年 (按:1890年)稅收減少是由于出口減少,而今年是由于本口岸商業的骨干——進口貨遭到重大損失。產生的原因是西江航線奪去了大量進口貨,該線與內地許多主要商埠通航,而本港是完全沒有這條件的。”[10]24廣西梧州位于珠江中游,是西南地區貨物流向廣州的重要門戶,它的開埠進一步加強了廣州對西南腹地的集散能力。1897年,根據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續議緬甸條約附款專條》,開辟梧州為通商口岸,梧州對外通商后對北海港的影響更甚。
生牛皮和牛角“前數年為 (按:北海港)出口之大宗貨物,多由廣西運來出口,今則假道西河”[14]。從表4可看出1897年梧州開埠后從北海港出口的生牛皮和牛角數量明顯衰減。珠江水系本是西南地區的傳統出海通道,梧州開埠后使北海港的西南腹地尤其是廣西省受到更深程度的分解。

表4:1893-1902年北海出口生牛皮和牛角數量變化表 單位:擔
3.北海港與廣東廣州灣的競爭
1899年,清政府與法國簽訂《廣州灣租借條約》,其租借范圍跨遂溪、吳川兩縣部分陸地和兩縣之間的港灣水域 (即今湛江港),法國把租借范圍的陸地和港灣總稱為廣州灣。[15]25北海與廣州灣分別位于雷州半島的西側和東側,兩者的腹地范圍大部分都重疊。
自《廣州灣租界條約》簽訂后,廣州灣成為法國管治下的自由貿易港,北海港口貿易再次受到削弱。在廣州灣,“貨物入口向不課稅”,“向不設立洋關,以稽查貨品入境”,僅在租借地交界處設常關征繳,但常關征收手續籠統,“且更可以情面而出”[16]670。商人因此趨之若鶩,“高州府之西出口來北海及北海入口往高州之貨多系道經安鋪,自廣州灣立定章程整頓商務,不但高州之東來往貨物由該埠轉運,即西邊亦然,所以由安鋪出入之貨未免被其挽奪,且廣西玉林運貨來北 (按:北海)道途焉遠,甘愿往南直赴廣州灣,即玉林往梧州之貨咸亦由南路轉赴廣州灣。”[17]北海出口的“煙葉多系高州府土產”[17]。從表5觀其十年間數量的變化可以看出高州府的貨物流向轉變。廣州灣的自由港制度使它迅速成為西南地區的又一個重要的出海口,北海因距廣州灣最近而受到的沖擊最大,曾經是兩地共有的邊緣腹地出現了“一邊倒”轉向廣州灣。

表5:1898~1907年北海出口煙葉數量變化表 單位:擔
(三)北海港的邊緣腹地與核心腹地
隨著時勢的變遷,北海港的腹地范圍發生劇烈的變化。云南蒙自的開埠、滇越鐵路的開通,北海港對云南和廣西西部地區的影響力下降;珠江商路的暢通、梧州的開埠,北海港與桂、滇、黔三省的貿易量大為減少;廣州灣開辟為自由港,對北海港的沖擊更是雪上加霜,不但失去廣東省的高州府和雷州府腹地,而且北海港所在的廉州府部分地區也受到影響。
可以看出,西南地區是多個口岸的共同腹地,這些口岸的腹地出現交叉重疊,因此對腹地的競爭尤為激烈。在不同時期各個口岸對西南腹地的影響程度不一,波動性較大。北海港對西南腹地影響較大的兩個時期是太平天國運動興起時期和19世紀80年代。除此之外,雖有短期的高潮但大部分時期北海港都在激烈的口岸競爭中處于低潮狀態。因此,西南地區僅是北海港的邊緣腹地。
北海港的核心腹地何在呢?查北海海關貿易報告中的《海關出口大宗土貨統計表 (1880年至1919年)》,每年均列入其中的土貨有豬、干魚、咸魚、花生餅、花生油、水靛、熟皮、八角、八角油、絲、赤糖和白糖,再查《常關出口大宗土貨統計表 (1904年至1919年)》,每年均列入其中的土貨有瓦器、爆竹煙花、木耳、牛皮膠、神香末、堿水、藥材、上等紙、次等紙、松香、酒、醬油、茶子餅和白糖。
《北海雜錄》對北海的主要出口土貨及其主要來源地有這樣的記載:“以靛、糖為大宗。水靛多出合浦屬之寨圩、張黃、福旺、小江、靈山之武利,廣西之博白等處。糖出合浦屬之西場、張黃、武利、北塞、那思、伯勞等處。糖有赤白二種,然白糖稱武利,赤糖稱欽州。其次厥惟海味,若魷魚、墨魚、大蝦、咸魚等;此外生豬、生牛,均出本地;元肉亦一大宗,以廉屬為最;牛皮、水牛皮、雞鴨毛出于廉、欽;煙葉以高州屬之安鋪、青平兩處為最多;黃絲出于小董,該處距欽州九十里;又合浦屬之常樂、石康等處,均有所出。花生油亦出口之一大宗。”[5]9-10
這些出口土貨大部分是近代北海出口貿易當中貨源較為持久穩定的貨物,提供這些貨物的區域范圍大致是清代廉州府全境以及南寧府、玉林州、高州府、雷州府的部分地區。近代這個區域的對外貿易大部分經過北海港進出口,至1919年,“所有本省 (按:廣東省)附近北海各屬暨廣西邊界一帶各類土產等物皆系由本口轉運出洋。”[18]可以判定,這個區域就是北海港的核心腹地。
四、北海港對西南地區貿易的影響
以上論述了西南地區的滇黔桂三省是北海港的邊緣腹地,進而再追問北海港究竟對滇黔桂三省貿易的影響有多大呢?北海在滇黔桂三省的對外貿易中占據什么樣的位置?
(一)北海港對廣西貿易的影響
廣西的貿易出海通道歷來有兩條:一是從水路或陸路南下北海港;二是順珠江黃金水道東去廣州。特別是珠江興起輪船航運之后,廣西對外貿易取道廣州更是大勢所趨。從1900年開始梧州至南寧之間已經開通輪船運輸,以往珠江航運依靠人力和風力,旺水期木船由南寧順流而下,6天至8天便可抵梧州,逆水而上則需25至30天才能到達,而輪船往返僅需5天,輪船運輸的出現使航運受季節風向和水流方向影響的狀況大為改觀。[19]117、134從表6數據統計可看出:廣西的對外貿易大部分是通過珠江匯向珠三角地區;梧州開埠之后西南方向的龍州和北海路線貿易量所占份額較小。此時,受北海輻射和吸納的地區僅有西江上游的南、太、泗、鎮四個府以及南流江穿越的玉林州。

表6:1898~1917年北海、龍州、梧州、廣州四口岸請領子口稅單直銷廣西洋貨貨值表單位:海關兩
(二)北海港對云南貿易的影響
關于云南的對外貿易交往,英國人柯樂洪 (Mr,Colquhoun)曾有過一段概括:“云南地形如此復雜,沒有一條商路能包攬該省貿易。他們抱怨說:‘所有能夠到達昆明的道路都漫長、艱險、昂貴,只能或大或小地供應云南某一區劃 (Part),而與他處無緣。云南高原各部由最相鄰的周邊低地供應商貨。四川貨在相當貧窮的滇北、滇東北和黔北流通;百色供應滇東、滇中及黔南;東京(今越南北部)與滇南、滇中聯系。緬甸與滇西南和滇西貿易,從商業角度來看,這大約是該省最理想的貿易對象了’。”[20]24特殊的自然環境,落后的生產力,其影響一是致使云南商業落后;二是限制了北海對云南的貿易輻射。按照柯氏的說法,北海在云南的腹地也僅是經百色通達的滇東、滇中地區。
云南蒙自與紅河相近,1885年岑毓英曾述稱:“滇省陸路十站可達蠻耗,由紅河下至河內入海,而粵而滬而津,四達無滯。”[21]766從地理位置上看,云南省大部分地區的對外貿易取道紅河達海防與走西江達北海出海比較,前者更占優勢,以地處滇省偏東的省會昆明為例,由昆明至海防的貿易路線“海防至河內,汽船運一日,河內至老街,舢板運十二日,老街至蠻耗,舢板運七日,蠻耗至蒙自,牲口運十二日,共計三十日”。而由昆明至北海的貿易路線“計北海至南寧十四日,南寧至百色十七日,百色至剝隘三日,剝隘至廣南八日,廣南至云南府 (按:昆明)十三日,共計五十四日”[22]。蒙自開埠通商后,云南尤其是滇南地區的對外貿易多經紅河出越南海防再轉至各地。
1910年滇越鐵路全線通車,這就極大改變了云南對外貿易的路線、規模和范圍。“來自香港、中國南部各港口的……主要貨物,都先存在海防,然后運往云南,根據需要再從云南運一部分到貴州、四川。相反,從云南出口運往以上這些港口……的貨物,則逆向運出。”[23]49、110
與其他通商口岸相比較,北海對爭奪云南腹地的競爭力較弱,與梧州、廣州和蒙自差距甚遠(見表7)。蒙自在近代云南的對外貿易中影響最為重要,大部分對外貿易活動通過南面的這條商路進行。

表7:1898~1917年北海、梧州、廣州、蒙自四口岸請領子口稅單直銷云南洋貨貨值表單位:海關兩
(三)北海港對貴州貿易的影響
關于貴州的對外貿易有三大路線:一是經岳州、漢口和重慶東出長江至上海;二是南下珠江至北海或者經梧州達穗港澳;三是入云南省取道蒙自出越南。其中以第二條商路的貿易量為最大(見表8),從貴州下珠江有三條水路可走,北路:榕江——融江——柳江——黔江;中路:北盤江/南盤江——紅水河——黔江;南路:馱娘江——右江——邕江。從這三條水路走向分析,北路和中路起源于貴州,其支流遍布貴州與廣西接壤的大部分地區,且均由黔江與潯江交于桂平注入珠江干流,從桂平取道梧州較之北海更加便捷。而南路起源于云南,僅流經貴州興義府一地,商品達南寧后再次分流部分從梧州出,真正流入北海的少之又少,比較表8中北海、梧州和廣州等口岸請領子口稅單直銷貴州洋貨貨值便可得到印證。[8]19

表8:1898~1917年北海、梧州、廣州、蒙自四口岸請領子口稅單直銷貴州洋貨貨值表單位:海關兩
通過把北海港分別與西南地區的其他出海口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北海港對爭取西南腹地的競爭力較弱,處于劣勢地位。北海港對腹地的影響呈空間距離由近及遠遞減,大體上符合距離衰減規律,即相隔越遠,影響越小。北海港對邊緣腹地——滇黔桂三省而言,對廣西的影響相對較大,而對滇、黔兩省的影響是相當弱小的 (見表9)。

表9:1898~1919年北海與各省內地之間進出商品 (請領三聯單部分)貨值表單位:海關兩

資料來源:《中國舊海關史料》中各相關年度的北海海關貿易報告。
五、結論及啟示
近代北海港崛起于太平天國運動興起時期,1877年北海正式開港通商后貿易日益繁盛。19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是近代北海港對西南地區影響最大的兩個時期,影響的范圍主要包括廣西西部和南部、云南的東部以及貴州的南部。北海港的核心腹地范圍包括廣東省廉州府全境,高州府、雷州府的部分地區以及廣西省南寧府、玉林州的部分地區,而西南地區的滇黔桂三省僅是北海港的邊緣腹地。
北海港與越南海防、廣東省的廣州和廣州灣都是西南地區對外經濟交往的出海口,北海港對爭取西南腹地的競爭力較弱,處于劣勢地位,影響的時期較短,范圍較小。北海港對邊緣腹地——滇黔桂三省而言,對廣西的影響相對較大,而對云南和貴州兩省的影響是相當弱小的。因此,對于“近代北海港是大西南的門戶”的模糊定性,認為北海港對西南腹地的影響時空范圍擴展至近代的全過程、西南地區的全境,實質上是夸大了近代北海港對西南地區貿易的影響。
從中國珠江口至越南紅河口沿岸的港口是我國西南地區空間距離最近的出海通道,其戰略地位當不言而喻。該區域港口對中國西南經濟腹地的競爭格局形成于近代,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近代北海港興衰交替和腹地變遷的歷史昭示著:交通和稅率是影響港口競爭力的兩個重要因素,貿易路線的選擇通常都是遵循交易成本最低的原則。
[1]李志儉.試論北海港的歷史地位[J].廣西地方志通訊,1985(2).
[2]李富強.西南——嶺南出海通道的歷史考察[J].廣西民族研究,1997(4).
[3]廖國一.近代環北部灣沿岸的對外開放及其啟示[J].廣西民族研究,1998(4).
[4]吳小玲.從開埠到開放:一百年間廣西北部灣地區對外通道透視[D].桂林:廣西師范大學,2003.
[5](清)梁鴻勛.北海雜錄[G]//北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北海史稿匯纂.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6]中國海關北海關十年報告(1892-1901年)[G]//北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北海史稿匯纂.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7](民國)陳公佩等修,陳德周纂.欽縣志·民生志·商業.桂林圖書館據四川省圖書館藏民國35年石印本抄錄,1975.
[8]麥正鋒.近代北海港口貿易研究(1877—1949)[D].桂林:廣西師范大學,2008.
[9](英)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國對外貿易史資料[M].上海:海關總稅務司統計科,1931.
[10]中國海關北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年)[G]//北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北海史稿匯纂.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11]光緒十五年北海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M]//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舊海關史料:第15冊.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
[12]朱進.中國關稅問題[M].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
[13]光緒十九年北海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M]//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舊海關史料:第21冊.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
[14]光緒二十五年北海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M]//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舊海關史料:第30冊.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
[15]甄裕平,何灼興.南海濱城——湛江[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16]佚名.北海商業冷淡之原因[N].廣州民國日報,1929,12(3)//北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北海史稿匯纂.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17]光緒二十六年北海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M]//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舊海關史料:第32冊.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
[18]中華民國八年北海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M]//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舊海關史料:第86冊.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
[19]《廣西航運史》編審委員會.廣西航運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20]英國殖民部檔案(C.O.129,286).云南——它的資源、貿易及商路.見:王福明.近代云南區域市場初探(1875-1911)[J].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2).
[21]張振鹍.中法戰爭:第2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5.
[22]新纂云南通志·商業考:第144卷.見:袁國友.近代滇港貿易問題研究[D].昆明:云南大學,2002.
[23](法)主文元.法屬印度支那與中國的關系[M].云南省歷史研究所,1979年中譯本.見:賀圣達.近代云南與中南半島地區經濟交往研究三題[J].思想戰線,1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