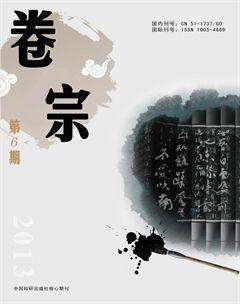論元電影《開羅紫玫瑰》的美學意蘊
摘 要:元電影蘊含著一般電影所無法承載的美學層面的意義,現實與虛構的干涉,現實與虛構無法共存的問題,新的時間秩序——時間可逆,自我主題意識等等,在元電影這一特殊的類型中都有所指涉和反映,挖掘元電影的美學意蘊,對元電影、對電影這種藝術都將會有更深層次的認識。本文將從幾個方面來探究元電影《開羅的紫玫瑰》的美學意蘊。
關鍵詞:《開羅的紫玫瑰》;美學意蘊;真實;虛構
電影作為一種藝術類型,與科技的不斷發展是一體的,用科技手段營造的光影的虛擬世界,給人以一種特殊的美的感受。電影有許多類型,元電影是電影中比較特殊的一類,元電影不僅從拍攝手法上,從表現形式上帶給觀眾一種不同于一般電影的感受,而且表現的內容、主題中也包含著深刻的美學意蘊。1985年伍迪·艾倫(Woody·Allen)導演的《開羅的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就是一部較為典型的元電影。本文將從以下幾方面來看元電影《開羅的紫玫瑰》的美學意蘊。
1 電影的“去”幻覺化,“去”神秘化
常規電影的目的在于制造幻覺,讓觀看者卷入其中,身臨其境。但同時,電影有它自身的界限——在這部電影中就是銀幕,這個界限抗拒和排斥著觀眾,使電影中的人物無法進入現實,現實中的人物也無法進入電影中的世界,這個界限時刻在提醒觀眾:我們屬于兩個不同的世界。電影中電影院上映的《開羅的紫玫瑰》就是一部常規電影——向那些在現實生活中不滿意的觀眾展示奢華浪漫的生活,借此來吸引觀眾。而當電影中有一個敘述者的聲音出現的時候,就是打破幻覺的時刻。顯然,敘述者聲音的出現是不和諧的,它打破了幻覺,將觀眾重新拉回現實,保持與電影的距離;但這個聲音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讓神秘化的東西變得不神秘。電影中的世界由于銀幕這個界限的存在神秘化、陌生化,在《開羅的紫玫瑰》中,男主角Tom Baxter從對Cecilia說話的那刻起,到走下熒幕的那一刻,電影變得不再神秘,現實和虛幻的界限變得模糊。而這個揭密的過程帶給觀眾的震撼一如電影所呈現的:一個女觀眾尖叫著暈了過去。Tom Baxter走出電影,進入現實,帶走了Cecilia,與現實生活和現實中的人們發生了多種干涉。交涉的過程是相互的,Tom走進現實生活后,又帶著Cecilia進入了電影中的虛擬世界。元電影打破了虛構性作品的封閉性,對話已不只是由角色來完成,對話還發生在多個層面:角色多重身份的自我對話,結構的對話,時間的對話,形式與內容的對話。角色的自我對話在《開羅的紫玫瑰》里非常明顯:Tom和Gill的對話,一個被創造的角色和演員之間的對話;電影文本的自我對話:Tom Buster離開后,原先電影的劇情也無法繼續進展下去,各個角色們停止了演戲,脫離了原本的發展路線,等待著Tom回來。在等待的過程中,他們與觀眾發生了對話,并且說出了自己心目中對于電影的看法。“這是一個關于追求自我實現的男人的故事”、“一個復雜心靈受創的故事”、“是金錢對真愛產生影響的故事”。Tom跟妓女在一起時說的那段話:“我在想一個很深奧的問題,我在思考生命的各個方面,死亡的終結,和真實世界、電影世界和那些閃動著的身影之間,幾乎是魔幻般的差異。”從電影看電影自身,這正是元電影自我主題意識的體現。
2 虛構與真實的界限
虛構與真實究竟如何相互介入,這個媒介或者通道是什么?在《開羅的紫玫瑰》中,放映機承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現實和虛擬的通道。由于這個放映機的存在,虛構與真實的世界被聯通,虛構與真實的界限開始模糊。我們可以注意到,當女領座員對經理說:“或許你應該把放映機關掉。”一個角色驚慌失措地說:“不不不,你不能關掉放映機,一關掉我們就會消失,什么都沒有。” 傳統敘事摹寫現實,與現實同樣假定時間不可逆轉,假定只有一種可能能成為最后的結果。而《開羅的紫玫瑰》則構建了另一種時間秩序------時間可逆,這樣就帶來多種結果可能性。電影中按照劇情Tom最后應該和kitty Hennes結婚在一起,然而,當他從電影里走出來后,“他不用參加婚禮了”“他自由了”,原先預設的結果被改變了;而當Cecilia沒有選擇他的時候,他依舊可以重新回到電影中去,再次改寫結果。最后當Cecilia選擇了Gill,也就是選擇了現實,讓將Tom回去的時候,Tom重新進入電影的那一瞬間,一切都回到了原點,回到了一種正常的狀態,也就是說,一切都重新開始了,又可以演繹任何一種可能性。《開羅的紫玫瑰》的時代過去了,另一部電影接替上映,從某一角度來看,可以說,現在與過去沒有分別。怎么不能說回到了過去又或者是現在就是過去呢?“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生活就是這樣循環往復,一次次回到起點,然后演繹無限的可能性。電影的結局是Cecilia依舊在看電影的畫面,放映機開始工作的那一瞬間,現實與虛構的通道再次被打開,虛構與真實的界限有可能再次模糊。法國博德里亞爾說:“影像不再能讓人想象現實,因為它就是現實。影像不能再讓人幻想實在的東西,因為它就是其虛擬的實在。”應該這樣理解,現實與虛擬很難被清晰的定義。不同的視角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一切都是真實,或者根本沒有真實。
3 真實與虛構的共存問題
Cecilia愛上了電影里的男主角,愛上了電影里離她現實生活——一個小飯店的女服務員,經常犯錯被責備,回家要面對粗暴并且經濟狀況很差的丈夫——十分遙遠類似“白日夢”似的完美的世界。Woody Allen讓男主角魔術般地走下熒幕并且以一種不真實的方式愛上了Cecilia。穿著不合時代的服裝,用著“偽鈔”,開車時以為不用鑰匙就能開,深情一吻后做愛前有淡出畫面,觀眾似乎已經明白,他終究不屬于現實。而Cecilia面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真實但是并不完美的Gill,還是完美但卻是虛構的Tom。真實和虛構是一種本質的屬性,不是通過學習就能改造的。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從被創造的那刻起就已經被規定了。對于Tom來說,兩個合寫劇本的作家就是他的上帝,是“一切事物的情理”。Tom和Monk打架的時候,Tom說,“有膽量是寫在我的角色里的”,打架之后,“一點痕跡都不會留下,不疼也不流血,頭發也沒亂”,Tom笑著說“這就是愛幻想的好處”,而Cecilia說出了實質:“這就是你永遠會在銀幕上生存的原因。”現實與虛構是無法共存的。電影還有一個極具隱喻意義的鏡頭,當Cecilia進入電影中時,歌星kitty Hennes觸碰了Cecilia的時候,她昏了過去。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虛構的和真實的可以相互介入,但是是永遠不能共存的。最后Cecilia選擇了Gill而不是Tom,拋開一切情感或者其他外部原因,本質原因就是因為現實與虛構無法共存,Cecilia和Gill都屬于現實世界,Tom只屬于虛構的電影世界。就影片里電影院放映的《開羅的紫玫瑰》來說,它作為一部電影,有一個非常完整的系統,有其自身的構成部分,圓滿的故事情節,人物角色,各個部分構成了一個完美的世界。然而當Tom出來或者Cecilia進去之后,一切協調都被打破了,這個完整和和諧被打破,兩邊的世界都認為這是一個大麻煩。這部電影也完全符合歐洲美學觀的基本原則是:在藝術作品與觀賞者之間存在著一個外在和內在的距離。它意味著一件藝術品自身構成一個封閉的微觀世界,尤其必須遵循自身的規律,從而使它無法成為現實的延伸。同樣,電影作為一件藝術品,終究無法成為現實的一部分。真實與虛構,永遠處于矛盾之中,永遠處于對立面。伍迪·艾倫的自反電影《開羅的紫玫瑰》很好地表現了他的傾向:無意使電影神圣化、神秘化,反而使電影生活化、日常化。不斷地從電影本身反觀電影,不再刻意給觀眾營造一種主觀的審美體驗,而是反映了一些客觀事實,進而討論真實與虛構的問題,從而使這部電影具有了深刻的內涵和美學意蘊。
從以上三個方面,本文討論了元電影《開羅的紫玫瑰》的美學意蘊。作為一種獨特的電影類型,元電影還存在著更深層次的美學意蘊,值得觀眾去發掘。
參考文獻
[1]楊弋樞:《電影中的電影——元電影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李恒基、楊遠嬰主編:《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三聯書店,2006.
作者簡介
王倩齡,女,浙江樂清人,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