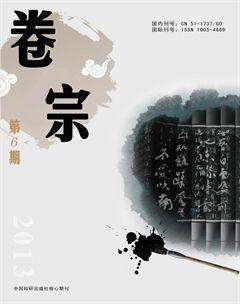領(lǐng)導(dǎo)干部應(yīng)拿起筆桿子
陳慶
一段時期以來,領(lǐng)導(dǎo)干部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即官員寫作,逐漸發(fā)展成為一種獨(dú)特的文藝現(xiàn)象。其作品的數(shù)量由少積多,質(zhì)量日益提高,影響不斷擴(kuò)大,堪稱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一大亮點(diǎn)。特別是2010年武漢市紀(jì)委書記車延高以詩集《向往溫暖》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xué)獎以來,領(lǐng)導(dǎo)干部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引起了更為廣泛的社會關(guān)注。
綜觀領(lǐng)導(dǎo)干部的優(yōu)秀文學(xué)作品,既有反映社會生活、描摹人情世態(tài)、洞悉人生至理的小說,也有或以懷古述往啟迪今人、或借他山之石鏡鑒當(dāng)下、或?qū)び挠[勝而有所興寄的散文;既有昂揚(yáng)正氣、催人奮進(jìn)的報告文學(xué),也有造型造境、言情言理的詩詞。這些文學(xué)創(chuàng)作從現(xiàn)實生活的深處走來,糅合著理性的思考與感性的表達(dá),把優(yōu)美的藝術(shù)形式與深刻的社會思想冶于一爐,呈現(xiàn)出十分鮮明的特點(diǎn)。
首先,文化視野較為開闊。領(lǐng)導(dǎo)干部的身份決定了官員寫作者的生活經(jīng)歷不同于專業(yè)作家們,這種特定的生活歷練、專業(yè)背景以及相應(yīng)的知識結(jié)構(gòu),決定了其創(chuàng)作具有闊大的文化視野這一鮮明特點(diǎn)。一是能夠以象見意、才識并舉地體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人間情懷。如馬凱的《減字木蘭花·千年交替夜》:“暮云送日,一頁翻過千歲史。朝旭驚宵,幾縷迎來世紀(jì)交。花開花敗,盡閱滄桑天未改。鐘抑鐘揚(yáng),再換人間路且長。”作品不僅具有耐人尋味的韻律和美感,而且最為可貴的是并不流連駐足于文字構(gòu)成的光與色,而且能夠由博返約、舉重若輕地表現(xiàn)出一種高于常人的豪邁氣勢與遠(yuǎn)見卓識。而李東東的詞賦創(chuàng)作,在文學(xué)性與歷史性融通中,涵攝各路信息,凝聚了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對時代的深入思考。“威武之師,百煉成鋼。摧鋒陷陣,拔關(guān)奪隘,悲歌慷慨,龍血玄黃。曾挽國之危難,曾拯民于倒懸,腳踏祖國大地,背負(fù)民族希望。風(fēng)云開合,壯士請纓,生當(dāng)人杰,死亦國殤。”(《八一賦》)二是呈現(xiàn)出大敘事的品格。往往能夠從厚重的歷史背景生發(fā)開來,從而使作品獲得了鮮明的時代性與厚重的歷史感。“天地滄桑皆塵土,世上何人稱不朽?不朽二字是精神,獨(dú)把不朽留與君。”這是唐雙寧在抒情詩《周總理逝世三十周年祭》中的句子,這首詩始終把強(qiáng)烈的個人的情感灌注在詩行當(dāng)中,藝術(shù)地解讀歷史,文情并茂,折射出樸素的理性思考,使我們得以走進(jìn)歷史深處,與作者的心靈一起律動。田聰明的散文《媽媽的心》深情地回憶了與母親一起生活過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寄托了對母親無盡的思念和拳拳的感恩之心,在作者充滿濃濃溫情與淡淡憂傷的文字背后,在浸透著懷念與感激之情的敘述當(dāng)中,一個慈愛而又堅強(qiáng)、質(zhì)樸而又明理、平凡而又偉大的中國母親形象躍然而出。
其次,現(xiàn)實主義特征最為突出。從整體看,現(xiàn)實主義基本上是貫穿官員寫作的一條主線,無論是以真摯樸實為基調(diào)的美學(xué)風(fēng)格,還是以天下憂樂為己任的擔(dān)當(dāng)意識,現(xiàn)實主義始終是主領(lǐng)內(nèi)蘊(yùn)、涵詠萬物的精神品格。其一是具有高度的責(zé)任意識與反思精神。孟學(xué)農(nóng)的抒情詩《心在哪里安放?》中,“融入吧,像細(xì)小灰塵一樣,冉冉升起悄然落下,覆蓋在祖國的土地上,心,不需要安放,只要在難忘的地方,有山在呼喚,有水在蕩漾,心,就在揮灑的過程中——發(fā)光、閃亮!”在對于人生的深切思考中,作品傳神地表達(dá)出詩人無論在順境還是逆境中都愿意把心交給祖國和人民的心跡,全詩始終都蘊(yùn)蓄著充沛的真情,語言樸素卻自有一種動人的力量。劉上洋的散文《江西老表》在歷史與現(xiàn)實交匯的雙重視野中,在縱向觀照與橫向比較中,既有對江西老表性格由衷的贊嘆和欽佩,更有對其劣根性的冷靜分析和深刻反思。在他看來,根本原因就在于江西老表的觀念和性格當(dāng)中的保守和陳舊的一面,因而江西老表要重新崛起,就必須沖破舊觀念的藩籬,改造和重塑自我。其二是深廣的人文主義情懷。丹增的散文《我的高僧表哥》以樸實無華的筆調(diào)為我們勾勒出一位智慧、虔誠、善良的藏族高僧。表哥品行高潔,唯信仰而終其一生;表哥歷經(jīng)坎坷,觀世閱人但求向真向善。表哥有如雪域高原一樣淳樸的人格魅力,使其形象猶如聳立于眼前的圣潔雪峰,傳遞出靈魂的感動。梁衡的歷史散文《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把筆墨集中在林則徐雖蒙冤戴罪被發(fā)配新疆但仍不忘報國的種種表現(xiàn),生動地詮釋了“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所凝結(jié)的分量。
第三,藝術(shù)水平不斷提高。客觀地說,官員寫作的總體藝術(shù)水平從趨勢上看,是不斷上升的,而有些作品則達(dá)到了很高的藝術(shù)水準(zhǔn),可與專業(yè)創(chuàng)作并駕齊驅(qū)。王巨才的散文《走馬平塘》濃縮精煉,層次分明,文詞清麗,詩意盎然。在他眼中,平塘的美是“在于它的天生麗質(zhì),不事雕琢”,而平塘的民居之美則是“黛瓦蒼臺,歷經(jīng)歲月風(fēng)霜,滿布滄桑古跡的布依族木樓”,這種美是縈繞于天地間的大美,以至于“遠(yuǎn)遠(yuǎn)望去,依稀有一種路無拾遺、夜不閉戶的古風(fēng)傳遞而來”。王躍文的《國畫》既是官場小說的濫觴之一,又為這一類型的小說創(chuàng)作樹立起較高的藝術(shù)標(biāo)準(zhǔn)。《國畫》深刻而傳神地描寫了都市的官場世相圖,塑造了朱懷鏡這一鮮明的藝術(shù)形象,無論是對語言和敘事技巧的運(yùn)用,還是在反映社會背景的深刻程度上,都達(dá)到了較高的水準(zhǔn)。
當(dāng)前,官員寫作無論是在數(shù)量上還是質(zhì)量上均交出了一份較為出色的答卷,不僅有大批作品問世,而且也不乏引人注目、膾炙人口的精品佳構(gòu)。當(dāng)然,不可否認(rèn),圍繞著官員寫作這一特定的文學(xué)現(xiàn)象,爭議一直存在,其中甚至不乏一些頗為極端的觀點(diǎn)和看法。
有人認(rèn)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來加以精心構(gòu)思,既耗費(fèi)時間又要付出極大的精力,可謂勞心費(fèi)神。而官員特別是領(lǐng)導(dǎo)干部在任期間最為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全力以赴做好本職工作,而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勢必會分散精力,影響工作。這種擔(dān)心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細(xì)究起來,就會發(fā)現(xiàn)官員寫作與本職工作其實并不沖突。事實上,在我國官員寫作的傳統(tǒng)由來已久,身兼政治家與文學(xué)家二任于一身,“學(xué)而優(yōu)則仕”在古代的官員中幾乎成為一種自覺的“慣例”。中國古代的官員本身便是文學(xué)大家的數(shù)不勝數(shù),屈原、賈誼、曹操、李白、杜甫、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劉基、紀(jì)曉嵐……一直到當(dāng)代,毛澤東同志在詩詞創(chuàng)作方面的造詣堪稱一流,朱德、陳毅、董必武、葉劍英等同志的詩詞創(chuàng)作也有很高文學(xué)價值。這里主要存在一個怎么辯證地看待和處理工作與寫作的關(guān)系問題。應(yīng)該說,把兩者關(guān)系解決得好就會相得益彰,實現(xiàn)兩不誤、兩促進(jìn)。領(lǐng)導(dǎo)干部們把在工作和生活當(dāng)中的所見聞所思所想筆之于書,既能把一些好的想法、經(jīng)驗、觀點(diǎn)寓于創(chuàng)作之中,使其影響進(jìn)一步擴(kuò)大,讓更多的人通過審美得以分享這些從大量實踐中提煉出的經(jīng)驗和思想,使人們在享受美的同時也有所啟迪、有所收獲。而對于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領(lǐng)導(dǎo)干部而言,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過程本身就是對行政工作更為深層的審視和反思,這無疑有助于總結(jié)工作當(dāng)中的得失,鑒往知來,厘清工作思路。當(dāng)然,這種思考和創(chuàng)作必須始終遵循文學(xué)本身的規(guī)律,以藝術(shù)的方式加以表達(dá)。
有人認(rèn)為,官員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多是嘩眾取寵,裝點(diǎn)門面,甚至?xí)呱瘮。斐韶?fù)面影響。不可否認(rèn)的是,有極少數(shù)的領(lǐng)導(dǎo)干部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目的并不單純,他們要么借文學(xué)創(chuàng)作來大肆炒作自己,以期獲取政治資源,要么把文學(xué)創(chuàng)作當(dāng)成提高和顯示身份的砝碼,附庸風(fēng)雅,以期揚(yáng)名立萬,更有甚者干脆把文學(xué)創(chuàng)作當(dāng)成斂財?shù)墓ぞ撸云诎l(fā)家致富。事實上,凡是抱著類似私心雜念的人,其作品的藝術(shù)水準(zhǔn)大都差強(qiáng)人意,無論是美學(xué)境界還是思想內(nèi)涵都乏善可陳、淺薄庸俗,因而大都難逃“言之無文,行之不遠(yuǎn)”的命運(yùn)。必須看到,絕大多數(shù)的領(lǐng)導(dǎo)干部之所以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除了自覺的社會擔(dān)當(dāng),創(chuàng)作主體本身產(chǎn)生的難以遏抑的創(chuàng)作激情也不能忽視。王躍文在談到自己創(chuàng)作的初衷時說:“我想把我的體會通過一種東西表達(dá)出來,寫小說,是我能夠找到的最好的方法。”因此,官員寫作的本質(zhì)就是創(chuàng)作主體有感而發(fā),將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人生閱歷上升到思想的層面上,用藝術(shù)形式“加工”成文學(xué)作品。從構(gòu)思、創(chuàng)造、呈現(xiàn)到接受這一系列的創(chuàng)作過程無一不是嚴(yán)格遵循著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只是因為創(chuàng)作主體是領(lǐng)導(dǎo)干部這一特定群體,而使作品呈現(xiàn)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特點(diǎn)。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與專業(yè)作家的創(chuàng)作相比,官員寫作的崛起具有別樣的重要意義。一是有助于提高執(zhí)政能力。鄧小平同志曾經(jīng)指出:“拿筆桿是實行領(lǐng)導(dǎo)的主要方法,領(lǐng)導(dǎo)同志要學(xué)會拿筆桿……實現(xiàn)領(lǐng)導(dǎo)最廣泛的方法是用筆桿子,用筆寫出來傳播就廣,而且經(jīng)過寫,思想就提煉了,比較周密。”的確,領(lǐng)導(dǎo)干部豐富的政治生活、人生閱歷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豐厚養(yǎng)料,同時對這些素材進(jìn)行藝術(shù)加工、創(chuàng)造,又能以一種獨(dú)特的視角加深對政事、生活、人生的理解和領(lǐng)悟,鍛煉和提高邏輯思維能力、理解判斷能力,從而有效地提升為官理政的綜合素養(yǎng)。二是起到積極的示范作用。領(lǐng)導(dǎo)干部帶頭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無疑有助于推動在全社會形成閱讀、寫作的良好文化氛圍,有助于樹立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費(fèi)理念,有助于引導(dǎo)廣大黨員干部擠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學(xué)習(xí)和思考,不斷拓展知識、開闊視野、提高能力。特別是對于我們黨提出的建設(shè)馬克思主義學(xué)習(xí)型政黨這一戰(zhàn)略任務(wù),必將起到積極的作用。三是有助于從政者養(yǎng)成健康的情趣。文學(xué)具有育德勵志、陶冶情操的功能,領(lǐng)導(dǎo)干部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利于養(yǎng)心益智、砥礪精神、慰藉心靈,有利于豐富精神世界,提高人文素養(yǎng)。此外,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需要平等交流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讀者不會因為作者身居高位而放棄評價的權(quán)利,因而不免會聽到一些逆耳之音,這對于領(lǐng)導(dǎo)干部保持清醒是大有益處的。總之,為官與為文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相互促進(jìn)、相互深化的。
我們在肯定官員寫作的同時,并不能只看成績,回避不足。官員寫作要想不斷前進(jìn),“再上層樓”,就必須高度重視并且很好地解決當(dāng)前兩個較為突出的問題。
一是在藝術(shù)性方面,文學(xué)創(chuàng)作強(qiáng)調(diào)的是藝術(shù)魅力和文學(xué)性,無論是多么偉大的思想、多么震懾靈魂的情感,都只能通過審美來表達(dá),用藝術(shù)的魅力來感染人、打動人、教育人。因此,藝術(shù)性在文學(xué)作品的價值構(gòu)成當(dāng)中居于首要地位,失去了這個基本要素,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意義將不復(fù)存在。以此反觀當(dāng)前的官員寫作,不難發(fā)現(xiàn)尚有為數(shù)不少的作品藝術(shù)價值不高,語言欠缺雕琢,缺乏韻味和個性,顯得千部一腔;意象提煉還不夠精粹、集中,缺乏神韻,因而難以營造出自然傳神、韻味悠遠(yuǎn)的意境;人物形象面目模糊,既不具備典型性也沒有予人深刻印象的閃光點(diǎn),顯得千人一面。此外,藝術(shù)形式還比較單一,基本上以現(xiàn)實主義風(fēng)格為主,缺乏多元的藝術(shù)手法。考察文學(xué)史,就會發(fā)現(xiàn)歷來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求新求變大都從藝術(shù)形式上進(jìn)行探索和突破,并由此不斷深化,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學(xué)變革,有力地推動了文學(xué)的發(fā)展。
二是在思想性方面,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和思想開掘能力的作家必須深入生活又不拘泥于生活,能夠以理性的思考和獨(dú)立的判斷審視生活,提供發(fā)聾振聵的思想,成為“引導(dǎo)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文學(xué)才能成為人們的精神家園。真正的文學(xué)并不僅止于娛樂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相反追求高尚的情調(diào)與思想,使真善美的高度融合,最終讓人的娛樂本性在審美中升華,才是最終的旨?xì)w。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必定是把感人肺腑的道德內(nèi)蘊(yùn)和超拔的精神向度巧妙地溶解于審美價值當(dāng)中,從而使讀者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共鳴,得以澡雪精神、啟人深思。以此鏡鑒當(dāng)前的官員寫作,必須承認(rèn)的確還存在思想價值不高,終極關(guān)懷不夠的問題。以官場小說創(chuàng)作為例,近年來的確產(chǎn)生了諸如《國畫》、《人道》、《人精》等既被專家叫好又受市場追捧的優(yōu)秀作品。但也不能否認(rèn),還有為數(shù)不少的官場小說的價值取向產(chǎn)生了偏離,它們似乎僅僅滿足于揭露問題,不厭其煩地暴露官場的種種黑幕、一擲千金的豪奢和令人咂舌的腐敗現(xiàn)象。這些作品不僅對問題深入剖析,只是淺嘗輒止、敷衍了事,只是停留于簡單的揭露丑惡,完全屈從于市場法則,把文學(xué)創(chuàng)作簡單地視作一種“消費(fèi)”,更為嚴(yán)重的是對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和腐敗分子不是譴責(zé),而是打著“還原人性”、“更加真實”的招牌,給予同情甚至是某種程度的認(rèn)同。總之,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要么僅僅關(guān)注藝術(shù)形式,把文學(xué)作品變成空洞虛浮、言之無物的雞肋;要么無限放大娛樂功能,惡搞、無厘頭等紛紛上陣,或者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凡此種種皆使文學(xué)創(chuàng)作步入歧途,陷入獵奇驚悚、庸俗膚淺的泥淖,對文學(xué)的發(fā)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官員寫作要突破現(xiàn)有格局,保證不斷出新出彩,佳作蟬起,這就要求領(lǐng)導(dǎo)干部不僅要真正沉入生活,貼近時代、貼近群眾,大力提升藝術(shù)境界,還要有效借鑒一切文明和文化中的養(yǎng)分,擁有進(jìn)步的人文知識和人文觀念;就要求在創(chuàng)作中精心篩選過濾素材,精心營造意象與意境,精心安排結(jié)構(gòu)、設(shè)計情節(jié);就要求在作品中實現(xiàn)藝術(shù)價值和思想深度水乳交融。只有這樣,官員寫作才能得到進(jìn)一步的開拓與創(chuàng)新,才能不斷有所突破、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