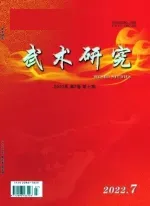梅山武術文化內涵探驪
羅沅洲
(上海體育學院武術學院,上海 200438)
1 梅山武術文化的生活內涵
1.1 梅山武術的器械生活化
梅山武功源于梅山人們長期的生活生產實踐,在梅山蠻抵抗歷代統治者殘酷的斗爭中糅合了外來技擊特征,發展為自成體系的地方拳種,梅山蠻“出操戈戟、居枕鎧弩”,長期保持著尚武好勝的習性,在梅山地區這塊特定區域內,習武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1]。據宋吳致堯《開遠橋記》載:梅山,春秋戰國時為“梅山蠻之地”。地方千里,廣谷深淵,高巖峻壁,繩橋棧道,民居十洞之中;食則引藤,衣制斑斕,言語迷離,出操戈戟,居枕鎧弩,刀耕火種,摘山射獵”。梅山先祖生活在如此惡劣的自然條件下,長期過著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在求生和與猛獸搏斗過程中,逐漸的具備了強健的體魄和翻山越嶺的奔跑能力,并不斷改造和創新與自己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工具,比如可以隨手拈來的板凳、煙斗、鐵尺、耙、魚叉等皆可作為防身自衛亦或是攻擊的器械,并且慢慢地形成了系統的的格技動作和方法,即梅山武術,其中比較常用的武器有七星鐵尺、梅山尺、四門鐵尺、梅宿尺、虎尺、四十八尺、三十六連環尺、四合尺、舞花尺、六合尺、二十四合尺、佛光鐵尺;梅山耙、木耙、四門耙、一字耙、四門對八門耙、滾耙、飛耙、南洋耙、花耙、九尺釘耙、斗虎耙、七星耙;四門關刀、關刀、青龍偃月刀、仆刀、南岳大刀、王斧大刀、梅山大刀;梅山凳、四門凳、六合凳、一字凳、田字凳、九打九沖梅花凳、猛虎下山凳;腰帶、煙袋、九節鞭、三節棍、梅山鞭;長煙筒、箭、桌拳、穿山角等,無不體現了濃濃的生活氣息。比如各種耙,一開始是應用于人們晾曬稻谷,在曬谷的過程中對稻谷進行梳理或者曬好谷子之后用于把谷子聚攏的工具,而梅山先輩則在晾曬稻谷的過程中受到啟發,再結合梅山武術獨有的特點自創了適合應用于“廣谷深淵,高巖峻壁,繩橋棧道”的具有獨特的域性的武術套路,成了可以隨手拈來的武器,與生產很好的結合了起來。
1.2 梅山武術的套路生活化
生產勞動是原始人類第一位的社會活動,狩獵是人類最古老的生產活動。遠古時期,梅山地區人少而禽獸眾,梅山人為了生存,防止和制服各種禽獸的襲擊,產生了拳打腳踢、躍撲滾翻、跳躍閃擊等自然動勢,并在實踐中運用四肢、模仿猿鳥原形,效其運動來保衛自己和獵取食物,出現了產生武術的基本因素和條件[2]。當原始梅山人進化到晚期階段,直接從生產、狩獵中篩選出來的某些身體活動形式,經過特定目的加工、嫁接和復合,逐漸從勞動、狩獵活動中分化出來,其動作形式的性質開始轉變為抽象、復雜,形成了梅山武術的原始勞動形態,如白虎拳、黑虎拳、三意拳、八虎拳、黑虎下山拳、仙人指路拳、梅花拳、梅城拳、梅花掌等,其中以動物的攻防形態命名的招式如:黑虎掏心、玉蟒纏身、金龍罩體、犀牛望月、雙豬揀槽、猛虎撲豬、喜鵲歸巢、雄鷹追雞、青龍下海等,這些招式與套路凝聚了梅山先人的智慧,使之具有生活氣息。
1.3 梅山武術的功能生活化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生活方式的改變,梅山武術的廝殺搏斗與上山趕獵的功能逐漸弱化,而其獨特鮮明的健身娛樂性則日益體現于梅山地區社會各階層的文化生活中,其一,人們從習武中獲得身心的愉快,并在社會大眾中得到發展。其二,人們從對梅山武術的觀賞中獲得了藝術的賞受,尤其是現代,武術與戲曲、舞蹈、雜技、文學、影視等文藝形式的結合表演均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著現代生活方式的演變人們對梅山武術的健身、防身實用價值的認識大大提高,從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梅山武術的發展。
從文化學角度來講,民族傳統體育具有地域性、生產性、封閉性,也正是這種特性,梅山武功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已經深刻的融入到梅山峒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行使著生產、斗爭、娛樂和教育的社會功能。任何民族的進步,都離不開其傳統文化的維系;任何時代的發展,都必須以其民族精神來支撐,梅山武功的特征是由其特殊的地域特所征決定[3]。封閉的地域衍生了封閉的文化,由于梅山地區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加上忙時農耕,閑時追山趕獵人們生活自給自足,所以封閉文化形態下的梅山武功其主要目的便是生產實用,當遭遇外來侵犯時便表現為敏感和沖動的對抗[4]。從梅山文化、梅山地域的視角看,這種敏感和沖動的對抗是梅山峒蠻追求自由的不屈精神體現。因此,梅山武功的特殊性體現在它不僅是一種地方拳種,也是一種影響梅山地區社會走向和梅山峒蠻政治態度的傳統文化。
2 梅山武術文化中的宗教內涵
2.1 梅山武術宗教內涵的表現樣式
原始人類由于對許多自然現象的不理解和恐懼,因而產生了萬物都是受神靈主宰的觀念,由此產生宗教活動和圖騰崇拜,宗教是現實生活中人們意識的幻想和歪曲。由于迷信,原始人類常用種種形式以圖影響自然力量,在祭祀活動中,逐漸用舞蹈、競技、角力來進行祈禱,娛樂神祗,祈求庇佑[5]。古梅山人信奉梅山教,梅山人許多的風俗習慣都來自于對梅山教的信仰,甚至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據史料載:古梅山洞主符天賜、李天華、趙天祥武藝高強,狩獵本領高,死后被奉為梅山祖師。以后的獵人進山,必先拜祖師,求其保佑平安。據傳就連梅山教教主張五郎,也是武功高強、趕山狩獵的好手。梅山教沒有成文的宗旨教義,主要利用符咒授徒苦練耙、棍、刀、劍等武術,尤以槍法、劍法以及配置弩藥為主,籍以制服猛獸和敵人。在今天的梅山武術套路中,依然發現一些武術動作仍然保持著梅山教的淵源。如在梅山叉和流星錘的套路中,結束動作就叫“朝天三柱香”,喻以驅邪逐魔,慰藉人類的靈魂,構成了宗教形態的梅山武術活動。
2.2 梅山武術宗教內涵表現的原因
梅山文化最初表現為一種村落巫教文化,是梅山峒蠻解釋、征服大自然及社會生活的生動記錄[6]。梅山巫教是梅山文化傳承、蘊含及表現的主體,并有系統的神、符、壇、演、會和教本,施教的男神叫張五郎,又名開山五郎,女神叫白氏仙娘。梅山教徒按職業分成三類,所謂“上路梅山,張弓挽弩;中路梅山,追山趕獵;下路梅山,撈魚摸蝦。”[7]教徒習慣在腰帶上懸一木雕或骨雕的梅山祖師形象,求得福佑,遇難呈祥。他們崇拜自然、圖騰、祖靈,重祭祀,小至上山打獵、下水撈魚,大至造屋架橋、婚喪喜慶都要先舉行祭祀儀式,而在祭祀和傳教訴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民俗文化,特別是融演唱、舞蹈、武術于一體的“搬開山”,至今仍在湘中一帶流傳。梅山峒蠻在祭祀梅山神時,祭祀人頭戴羊角帽身著百衲衣,戴假面具,扛開山斧,殺雄雞,口唱有一定程式的韻文頌詞。這種祭祀演唱就被稱為“搬開山”。唐以后,發展成為祭祀人身著僧袍道服,執長柄柴刀,鑼鼓聲中,上下左右起舞耍刀,舞姿粗獷,節奏自由,同時揉入“烏云蓋頂”、“枯樹盤根”等大量武術動作,章淳在《開梅山歌》中就以“川堂之鼓當壁穿,兩頭擊鼓歌聲傳”的詩句,記錄了這種“群眾文化”的盛況,梅山武功正是在這種祭祀活動中得以發展流傳.
3 梅山武術文化中的技擊內涵
3.1 梅山武術的技擊特點
梅山武術的技擊方式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梅山地區地勢險惡,峰巒起伏,山高林密,因此動作少騰挪跳躍,具有“拳打臥牛之地”的特點,“拳打臥牛之地”,形容的是打拳時用地之小,梅山“地方千里,廣谷深淵,高巖峻壁”,梅山人要想抵抗自然災害和豺狼虎豹的無情侵襲,以及歷代封建統治者的無情鎮壓,就必須創造適合當地地形的武術動作[8]。動作舒展大方,高舉高打的北方拳種顯然不適合,聰慧的梅山人便創造了步法以五點梅花為主、手法勇猛剛烈的梅山武術。梅山武術套路短小精悍,以攻為主。出招時“沖拳為三角,挑拳似牛角,相打緊逼前,掌法似刀鐮,好打前后打。由于地處高山,活動環境狹小,梅山武功也十分注重樁功的練習,民間有“四十天打,三十夜樁”之說,即學四十天的武術,需練三十天的樁功,有拳好樁功穩,學拳先練樁的傳統,有練好“三樁”,功夫一半之傳說,由此可見樁功的重要。其主要練功方法有練坐樁、箭樁、丁樁、組合樁功、負重、練抓勁等。這充分反映出梅山武術具有獨特地域性的技擊特點。
梅山武術以地名或步法的形狀命名套路也是一大特色。比如梅山拳、工字樁、梅城拳、梅山掌等,它具有拳打臥牛之地(上護胸、下護檔)、出手三不歸、手不搭腳不踢、沖拳迅猛之技法,此外,梅山武功套路短小精悍,動作樸實,一招一式,直來直去,手法多變,多拳法,善用掌,變化無窮。梅山武功腿法雖少,但步法穩健,下盤扎實。《梅山拳譜》記載:“沖拳為三角,挑拳似牛角;相對緊逼前,掌法似刀鐮;好打前后打,左右開弓打兩邊,對方來的兇,我即把肘沖;急來滾子,閉上斜行;九斬九金剛,十斬十金剛,上用打,下用穿,上打雪花蓋頂,烏云罩地,雷火燒天,下打古樹拔根,席地而掃,連根而拔……”意思就是依金木水火土五行而變化,并結合剛、柔、直、橫、斜、虛、實七種勁力是其獨具的特色。
梅山武術拳法種類繁多。按類型分主要有沖拳、貫拳、扣拳、橫拳、砸拳、挑拳、蓋拳、撩拳等,手法主要有擒拿手、封閉手、砍手、劈手、標掌、壓手、推手、轉手、接手、抓手、牽手、擺手等,肘法技擊要點主要是靠、橫、擋、撞、架、頂,腿法技擊要點主要有彈腿、踹腿、蹬腿、鏟腿、掃腿、掛腿等。

表1 梅山武功徒手套路統計表

表2 梅山武功短器械統計表
梅山武術的器械套路更是多樣化。如刀、槍、劍、棍、板凳、鐵尺等器械套路。清代橫陽劉應樸、大石夏屋場發轉子、鐵山逆壩凼肖老四被民間譽為:“樸少爺的拳、肖老四的尺(鐵尺)、發轉子的棍”。在1983年武術挖掘整理工作中,新化鵝塘陳渭南、陳漢華、廖湘元、劉正和,橫陽陳福球、陳益球、楊鐘澤、楊海珊,爐觀的何艷華、何青海、何庭侯,洋溪的歐啟楚、鄒聯忠,白溪的張策民,游家游本恒、易智勇、李保光,城關的劉魁作、張六喜、晏西征等拳師紛紛獻藝。經過調查整理,梅山武功徒手套路大約八十六種,器械套路大約114種。

表3 梅山武功長器械統計表
由此可以略窺梅山武術技擊內涵的博大與豐富,在一代代梅山前輩的共同努力下積淀得愈發厚實。
4 社會的現代化賦予梅山武術新的內涵
隨著梅山人們社會生活結構的改變,與世界全球化的趨勢,在人們眼中它更多的表現為一種傳統的民族文化,梅山武術文化是應該收藏進歷史的博物館還是重新找到它的位置,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經過多渠道的調查研究,最后總結出了梅山武術在現代化的新內涵,正是武術調試性與適應性的表現。
4.1 梅山武術的健身內涵
“梅山峒蠻閑來練武習藝,忙時追山趕獵”,是古時候梅山先人生活的生動寫照,其原因一方面是為了對抗統治者的征伐,另一方面是梅山民眾謀求食物的需要。雖然如今的梅山民眾已很少再追山趕獵,但是作為一種原始文化特征,梅山武術的健身價值依然存在。這是因為梅山武術在與其他文化交流過程中涵攝了我國傳統養生學、醫學、仿生學的諸多精華,大大豐富了其健身價值價值,這種價值隨著梅山武術的流傳而保存下來,在今天的湖南省梅山地區,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在練梅山武術。同時,由于梅山地區廣大農村缺乏基礎的體育設施,人們也很少接觸現代西方體育健身運動,于是土生土長的梅山武術便成為了梅山民眾最佳的健身方式。據筆者的調查訪問,約有66%的學者和專家認為從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梅山武術開發成一種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健身運動方式,有多達約94%的學者和專家一致認可梅山武術在梅山地區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因此,梅山武術不僅僅是梅山地區古老的地方拳種代表之一,更是梅山地區優秀的民眾傳統體育項目,有積極的健身內涵。
4.2 梅山武術的教育內涵
近代以來,在梅山地區,隨著中華民族危機不斷加深,梅山武術的教育功能也開始被世人所關注,1938年新化縣城西正街正式成立中國國術研究所,研究所所長由縣教育科長兼任,同時有7名研究員,第二年改名為中國國術館,館長由縣長兼任,所有研究員改稱為教員,同年招收廣大青年農民50人入館學習國技。國術館自開館以來共舉辦5期培訓班,學員培訓達370人之多。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梅山地區,地方各類武校培訓班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據相關資料顯示,有縣辦武術館一家、私辦武校多達24家之多,在縣城外開場授徒的武師多達300余人。據新化縣教育局李志成介紹,如今在新化縣內各中小學,每個學生業余時間都必須學習新編梅山武術套路,要求新化縣各級中小學保證至少每周一個課時用于學生學習梅山武術,并每年定期舉辦一次中小學梅山武術比賽。作為地方典型傳統文化代表,梅山武術得以在梅山地區各中小學傳承;作為一種傳統的強身健體的運動方式,無疑也從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學生的校園生活。因此梅山武術的教育價值功能在現代社會中仍然存在。
4.3 梅山武術文化的經濟內涵
經濟功能在武術上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利用武術特有的表演觀賞、競技、組織宣傳及開展相關的經貿活動;二是武術健身修身的效果自身具有巨大的潛在經濟功能。習練武術能增進人身心健康、提高工作學習效率,促進社會和諧。隨著梅山文化旅游的升溫及國內外梅山文化研究熱潮,梅山武術因為其獨具特色及神秘的源流和作為一種武舞類節目開始走向現代舞臺向外來游客展示,這種形態的梅山武術文化在現代流變中滿足外來游客獵奇探秘心理,注重表演性,梅山武術從地域經濟學角度來說是梅山地區極具有經濟開發價值的人文資源,對于梅山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非常大的作用。
5 結語
梅山文化是梅山峒蠻在長期的社會生活生產實踐中的積累沉淀,包含了梅山峒蠻原始思維特征和文化信息,梅山地區山高林密,長期與外界隔絕,造就了封閉的梅山文化,章淳開梅后又吸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形成了梅山地區文化融合、習俗交叉的社會現狀,封閉的梅山文化決定了梅山武術特殊屬性,它與宗教祭祀、娛樂教育的結合形成具有民族體育屬性的武術文化,與生產實踐和戰爭格斗的直接聯系決定了梅山武術的實用性。梅山武術在流傳中發展、變化,從重生產實用到重技戰格斗,再與宗教祭祀聯姻,并汲取了其他地方拳種的特點,最終自成體系。梅山武術文化的內涵主要體現在生活內涵、宗教內涵和技擊內涵等方面,在新的時代下梅山武術的又呈現出新的內涵主要體現在健身娛樂、文化教育和經濟功能上。梅山武術的研究在微觀的角度與梅山地區的歷史因素和地域條件相結合,體現出其個性。梳理梅山武術的文化內涵,從文化脈絡把握梅山武術的演變過程是其現代社會價值重構的重要參照系統,梅山武術的健身、經濟、教育等內涵的發掘必須結合當地社會現狀,兼顧其本身特點。
[1]陳立群.梅山文化考略[A].梅山文萃(第一卷)[C].新化縣文化局,2009:20.
[2]馬鐵鷹.神奇的梅山文化[N].湖南日報,2003-10-08.
[3]周行易.當前梅山文化研究應注意的幾個問題[A].中國第四屆梅山文化學術研討會交流論文[C].2006:43.
[4]蔣寶德.中國地域文化[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7:35.
[5]陳益球.梅山武功[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40.
[6]陳文卿,王洪元.梅山武功的文化淵源[J].婁底師專學報,2003(3):45.
[7]楊俊軍.梅山武術及其文化特征[J].體育成人教育學刊,2004(5):26.
[8]周惠新.梅山武術的生存形態與特征[J].搏擊·武術科學,2009(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