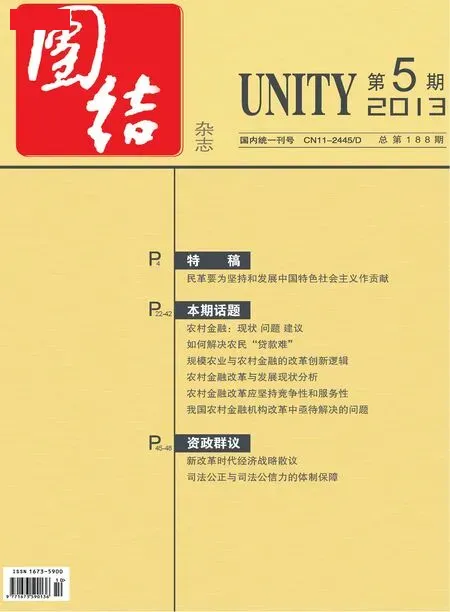咨詢性投票:政協履行職能的有效方式
◎鐘茂初
(鐘茂初,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民革中央委員。本文原載 《理論研究》2013年第3期/責編 盧淼)
政治協商、民主監督,是現行政治制度賦予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的基本政治權利。要使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有效行使這一權利,需要在協商民主、民主監督過程中設計出有效的行權方式,以使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有真實意愿參與、有序參與、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地參與。毋庸諱言,以往一些協商事項、民主監督事項往往是形式高于內容,很難體現出有效參與的效果,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在參與過程中,由于無法體會到是否有實際作用,往往在缺乏真實參與意愿的狀況下被動地參與,進一步影響了政治協商與民主監督的實際效果。所以,探索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參與協商民主的有效行權方式,是實現這一政治制度的重要課題。
筆者探索性地提出:“咨詢性投票”是一種有效的協商與監督方式,可以作為一種制度設計借鑒應用于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與實踐之中。
一、“咨詢性投票”的一般形式及其作用效果
“咨詢性投票”作為一種協商與監督方式,較為普遍地應用于高校或科研機構的職稱評定過程中,且形成了較為成熟、完善的制度程序。在職稱評定這一決策過程中,制度規定的決策機構是 “職稱評定委員會”,但是,在 “職稱評定委員會”的決策應充分考慮 “教授會”(由全體正高級職稱成員組成)的 “咨詢性投票”結果。在這一決策過程中,“教授會”的 “咨詢性投票”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l)教授會成員的投票代表了一種專業性評判,體現了整個機構內最高水準的專業評定;(2)教授會成員的投票反映了整個機構內的整體性意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民意基礎; (3)教授會成員的投票,具有排序作用和篩選作用,贊成票越多,意味著教授會成員越傾向于申請人具有晉升資格;反對票越多,意味著教授會成員越傾向于淘汰該申請人。這一投票結果,對決策者具有指導性作用;(4)教授會成員的投票結果,對于 “職稱評定委員會”的最終決策有一定的制衡與監督作用,如果 “職稱評定委員會”的最終決策完全偏離了 “教授會”的 “咨詢性投票”,那么其決策的專業性、公正性、公平性就會受到質疑,這對于 “職稱評定委員會”的決策權力有一定的制衡;(5)由于教授會成員的投票只是 “咨詢性投票”,不具有法定的投票決定作用,所以不會影響法定決策機構的最終決策權力。
二、“咨詢性投票” 借鑒應用于政治協商的可能途徑與預期效果
鑒于 “咨詢性投票”是一種有效的協商與監督方式,且具有較為成熟的操作程序,完全可以借鑒應用于政協、民主黨派參與協商民主和民主監督的制度建設與制度實踐之中。如,政府部門擬出臺某一重要政策或某一重要法規,在提交立法機構決策之前,可以通過政協平臺邀集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對方案進行 “咨詢性投票”。在整個政策法規制定的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過程中,這一“咨詢性投票”可以起到以下作用:(l)具有較高專業化程度的政協委員的投票,可起到一種專業性評判的作用;(2)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的投票,具有較為廣泛代表性的民意基礎;(3)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的投票,具有對政策、法規進行決策或調整的指導性,贊成票越多意味著全體成員越傾向于通過政策法規的某一條款,反對票越多意味著全體成員越傾向于修正或取消該條款,對決策者具有指導性作用;(4)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的投票結果,對于政府部門和立法機構的最終決策有一定的制衡與監督作用,如果最終決策完全偏離了 “咨詢性投票”,那么其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就會受到影響,這有助于把最終決策權力 “關在籠子里”;(5)由于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的投票只是“咨詢性投票”,不具有法定作用,所以不會影響法定決策機構的最終決策權力。
同樣的道理,對于政府部門擬進行重要的人事任免事項,在提交法定決策程序之前,可以通過政協平臺邀集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對人事方案進行 “咨詢性投票”。這一 “咨詢性投票”也可起到以下作用:(1)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通常不涉及關聯利益,其投票,可以從更為中立的立場,對人選是否適任作出更為客觀的評判;(2)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的投票,由于其與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聯系性,能夠基于民眾對于人選的一般社會評價、社會口碑、行使職權的操守與能力,作出代表整體民意的一般判斷;(3)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的投票,對人選的任用或不任用有一定的指導性,贊成票越多意味著全體成員越傾向于某一人選適任,反對票越多意味著全體成員越傾向于該人選不適任,決策者應以此評判作為決定參考; (4)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的投票結果,對于人事方案的最終決策有一定的制衡與監督作用,如果最終決策完全偏離了 “咨詢性投票”,那么其決策的民主化就會受到負面評價,這一約束有利于人事最終決策權力受到監督;(5)由于 “咨詢性投票”不具有法定作用,所以組織部門擁有人事最終決策權力的基本制度不會削弱。
三、“咨詢性投票”作為協商民主方式,與現有政治制度具有高度契合性
從政治制度層面來認識,“咨詢性投票”作為協商民主方式,完全符合現有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且具有推進這些政治制度要求得以落實、得以完善的操作性。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方面。
(l)由于“咨詢性投票”,不具有法定作用,所以,執政黨的決策權力不會被削弱,也不會影響法定決策機構的最終決策權力。同時,卻預期可起到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的有效作用。因此,通過政協途徑進行的 “咨詢性投票”,可以使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基本政治制度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政治制度得以有機結合。
(2)“咨詢性投票與最終決策,是在同一目標下的投票,通常情況下,最終決策與 “咨詢性投票”傾向是一致的,因此,這一制度安排可以有效避免其他政治制度下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對立性投票的機制。
(3) “咨詢性投票”是在具有較廣泛民意基礎上獲得最終決策所需要的專業評判、社會評判以及其他意見建議信息,為最終決策機構提供了科學決策的客觀依據,體現了 “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原則。
四、“咨詢性投票”作為協商民主有效方式應建立的具體規章制度
“咨詢性投票”制度,要想實現協商民主、民主監督的有效效果,還需要具體規章制度的支持。要想使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有真實意愿參與、有序參與、且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必須建立完備的具體規章制度與程序。
(l)在思想認識方面,不應把協商民主與投票決定民主對立起來。要認識到,協商民主也可以通過 “咨詢性投票”方式來實現,且“咨詢性投票”方式是實現協商民主較為有效可行的方式 (因為,只有“投票”方式才能使所有成員同時參與,且對參與成員最具吸引力的參與方式。其他方式,往往容易出現 “有意愿者沒有機會參與,有參與機會者卻沒有參與意愿”的情形)。
(2)在什么情況下、針對哪一類的問題,必須舉行 “咨詢性投票”,應有明確的制度規定。制度一旦確立,就必須制度性地堅持,不得隨意決定舉辦或不舉辦,不得隨意修改、隨意作出歧義性解釋,應逐步樹立這一制度的公信力。同時,制度應明確規定,不得對投票人的歷次投票行為與其后的政治安排 (如政協委員的遴選、實職安排等)以及其他利益掛鉤,否則會導致 “咨詢性投票”制度的異化。
(3)實行“咨詢性投票”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較為客觀且具有民意基礎的決策依據。所以,應盡可能向參與者提供完備的信息,不應在預設傾向的前提下選擇性提供信息。制度還應明確規定,不得對參與投票者的投票傾向作出任何形式的勸誘或誘導,否則就難以得到真實的專業判斷、真實的民意反映、中立客觀的意見反映、合理的建議主張。
(4)在參與范圍內,應及時公開投票結果,以使參與者能夠真切感受到參與效果。同時,在作出最終決策后應及時通報最終決策結果,以使參與者對比最終決策與 “咨詢性投票”的關聯關系,使之能夠感受到 “咨詢性投票”的真實作用,這樣才能夠使參與者逐步增強對該制度的信任度、參與該工作的積極性以及真實意見表達的意愿性。
(5)大多數情況下,最終決策應與 “咨詢性投票”所反映的傾向大體一致,較為偏離的情況,應作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如果,經常性地出現最終決策偏離 “咨詢性投票”傾向,則會使該制度失信、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