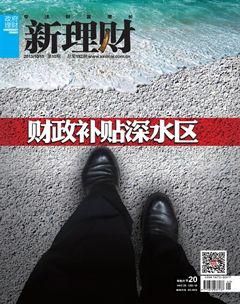財政補貼隱秘
黃前柏
財政補貼,作為一項扶持相關產業的政策,在發揮其重要作用的同時,諸多弊端也逐漸凸顯,這也反映出財政補貼過程中的種種漏洞。
本文將重點分析在財政補貼過程中存在的一些現狀和隱秘。
上市公司調節器?
對于許多上市公司來說,各種形式的財政補貼,是其調節利潤的重要工具。
7月1日,上市公司三安光電公告表示,公司2013年6月28日收到安溪縣財政局《安溪縣財政局關于撥付三安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藍寶石襯底項目財政補貼的通知》。該項財政補貼資金5000萬元。目前,該款項已收到。
公眾廣泛質疑,三安光電究竟是一家什么樣的企業,短短幾年內屢獲補貼,并且每次數額巨大。據統計,三安從2009年到2012年4年間,累計進補16億,占同期凈利潤的68%以上。歷年中,三安光電獲得補貼可謂名目繁多,2012年竟達24個。其中,設備補貼是大頭。
據統計,兩市從今年8月份以來,共有57家上市公司收到政府補助、補貼的公告公布。這57份公告中提及的補助、補貼款,累計總金額約為9.6億元,而單筆補助、補貼款的數額,則從數千元到上億元不等。
財政補貼的種類可謂五花八門:有稅收優惠,也有減免銀行利息、節能減排補貼,還有調整產品價格和設備購買、產品推廣補貼等等。財政補貼對上市公司全年的業績將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不少瀕臨退市的公司可能因此起死回生,也有一部分公司借助財政資助扭虧為盈,避免暫停上市。
從財務層面來分析,總體來看,多數上市公司都表示,會將補貼款計入當期營業外收入并計入公司2013年度損益,從而預計將對公司2013年度損益產生一定的正面影響。此外也有少數公司表示,補貼屬于與收益相關的政府補貼,將其計入“遞延收益”,公司將根據項目實際進展情況,在項目期內分期確認為當期收益。
從地方經濟層面來分析,財政補貼并沒有明顯的周期性特征,政府什么時候收到稅收,就會把財政補貼發放到相關企業。上市公司總資產在地方經濟有著重要地位,而且上市公司的存在有助于提升地方知名度,從而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吸引更多投資,所以地方政府往往都會幫助地方企業保住上市公司的“殼資源”。因此,年底“突擊”獲得補貼是ST公司經常上演的戲碼。
財政支出“兩大漏斗”
今年6月份,審計署發布“5044個能源節約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資源綜合利用項目審計結果”公告,格蘭仕、格力、美的、長虹、長嶺冰箱等8家家電企業,騙取國家節能補貼9061.84萬元;上海大眾和上海通用,也用非環保汽車,騙得節能補貼共計1725.6萬元。
與此同時,實施近三年的“金太陽工程”屢屢曝出問題重重:項目停工、騙取補貼等等。
以上的案例,都反映出一個問題。過多過大過泛的農業補貼與新產業補貼,已經成為財政支出的重荷。日漸增多的“騙補”與日益嚴重的“補貼尋租”,正在使農業補貼與新產業補貼擴大為財政支出的“兩大漏斗”。
據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國有經濟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研究,近10年農業補貼額累計約5.8萬億元,新產業補貼額累計約28.7萬億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農業補貼與新產業補貼的過多過濫。
文宗瑜認為,累計十年的巨大農業補貼沒有換來中國農產品質量與農業效率大幅度提高。累計十年對新產業天文般數字的補貼仍沒有使中國步入科技創新時代。相反,這些領域中眾多公司圍著政府官員及政府要錢、要地、要戶口指標、要優惠政策幾乎成為常態,導致一些所謂科技創新的“明星公司”不得不靠財政補貼改善其財務指標。農業與新產業的巨大補貼額與兩大產業的低質量低效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財政補貼“養”不出現代農業,財政補貼“養”不出有國際競爭力的新產業,如果不及時調整已有的農業與新產業補貼政策,不僅會嚴重拖累財政,而且會使財政收入增長放慢條件下的財政風險進一步放大。
政策究竟該怎么改進?文宗瑜認為,把農業與新產業補貼政策調整與通過深層次改革促進農業與新產業發展銜接起來。
首先,對農業與新產業補貼政策進行全面的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定性評價,要著眼于:補貼效應是不是已經異化;如果不調整,繼續沿襲該政策會不會拖累財政;如果要調整,調整的力度多大等。定量評價,要著眼于:補貼多少合適?財政可承受的補貼額度?年調整幅度及中長期調整的力度等。評價的過程,要盡量弱化行政色彩,降低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度,多依賴外部的專業人才與專業機構。
其次,要盡快啟動農業補貼與新產業補貼調整的工作并不斷加大力度。補貼政策應放大財政體制改革的大思路與大框架中去思考,應先從補貼方式入手,逐漸調整標準及規模。
第三,積極推進相應的深層次改革而弱化農業與新產業對財政補貼的依賴性。應以“農村居民市民化”創造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條件,逐步調整落后的農業生產關系。應吸取政府過多介入與介入過深的教訓,還要求政府在知識產權保護等軟環境改善上有更大的作為。
補貼“掮客”
政補貼存在的漏斗,也催生出一批補貼“掮客”。他們利用手中所謂的資源、關系、項目,在政府、企業、官員之間架起了一條完整的利益鏈條。
記得早在2010年,“金太陽工程”實施之初,一些補貼“掮客”紛紛進京,托各種關系,其中不乏魚目混珠者。
一家曾經參與過的企業家介紹,“金太陽工程”是國家的項目,申報的時候需要先報到省里,再由省里上報國家,每一層在篩選項目的時候,都可能會被篩下去。“金太陽”的通過率一般在20%左右,報5個項目往往只有1個通過。
申報時需要提交的材料有上百頁,包括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等諸多方面,還要請有資質的單位,通常是設計院,來做可行性研究報告。
在這個過程,最重要的做到消息靈通,及早準備。
與此同時,在利益的驅動下,一些專門為企業申請補貼的第三方機構也紛紛成立。據浙江某機構的負責人介紹,補貼申請的難易程度,也與企業所屬的行業有關。如果做的是高新技術、電子信息、生物醫藥、軟件、新能源等等這些,就比較容易申請到,但如果是做貿易,幾乎不大可能拿到補貼。
一位地方財政局人士告訴記者,財政補貼之所以被一些人當作“唐僧肉”,需從程序上尋找原因。一個項目從立項到最終獲得財政補貼,需要經過一系列流程。從地方審核到確定上報,都在地方政府的掌握之中。對于地方來說,項目獲得財政補貼,本身就是一個政績;而對于那些具體負責部門,有些地方補貼分成已經潛規則化,企業拿多少,部門分幾成;事先有約定,事后忙兌現。而對于補貼發放部門來說,項目補貼資金是事先立項的,也存在“不花白不花,給誰不是花”的利益尋租。
拿財政補貼當“唐僧肉”其害無窮,為此,必須打破“封閉審核”,讓社會公眾參與、監督項目審核。一些項目的內情,體系內部或許不知,但公眾往往清楚;體系內部或許作假,但公眾不會。拿環保項目來說,到底有沒有建,最終效果如何,那些身處第一線與項目密切相關的民眾最有發言權。聽其意見,讓其參與,就能夠擠掉項目本身的水分。把項目打回讓地方自審,難免重新掉入“封閉式審核”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