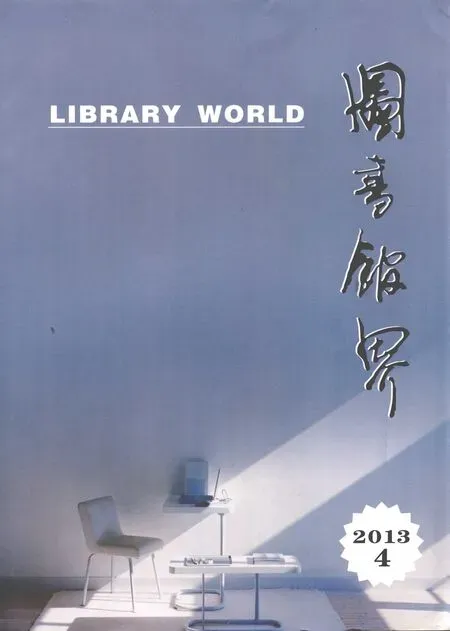愚齋書目的兩個問題及引發的思考
鄭曉霞
(華東師范大學,上海 200241)
愚齋藏書指的是清末盛宣懷的藏書。盛宣懷一生致力于洋務運動,不以藏書顯名,然其藏書數量過十萬卷,書籍類型涵蓋古今中外,且能摒棄傳統藏書家敝帚自珍的習氣,創建愚齋圖書館,將收藏向公眾開放,嘉惠士林,傳播文化,開一個時代藏書家收藏理念轉變之先河,從這些方面而言,完全可以躋身近代著名藏書家之列。令人惋惜的是,愚齋藏書在盛宣懷過世之后,逐漸流散,今天人們對于其當年狀況的認識主要基于藏書書目。目前存世的愚齋藏書書目共有四部:《愚齋圖書館藏書書目》18卷附《愚齋圖書館未分類書籍總目》,“民國”二十一年(1932)上海大成印務局鉛印本,以下簡稱“18卷本”;《愚齋圖書館藏書書目·詞曲類·戲曲類》,“民國”二十一年(1932)上海大成印務局鉛印本,是18卷本書目集部第五卷的補輯,以下歸入18卷本討論;《愚齋圖書館藏書書目》不分卷,附未分類書目、《愚齋圖書館叢部書目》,“民國”二十一年(1932)上海大成印務局鉛印本,以下簡稱“不分卷本”;《盛氏圖書館善本書目》,抄本,以下簡稱“善本書目”。在通過這些書目對愚齋藏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了兩個問題:一是愚齋圖書館的普通本藏書為什么會有兩部書目,即18卷本書目和不分卷本書目,二者之間的關系是什么?二是《盛氏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的善本數量及品質相對于盛宣懷的經濟實力和當時的善本流通量而言,似乎太過薄弱,是否真實反映了愚齋所藏善本的全貌?而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又直接關聯著愚齋藏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因此,本文擬將書目之間的比對分析、相關文獻的搜集爬梳與盛宣懷所具備的收藏條件的分析相結合,對這兩個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對目前愚齋藏書研究的進一步展開有所啟示。
1 “18卷本”與“不分卷本”書目之間的關系
善本書目之外,愚齋藏書還有兩部書目——18卷本書目和不分卷本書目,著錄愚齋所藏普通書籍。二者從題名到編纂體例幾乎完全相同,然將它們詳加比對,著錄重出者僅50種50部3375本(未分類者除外),在卷帙和內容方面,又幾乎完全相異,顯然著錄的是不同部分的愚齋藏書。18卷本書目卷前《敘》有言:“適敦聘繆筱山、羅榘臣諸公主持編輯,未及竣事,愚齋公作古。該館基地原屬義莊,邇以變產輸將,館址亦預其列。倉卒遷讓,錯亂不可言狀。爰由同人商請四五老友,擔任清厘,搜蠹拂塵,經五閱月之工作,始獲整理上架、粗具規模。計纂成經、史、子、集目錄十冊。至種類、卷數、悉系于各部子目之下,不復贅列云。”可知繆荃孫等人在盛宣懷去世之后,仍然堅持編纂并完成了盛氏所建愚齋圖書館的藏書目錄,即18卷本書目。既然如此,為什么還會有另外一部相類書目的出現?這部書目著錄的圖書又從哪里來?由于相關文獻的缺失,要通過直接論據得出確切結論顯然不太可能。然而,如果我們轉換視角,順著愚齋藏書本身的方向追溯,卻能使這些問題得到相對合理明確的解釋。
眾所周知,愚齋藏書在盛宣懷去世之后,除了善本秘籍被盛氏后人分割變賣外,普通書籍中的主要部分分別捐贈給了圣約翰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和山西銘賢學校。關于圣約翰大學得到的這部分藏書,1933年12月《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上有一則題為“約翰大學將建盛氏圖書館”的報道,文曰:
久為全國知識界景仰的盛氏(盛宣懷)藏書樓,搜儲國學新舊善本圖書達數十萬冊之巨,平素封秘珍藏,外人莫窺其奧。聞今已由盛氏后裔全部捐贈梵王渡圣約翰大學,士林贊美,以較浙江天一藏書之終不免于散失為善多矣。特盛氏不捐于其先人所手創之交通大學,而轉贈與外人統制之約翰大學,似猶令人尋味。個中人言,此事系約翰大學舊同學,國府前財長宋子文先生介紹之力。該校已準備另建三層大廈之新圖書館以藏之,且命名為“盛宮保圖書館”,日下第一箱書已到校云。
這里所說的“盛氏(盛宣懷)藏書樓”,應指盛宣懷一力創辦的愚齋圖書館。據此報道,可知愚齋圖書館的普通藏書在1933年應該已經全數捐贈了圣約翰大學。圣約翰大學的這批藏書新中國成立后又歸入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華東師范大學的周子美和吳平兩位學者通過對該校所藏愚齋藏書的調查,亦肯定了這批藏書就是18卷本《愚齋圖書館藏書書目》(不包括未分類書目)著錄的圖書,即愚齋圖書館的藏書。
既然愚齋圖書館的藏書基本都捐給了圣約翰大學,那么,上海交通大學和山西銘賢學校得到的愚齋藏書又來自哪里?關于上海交通大學得到的藏書,查閱《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圖書目錄第一輯·善本目錄》,可以發現,交通大學得到的這部分書籍與不分卷本《愚齋圖書館藏書書目》的著錄基本一致(不包括未分類部分)。聯系吳平、周子美二先生的研究都指出愚齋藏書“有一部分捐給了交通大學圖書館,這批藏書共557種,16702冊,在《愚齋圖書館藏書目錄》(18 卷本)中沒有著錄”的事實,應該可以認為,除了愚齋圖書館的藏書外,愚齋藏書還有家藏的部分,而交通大學得到的這部分就應該來自家藏。也許是出于共同的編纂者之手,也許出于捐贈公藏的共同原因,在編目時采用了與18卷本一致的題名和體例。
至于山西銘賢學校得到的藏書,由于戰亂與時代變遷,輾轉流徙,今已不知身歸何處,加之又未發現相關書目,要明確其面貌,目前確實不太可能。筆者還是偶然在近年的圖書拍賣會資料中發現了這批藏書的兩條線索:一是中國書店海王村拍賣公司2006年秋季書刊資料拍賣會圖錄中的一部圖書,著錄如下:
《籌濟篇》三十二卷首一卷
作者:(清)楊景仁輯
年代:清光緒四年(1878)詒硯齋刊進呈本
函冊:1函6冊
紙張:白紙
裝幀:線裝
尺寸:半框:20.4×13.2
鈐印:銘賢學校亭蘭圖書館之章、愚齋圖書館藏
二是上海博古齋拍賣有限公司2008年夏季藝術品拍賣會圖錄中的一部書,著錄如下:
淮鹺備要(殘)
歷史年代:清道光間寫刻本
函冊:4
紙本線裝
是書存卷1 -3、9、10
鈐印:愚齋圖書館藏、銘賢學校亭蘭圖書館之印
這兩套書顯然屬于山西銘賢學校得到的那批盛氏藏書。對照愚齋藏書目錄,前者與18卷本所附《愚齋圖書館未分類書籍總目》史部第340號著錄吻合,后者與第373號著錄吻合。由于愚齋的未分類書目編纂過于簡單,當然不能就此完全確定銘賢學校得到的就是18卷本所附《愚齋圖書館未分類書籍總目》中的藏書,但是比照圣約翰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所得部分,這個結論應該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如果這個結論成立,那么山西銘賢學校得到的愚齋藏書應該有1714種,1948部,15248本。
通過追溯愚齋藏書的方向,筆者認為,18卷本書目為盛氏所建愚齋圖書館的普通本藏書目錄,不分卷本書目為部分盛氏家藏普通本書籍目錄,也就是說,愚齋藏書并不像之前一些學者認為的就等于愚齋圖書館藏書,應由圖書館藏和家藏兩部分組成。
2 善本書目是否反映了愚齋善本的全貌
《盛氏圖書館善本書目》是迄今所見唯一的愚齋善本書目。該書目共著錄圖書245種251部,其中宋元本17部(含三朝板史籍1部,宋刻明補本2部),明刻本80部,稿抄本109部。這樣的收藏數量和品質,在盛宣懷這樣的收藏家而言,似乎不合常理。善本收藏一般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收藏的意愿、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社會相對豐富的善本流通量。盛宣懷正好具備了這三個條件。首先,追尋善本,擁有更多的善本,歷來是藏書家們的理想,盛宣懷也不例外。雖然他將普通本的收藏與利用擺到了一個重要的位置,但也重視珍本、古本。比如他曾咨詢繆荃孫:“有人送來《晉書》,是否宋版,索價三百元值否?”只要是聽聞有名家、舊族的收藏流出,總是想方設法收購過來。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寫給親家呂海寰的信中說:“宅有隙地,擬造圖書館,近頗收買舊書,如部中有罕見典籍價不甚貴者,乞代留意。孫濟寧收藏甚富,能否設法收購,兩有裨益。”
其次,在經濟實力方面,盛宣懷辦洋務40年,其巨額家產難以計算,足以支持他收藏到更多珍稀圖籍。所撰《愚齋東游日記》對其在日本的購書活動有這樣的描寫:“中國書籍不少,而精本標價極昂。內有鈔本《欽定西清硯譜》一部,計二十五卷,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凡陶之屬六卷、石之屬十五卷,共硯二百,為圖四百六十有四,附錄三卷。則今松花紫金駝基紅絲傍制澄泥諸品,共硯四十有一,為圖百有八。每硯正背二圖,亦間及側面。凡御題及諸家銘識,一一鉤摹,精好絕倫。稱系內府藏本,問其價二千元。”雖然日本漢籍并不便宜,盛宣懷卻可以“隨閱隨購,總計新舊不下千余種”,可知其完全有能力購入那些價格不菲的珍藏秘本。
第三,盛宣懷生活的時代,社會上善本的流通量遠遠多于今天。尤其是正處時代變遷、社會動蕩之時,貴族沒落,世家輪替,名家大族的收藏時有流出,只要經濟條件允許,善本收藏并不是遙不可及的事。與盛宣懷同時期、收藏條件相當的另一藏書家李盛鐸,其木樨軒就收藏有宋元古本三百部,明刊本二千余部,抄本與稿本兩千余部,從中可見當時古籍珍本的流通量還是相當可觀。盛宣懷也充分注意并試圖抓住這種機遇。他在1912年致信趙鳳昌曰:“近日常赴公園(日本)各圖書館博覽群籍,華洋今世無所不有。聞羅叔蘊、董綬金輩各攜所藏而來,深有慨于吾華數十年明哲精英淪落于外人之手一去不返……共襟懷夐遠,若到此一覽,當無不喟然長嘆也。弟前因上海為各國散處,可以持久不變,特建圖書館一所,以便士林。聞南中舊家藏書迫于亂離,傾篋而出,若能趁此時廣為搜羅,未始不可為東南保全國粹。公諒有同心。茲先措上日金二萬元,交妥便帶上,到日即請查收,代為留意收買。俟奉復翰再當續籌,大約義四萬元為度,專買未見之書。”在他的這類購書活動中,最著名的就是購入了清末著名藏書家江標和方功惠的藏書(18卷本《愚齋圖書館藏書目錄·敘》)。江標(1860—1899),字建霞,一作蒹葭,號師鄖,一號苫誃、萱圃、師許,江蘇元和(今蘇州)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工詩文,好藏書。收藏重宋元刻本、舊校舊抄,所藏皆精品。藏書在其身后流散,今已無法了解全貌,然觀復旦大學所藏抄本《江氏靈鶼閣藏書殘目》,著錄圖書僅32種,而宋元本就有13種,可以想見其收藏品質之高。
方功惠(1829—1897),字慶齡,號柳橋,湖南巴陵(今岳陽)人。以父蔭任廣東監道知事,官至潮州知府。方功惠自幼嗜書,其碧琳瑯館藏書十萬卷,富甲粵東,收藏之富,當時幾乎可與陸氏皕宋樓和丁氏八千卷樓相匹。《碧琳瑯館珍藏書目》四卷,著錄各種類珍本約680種,其中宋版有《周易本義》等34種,元版有《樂典》等400種,精抄本有《佳趣堂書目》等200多種。所著《碧琳瑯館藏書記》,收錄方氏孤本藏書題識75篇。由江、方二家的收藏,加上盛宣懷得天獨厚的收藏條件,反觀其善本書目,實在是有違常理。唯一的解釋就是盛氏所藏善本大多并未歸入愚齋圖書館。這一點,存世文獻和藏書中也能找到一些印證。《藝風堂友朋書札》中收錄了盛宣懷致繆荃孫的一封信,其中寫道:“昨奉手示,書目已完,深為感慰。秋后擬即開館,大約閱書室求備不求精。弟勿慮宋元本之少,甚慮種類之不齊耳。都中攜回善本亦屬無多,且恐缺短,已命五兒即日檢送書館,即乞補入書目為幸。”可知盛宣懷認為圖書館藏書的宗旨是“求備不求精”,開始并未給予圖書館宋元本這樣的珍稀善本,似乎是由于繆荃孫認為如果缺少珍稀善本,顯得圖書館圖書種類不全,才從家藏中撿了一部分納入圖書館館藏。從中透露了愚齋藏書的善本大部分屬于家藏的線索。今天存世的一些盛氏善本書籍亦能說明這點。如在2008年上海嘉泰秋拍中露面的《黃石齋先生遺書》,為明黃道周編,稿本,內封有盛氏藏書專用貼簽,上書“黃石齋遺集原稿”“善本”“原稿本”“不分卷四本”等,另附有盛宣懷親筆所書一紙,上云“一百二十兩文珍齋”,是為當年盛氏購此書之價。該書就不見著于《盛氏圖書館善本書目》。另外,日本天理大學和小汀文庫所藏的部分盛氏書籍,也未見諸存世書目。這些亦印證了盛氏大多數善本家藏不宣的事實。
結論:盛宣懷具備的得天獨厚的善本收藏條件,結合存世文獻、藏書的線索,都揭示了《盛氏圖書館善本書目》反映的僅僅是愚齋圖書館善本的狀況,并不是愚齋所藏善本的全貌。
3 思考
一直以來,藏書書目都是相關學者認識、研究盛宣懷藏書活動及藏書的重要依據。由于目錄不止一部,沒有明確的編纂體例,亦未表明著錄對象的具體歸屬,一些研究者往往依據題名中“愚齋(盛氏)圖書館”的字樣,將這些書目均視作盛氏所建愚齋圖書館館藏之目錄,并據此展開相關研究。雖然一些學者在研究過程中也注意到了部分藏書未見諸于書目的情況,但往往也只是一筆帶過,并未進行深入探討,這就使得愚齋家藏部分藏書成了一塊未經開發的處女地,造成了愚齋藏書研究的缺陷。因此,筆者認為,對于愚齋藏書而言,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書目之上,而應該從書目出發,充分注意到其特殊的藏書狀態,才能獲得更加全面、深刻的認識。
[1]本報編輯.約翰大學將建盛氏圖書館[J].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3(12).
[2]佚 名.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圖書目錄第一輯·善本目錄[K].上海,1933:1—34.
[3]吳 平.盛宣懷與愚齋藏書[J].圖書館雜志,2001,20(3):56—57.
[4]周子美.愚齋藏書簡介[J].圖書館雜志,1983,2(3):62.
[5]盛宣懷.盛宣懷十五、十六[G]//繆荃孫等.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盛宣懷.寄呂尚書函[G]//北京大學歷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盛宣懷未刊信稿.北京:中華書局,1960:210.
[7]盛宣懷.愚齋東游日記[O].盛氏思補樓,1916:35—36.
[8]盛宣懷.壬子親筆函稿[M]//夏東元.盛宣懷傳.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