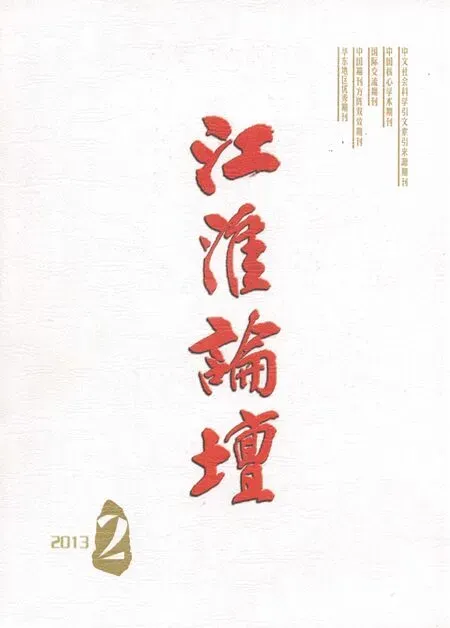“自我”與“他者”:文化政治與儒學復興*
廖永林 卞程秀
(內江師范學院政法與歷史學院,四川內江 641000)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最近十幾年,儒家文化在理論界的復興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從大型儒家文獻“儒藏”的整理到各種儒學出版物的發行,從國家形態上的中國孔子基金會的成立到各種民間儒學(儒教)社團的活躍,從各高校的儒學院成立及儒學專門人才的培養到民間的各種尊孔讀經運動,無不表明儒學在理論界的復興已經成為實事。對儒學復興的時代語境、儒學復興的具體路徑問題的探討也已成為理論界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當代儒家文化復興有著怎樣的時代語境?儒家文化復興在這種語境之下又有著怎樣的發展路徑?
一、“自我”與“他者”:世界歷史語境下的文化政治及儒學復興
對儒學的復興原因,諸多學者已經從不同的側面展開了研究。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崛起會導致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文化認同的加劇,如龔鵬程認為儒學的復興與經濟復興上的 “中國崛起”的文化身份認同有著密切的聯系。有的學者認為,上個世紀末期政治意識形態的退守使得各種理論得以發展,且儒學內部的某些價值亦為執政者提供了對現實的解釋力,如高瑞泉認為“文革結束以后,教條化的意識形態步步退守,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新秩序以后,重建意識形態成為了許多政治勢力關注的問題。儒學的某些價值再次被發現”。還有學者從現代性的角度對西方現代性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和弊端進行反思,以此提出儒學復興的必要性,如湯一介認為西方現代化中的主客對立的二元觀使得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處于一種對抗的狀態,造成了自我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相互之間的不和諧。
對于儒學復興的語境的探究基本在中國現代化的視閾之下,學者們致力于現代化中的經濟因素、政治因素以及現代化所導致的各種問題的研究。這種將儒學復興置于現代化背景下的打量方式,符合現實的語境。但是,現代化同時是民族的現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國家間的民族現代化。
那么,民族國家及民族國家間的相互關系與儒學復興有著怎樣的聯系呢?
在前現代,儒學的發展極少遭遇來自其他國家的影響,而近現代在民族國家紛紛建立的背景下,近現代儒學的發展始終面臨著一個外在“他者”。在早期,這一“他者”的形象始終是以政治、軍事及相關因素表現出來的,如政治聯盟、軍事斗爭等;近一個世紀以來,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和中國經濟、政治的發展,“他者”的形象由顯明轉而為隱晦。具體到文化領域,這一隱晦的“他者”就形成了文化政治。
所謂文化政治,是指力圖塑造一種同質文化這一群體公共意義系統,以謀求民族國家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文化與政治相結合的政治。這一術語曾在不同學者的不同著作中以不同的表達方式被提及,如趙汀陽曾在《壞世界研究——作為第一哲學的政治哲學》中提出了“文化政治化”。
文化政治作為訴諸文化因素以尋求政治利益的文化與政治相結合的政治,其產生有著文化和政治本身的原因和外在的現實原因。
第一,文化政治形成的基礎,在于各民族文化本身的想象和塑造的一個與“自我”相對立的“他者”形象。
文化作為基于生活方式而形成的一套心理、行為的群體公共意義系統,天然賦予了某一群體對自然和社會的認知模式和價值系統,它與異質文化之間相互區別,存在于某一文化系統中的存在者由于文化的影響天然具有一種“自我”和“他者”意識。
在西方,古希臘人將外族人稱為“barbarian”。這一稱謂在早期并無價值判斷,但是在公元前五世紀時,該詞逐步具有了“野蠻的”和“沒有教養的”含義。這種對于外族“他者”的稱呼證成了古希臘人在文化上的“自我”與“他者”的分離,并確認了“自我”的優越感。進入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時代后,“自我”與“他者”的界定又因宗教文化分化為正統的基督徒和異教徒。而與“自我”相對應的“他者”如伊斯蘭世界則被異化為“邪惡、丑陋和令人恐怖的他者”。近代以來,隨著西方率先進入現代化,他們構建了一個“他者”的東方世界。李慎之在評論《文化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時就將亨廷頓稱為“西方中心主義的遺老”。
文化上的天然“自我”與“他者”的區分也表現在中國文化中。雖然《說文解字》中并無“他”字,但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認為“他”為“它”的假借字。“其字或假佗為之。又俗作他。經典多作它。猶言彼也。許言此以說假借之例。”許慎《說文解字》對“它”的解釋為:“從蟲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從它。蛇,它或從蟲。”在華夏文化傳統中,與“自我”相對的“他者”類似于沒有教化的蟲類。這也就不難解釋,早期文獻中對少數民族皆以戎、狄、蠻、夷稱之。黃玉順在《中國傳統的“他者”意識》一文中認為“他”字在早期為遠指代詞,既可指人又可指物,更多的是指非人的物。因而,他總結說:“從存在論的角度來說,他者乃是異己的在者;如果從價值論的角度來看,則‘他’或‘它’那是邪惡不正的東西。 ”
第二,文化政治的形成基于政治及其利益的訴求。
如果說文化上的“自我”與“他者”的分割來自于文化天然和文化群體承襲中的無意識的結果的話,那么政治上的“他者”與“自我”則是有意識取舍的結果。
卡爾·施米特試圖超越道德的善惡、審美的美丑和經濟的利害,將“朋友”與“敵人”這一特殊劃分作為政治及其內容的簡明標準。但是,這一劃分始終無法擺脫現實的政治中的權力和由此而來的利益因素。
馬基雅維里將現代政治科學聚焦于權力,荀子提出從人之欲、勢不能容、物不能贍。雖然他們基于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目的,但是其后都隱藏著權力以及由權力所導致的利益問題。在現實政治中,“自我”總是有意識地將“他者”想象和打扮成危及“自我”利益的“敵人”。在政治參與過程中的主體都是理性的參與者,即使是在群體無意識的政治參與中,其目的都與利益相關。為了保全或最大化“自我”的利益,主體與主體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才成為了一種“非此即彼”的有意識選擇的“自我”和“他者”形象。
第三,文化政治的形成有著現代世界歷史所形成的民族國家這一現實原因。
在前現代的區域歷史中,由于交通與信息交流的限制,使得政治上的直接利益訴求也局限于區域范圍之內,所以文化上的“他者”與政治上的“他者”相對分離。以佛教為例,東漢末年佛教東傳,到唐代形成儒、佛、道并存的局面。雖然如韓愈等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力辟佛老,但是并沒有導致文化政治的發生。
近現代隨著西方率先現代化,在工業和科技的推動下,歷史也由區域歷史進入世界歷史。與此同時,基于對傳統歷史、語言和文化等的認同,王權國家逐步退出舞臺,在文化認同上的民族國家紛紛建立。民族國家的建立為文化和政治上的“他者”與“自我”意識相結合提供了現實的條件。
就文化而言,民族國家的建立本身奠基于共同或相似的文化心理。文化上的同質與相似,為其鑄就了一個摒離“他者”的藩籬。就政治而言,民族國家本身如何有效地獲得和拓展 “自我”的權力與由此而來的利益,是民族國家的主要目標。漢斯·摩根索在《國家間的政治》中言“國際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樣,是追逐權力的斗爭。無論國際政治的終極目標是什么,權力總是它的直接目標”。
至此,文化政治的形成就成為了必然。漢斯·摩根索認為帝國主義有三種手段:軍事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軍事帝國主義是最為明顯的卻難以預估結果的手段,經濟帝國通過隱性手段支配和控制他國,而文化帝國主義“他的目的不是征服領土和控制經濟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們的心靈,以此作為改變兩國之間權力關系的手段”。趙汀陽也認為文化天生就具有權力因素,文化作為一種“不能獨占而不得不分享”的物品“越被公共開采和使用,儲量就越變越多,利用價值就越來越大,權力也就越來越大,它就控制著越來越多的心靈和行為”。
在文化政治中,文化交往的過程實質是文化政治展開的過程,是隱藏在文化之后的政治進行權力規則和權力系統的建構過程。通過文化中的意識形態的灌輸、公共輿論的操縱、日常交往的影響,政治將文化中的異己的“他者”賦予“野蠻”、“落后”、“無知”等標簽。伊斯蘭世界將政治與伊斯蘭教結合,并積極倡導伊斯蘭教的優越性;歐美世界將民主、自由與基督教結合,并積極倡導一種普世主義。正如薩義德所言:“歐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種使一文化在歐洲內和歐洲外都獲得霸權地位的東西——認為歐洲民族和文化優越于所有非歐洲的民族和文化。”
當政治以文化的形態表現出對“他者”的拒斥時,民族國家間的格局與關系就表現為文化的斗爭。在文化政治格局下,國家之間的沖突就成為了 “世界范圍內的部落沖突”、“文明的沖突”,即一種文化沖突。“在這個新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 ”
因此,如何有效地在民族國家體系中維護本民族的利益,從文化本身對文化政治的拒斥來看,儒家的文化復興就是必然。在“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60多位學者發表了《甲申文化宣言》,要求捍衛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尊重異質文明、保護各國和各民族的文化傳統。他們或從多元主義、或從本民族中的普世主義尋求對文化政治的應對之方。
問題的關鍵是,對于異己的“他者”無論是強勢的“自我”抑或“弱勢”的“自我”,應當持允怎樣的一種態度?或者就儒學而言,儒學在復興中應當采取何種方式和路徑對文化政治中的 “他者”進行回應呢?是在民族國家視閾之下的非此即彼的“自我”堅守,抑或是超越民族國家的“自我”、“他者”發現一些更為公允的原則?
二、“自我”與“他者”的堅守與超越:當代儒家文化復興的兩條路徑
對于最近幾十年來的儒學復興,已經有學者對其形態、特質等進行了分析,如李承貴將當代儒學劃分為宗教儒學、政治儒學、哲學儒學、倫理儒學和生活儒學。而立足于民族國家和民族國家間的關系來進行分析的較少。
這十幾年中,繼港臺新儒家和海外新儒家之后,涌現出了一批致力于儒家傳統與現代生活相結合的一批學者,如蔣慶、陳明、黃玉順、干春松、秋風、康曉光等。他們或是致力于某特定范疇的研究,或是致力于儒學體系化的建設,學界一般將其稱為“大陸新儒家”。在大陸新儒家內部,以何路徑來對西方文化政治的“他者”進行回應也各不相同。大致而言,大陸新儒家內部已經分化為以蔣慶為代表的立足民族國家和以黃玉順、干春松為代表的試圖超越民族國家的兩個不同路徑。下面簡要以蔣慶和黃玉順、干春松為代表分析之。
1.“他者”的拒斥:民族國家視角下蔣慶之儒教政治
作為當代大陸新儒家的代表,蔣慶無疑是起步較早也是最具爭議性的人物。1989年他在《鵝湖》上即發表了《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一文,提出儒學復興的必要。截至目前,無論是主流意識形態還是儒學界內部,都對其評價不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從思想的基點而言,他試圖從堅守民族性和民族國家的立場,對以西方為主要對象的“他者”予以拒斥;從途徑上說,他訴諸宗教——儒教這一復古形式以期保持儒家文化的純粹性。
從民族國家角度對中國文化“自我”的堅守是蔣慶儒教體系的邏輯起點。蔣慶認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本,文化亡則民族亡、國家亡。“依中國人的歷史觀,亡國不可怕,亡國可以復國,社會生活依然存在;亡天下亦不可怕,亡天下可以復天下,社會生活依然存在;中國人最怕是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著亡價值,亡價值則使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可能,是人類萬劫不復的災難。”
為保持中國文化的“自性”,蔣慶形成了中西文化“自我”、“他者”的判然二分,認為在中國,任何政治建構只有符合相關的中國歷史文化才能具有正當性,而脫離了中國歷史文化或是從中國歷史文化中開出了“他者”的文化都是不正當的。
以“三重合法性”為例,蔣慶認為“王道通三”,中國政治只有具有了天道、歷史與民意的認同才能將“國民的服從變成政治的義務”,才具有合法性可言。“政治權力必須同時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才具有政治統治的正當理由。‘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 ”
以此,他對西方進行了批評:“反觀自由民主政治,在合法性問題上只具有‘一重合法性’,即只具有‘主權在民’法理原則下的民意合法性,并且一重獨大,排斥超越神圣的合法性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使‘三重合法性’不能實現‘政道制衡’,從而使所謂的憲政制度安排只局限在為民意一重合法性服務的偏狹格局中。”
蔣慶簡單地認為民主只是在西方文化基礎上產生的,所以秉承“自我”文化優越論,認為西方政治只具有民意合法性。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理解,而分析蔣慶之三重合法性,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合法性并不在于數量上的累加,三重合法性與一重合法性之間并不能僅從數量上就能決定其優劣。
第二,從中國政治思想的本意而言,所謂天道合法性其實是民意合法性的一種外在表現。湯武革命之后,周初統治者面臨著如何以天命解釋和確立周代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周公等一方面敬天法祖宗,另一方面又提出 “惟命不于常”(《尚書·康誥》)的觀念。這種天命的轉換實質上表現出來的就是民意。《尚書·康誥》中周公與康叔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應當說周公這里的主張一改周代之前的天命觀,將民情賦予天,使得周代的天走出了神秘主義,并被賦予了民本主義色彩。自此之后,儒家的天、君、民的關系其實是:民意體現天命,符合民意天命而為天子,天子統治人民。所以,天的合法性實質就是民意合法性的體現。
第三,從合法性的歷史文化因素而言,蔣慶將歷史文化存在者化。在其觀念中總是認為有一個凝固而物化的歷史文化在那里,而實質上歷史文化是不斷更新和被詮釋、賦予新的意義,并非歷史文化中沒有的東西在現實中就沒有合法性。在儒家文化圈中,臺灣、香港的文化也屬于儒家文化,但臺灣等相關的“政府”并沒有產生來自歷史文化方面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機。
在具體的政治建構中,蔣慶訴諸宗教——儒教形式,以期通過復古宗教的形式保持中華文化的純粹血統,從而與西方文化相區別。
蔣慶將儒學置于儒教之下,并從時間和超越性上認為儒教是“五千年中國人所共奉之超越神圣價值”,而儒學只是在漢代政制設計過程中超越了儒教。“在政制設計時降低儒教在歷史形成之獨尊地位,有否定六千五百年中國人共同同意之虞,于民主原則亦有所違背矣。 ”因此,在他看來,中國未來的政治設計必然以儒教為尊。
在具體的政治設計中,蔣慶依照三重合法性設置了通儒院、國體院、庶民院。通儒院,由儒者組成,以四書五經與天道為依據,體現的是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國體院,由歷代帝王君主圣賢忠烈后裔推選,代表著國家歷史性的承續,體現的是歷史文化的合法性;庶民院則由單子式的個人和團體組成,體現的是民意的合法性。
蔣慶認為,通儒院和國體院都是“善的制度性力量”,對于民意之惡能夠進行有限的鉗制。這種“善”的力量,或者僅僅因為與圣賢有血緣關系,或者嫻熟于圣王經典,實質上是在一種文化無意識之下對于“自我”有限性缺乏反思的表現。
2.“他者”的消解:世界體系視角下黃玉順與干春松的儒家哲學
與蔣慶立足于民族性和民族國家的基點不同,在大陸新儒家的內部以黃玉順和干春松為代表的一派,試圖超越民族國家,立足于天下體系以消解“他者”。
黃玉順在中西比較哲學的視野下提出了其生活儒學,目前積極致力于中國正義論的具體建構;干春松在近代哲學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度儒學,并于最近出版了《重回王道——儒家與世界秩序》。
黃玉順從民族性和現代性雙重角度對儒學發展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現代化是中國未來的必然方向,特別是在民族國家的體系下,只有現代化才有可能保種保國。現代化也是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因為西方經濟、政治現代化,“先行的事情是觀念的現代化”,而觀念的現代化則必須對傳統進行新的闡釋。
“我們的民族國家的命運一定離不開儒學的復興。因為民族國家同時具有兩個相互涵攝的維度,缺一不可:一個是現代性的維度,另一個就是民族性的維度。民族國家是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如果只有民族性的表達而沒有現代性訴求,就是原教旨主義;反之,如果只是現代性訴求而沒有民族性表達,就是自由主義西化派。”
在具體的正義論建構中,他提出了正義論的兩條原則:正當性原則和適宜性原則。所謂正當性原則即要求社會規范建構及其制度安排具有公正性、公平性。適宜性原則要求制度建構的空間性和時間性適宜,這種適宜性既涵蓋了自然空間也涵蓋了歷史文化空間,它所要求的是“歷時性的文化傳統被收攝于共時性的生活方式之中”。黃玉順試圖在民族國家體系下尋求一種既是普遍的,又應允多元民族性的正義論體系。
干春松將儒家文化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以民族國家解釋全球化背景下的沖突,并以“世界”為基點積極建構一種世界秩序。
干春松認為現有的民族國家體系是建立在利益和私欲上的政治體系。在這一體系之下“對利益和效能的追求促使國家之間并不真正尋求一種互利的秩序,任何國家都謀求成為強大的國家,只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形下,國家之間才尋求合作的可能性”。 以美國為例,美國沒有一個“世界價值觀”而有“美國利益至上”原則。因此,尋求一種“為人類提供一種表達人類共同價值的處理平臺”是對“他者”的有效的消解方式。
基于此,干春松提出了儒家王道秩序的觀念以期超越民族國家基點上的仇恨。其核心就是要推崇“天下一家”以情感消解敵意,使得每個人認識到除了個人、國家公民之外,又有一個新的身份,即全球公民的身份。在這種儒家的王道天下體系中,干春松認為應當首先“引入全球利益維度”,“反思啟蒙以來的人類發展模式”,“建立以個人和全球利益為基準的政治、法律體系”,“削弱各個國家的武裝力量”,“建立以自主公民為主體的自我管理的社團和組織”,“改革聯合國體系”,“通過協商建立一個議政機構”等。
三、余論:文化政治語境下的文化無意識與有限理性
文化作為基于歷史承續的意義系統,與個體生活緊密相連。實質上,個體作為存在者,當其被拋入這個世界之時,就處于一種文化的無意識之中。生活在特定的地區、特定的時間的人們將文化當作“現成之物”而缺乏反思。所以,在每一個族群觀念中都具有一種“自我”、“他者”的觀念,當這種文化的中心主義與政治相結合,“自我”與“他者”的對抗才變得越來越尖銳。
如何走出這種“自我”與“他者”的沖突,以及由此所帶來的文化與政治結合的文化政治,所需要的是各個族群走出這一文化無意識,謹持一種有限理性對其文化進行反思。面對多樣而復雜的世界,我們并不能自信地認為:僅僅以某一個族群的文化或觀念就可以徹底解決一切問題。不僅僅是對于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亦是如此。正如港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復觀所謂的“我不認為僅僅中國文化,便可以解決中國今日的問題。并且認為若僅僅肯定中國文化,且將無以防止中國文化本身所發生的流弊”。只有秉持如此態度,儒學才可能超越民族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煥發生命力。
注釋:
(1)這里所謂的儒學復興主要指的是儒學在理論界的復興,而并非社會意義上的儒學的普遍復興。雖然目前社會上流行各種祭孔讀經活動,但主要是以開發旅游資源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正如彭永捷所言,儒學的復興仍然是研究界小圈子的熱鬧,“儒家文化的處境可謂門庭冷落”。(彭永捷:《現代化背景下的儒學復興》,《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2)蔣慶儒學體系雖然內容很多,甚至他本人稱之為“政治儒學”,但以主要內容而言稱其為 “儒教政治”更為可行。關于文明沖突論的文章[M]//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