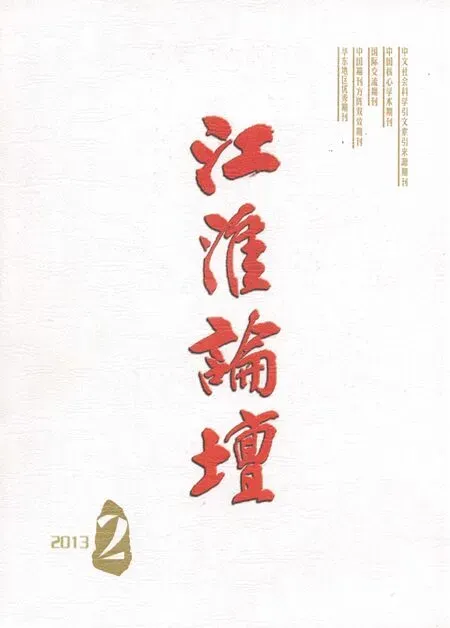文化斷裂帶上的足印﹡——論阿城的小說
王海燕
(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安徽安慶 246011)
經歷過“五四”激進的以啟蒙“現代性”為目的的“反傳統”和“文革”更為激進的以“破舊立新”為號召的“反傳統”,20 世紀80 年代,阿城這代作家無可選擇地站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帶上。 新生代的文化學者認為:“如果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傳統文化’被魯迅看作‘鐵屋子’, 并且對這種文化的認識本身也采取了一種寓言式的處理方式,那么,在80 年代特定歷史語境當中發生的‘尋根文學’,卻是一個關于中國文化的再辨析工程,人們開始在這‘鐵屋子’里挑挑揀揀, 試圖發掘那些還值得傳承下來的東西。在這里,不再簡單是‘中國/西方’、‘傳統/現代’的兩分結構,而是在此二元結構的基礎上‘中國’、‘傳統’ 本身的差異性也被提了出來。 而這種對‘中國性’自身的文化差異的追問,及其關于‘文化中國’的重構,使得一種不同于50—70 年代的‘民族性’敘事得以浮現,并成為80 至90 年代文化界的重要問題。 ”阿城是參與這場“關于中國文化再辨析工程”的作家。 他的“邊緣化”的小說,深植在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里,以包蘊、想象“中國文化”為手段,從而達到重構當代“文化中國”之目的。 他有著連接“傳統”與“現代”的極具個人化的方式。 他不算一個高產的作家,卻用精品,在中國文化斷裂帶上, 留下了與傳統文化筋骨相連的深深足印。 他再三說自己只是20 世紀80 年代創作的“個案”,“我的東西沒有普遍意義”。然而我們太需要對阿城式的“個案”給予剖析,由此看清“中國文化”傳承/揚棄、延續/重構的合理性、可能性、路徑方式、文學樣貌,切不可因其不入多種版本文學史的主流而將其隨意輕輕帶過。
一、邊緣化的人生啟蒙,邊緣化的人生經歷,與眾不同的“知識結構”,成就了阿城小說的“邊緣之相”。
阿城的父親, 著名的電影評論家鐘惦棐先生,因為《電影的鑼鼓》等評論,在1957 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全國知名右派。 家庭的政治變故,將共和國的同齡人阿城拋到了社會主流群體之外,因而成就了另一個被邊緣的、特立獨行也獨思的阿城。
被邊緣化和沒有尊嚴的憂憤,在阿城童年、少年的記憶里刻骨銘心,盡管他后來的小說,包括其他文類的文字, 從來都對被視作異類的傷痛顯得漫不經心,如同他在成名作《棋王》中,通過棋呆子王一生之口作出的聲明:“‘憂’這玩意兒,是他媽文人的佐料兒。 我們這種人,沒有什么憂,頂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而正是被邊緣化的政治遭遇, 導致阿城所受教育的邊緣化,進而是“知識結構”和“文化構成”的邊緣化。 北京琉璃廠的舊書鋪、古玩店、畫店成了少年阿城的課堂和“免費博物館”。 他聲稱“我的啟蒙是那里。 你的知識是從這兒來的,而不是從課堂上,從那個每學期發的課本。 這樣就開始有了不一樣的知識結構了, 和你同班同學不一樣,和你的同代人不一樣,最后是和正統的知識結構不一樣了。 知識結構會決定你”。 因此,阿城覺得人與人之間,“沒有代溝,只有知識結構溝”。
青年和中年的阿城繼續被邊緣:赴山西、內蒙、云南插隊十年有余(1968 年至1979 年);一作成名之后,他去了美國,又一個十年有余(1985年至1998 年)。 在國內外來來往往兩年后,2000年他終于又回到出生地北京。 倘若說前半段的“邊緣”是政治歧視,是人生無奈,那么后半段的“邊緣”則是“習慣”,是“選擇”,而不是“被”。 一路的人身歷練使阿城的小說也成就了一副 “邊緣之相”。
需要強調的是,成年之后阿城的“邊緣化”似乎比少年時代更多了一份理性的成熟和思想的深刻:他從社會底層的、從鄉村的、從少數民族地區的、從西方異質文化的諸多視角,看時代變遷的云卷云舒,看民族文化的變與不變。 阿城用他在“免費博物館”里的獲得,去確認民族文化深層那些積淀深厚、恒久不變的“常識”,去探究文化多元構成的歷史根系,去思考文化的顯性表達和隱性暗示,文化的規范性與非規范性的相互滲透參照,文化的普羅大眾和中產階級趣味,文化的“焦慮感”、另一種“焦慮感”和“不焦慮”,等等。
二、初始文本的“私密性”與不入文學主潮
因為被“邊緣化”的自知之明,阿城成為一個沒有強烈發表欲的作家。 請看他的幾段自白:
我在公開發表文字之前,也寫點兒東西給自己,極少,卻沒有誰來干涉,自由自在,連愛人都不大理會。 我想,任何人私下寫點兒東西,恐怕不受干涉的程度都不會低于我
……自由寫的東西若能滿足自己這個世界,足夠了。
《棋王》發表后,阿城1987 年在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訪問時這樣回答《華僑日報》文藝副刊記者的提問:
我寫好《棋王》后,一位朋友拿去看,他有一個在《上海文學》當編輯的朋友在他家里看到了手稿,就拿去發表了。 我都沒來得及表態,手稿的標點符號還沒寫清楚就給人發了。 發了以后就熱鬧起來,我也被人吊起來了。
2004 年阿城接受査建英女士訪談時說:
我寫的那些東西本來是私人交流的……這之前我寄過一些插隊時寫的東西給在紐約的丹青看過,也給美院的一些朋友看過。 八五年講給李陀他們聽的時候,李陀他們的鼓勵讓我明確知道,手抄的可以轉成鉛印的,可以給不認識的人看,這對我的心理有建設性,我永遠感謝李陀他們在這方面給我的幫助。
畫家陳丹青印證了阿城的如上所說:
從八三年夏天, 我記得此后一年多,阿城陸續寄了好多篇小說給我看,天哪,全是原稿啊!楞用圓珠筆寫的那種,寫在分行的、
有字格的紙上,一篇一篇寄過來。
阿城1991 年8 月18 日致法國評論家諾埃爾·迪特萊的信:
《遍地風流》 是我七十年代隨手寫下的一些文字,有關一些情緒,一些場景,一些人物和事物的印象。這些文字,通常很短,失散的也很多。 從鄉下回到北京后,曾投給文學雜志,被退回來,大概是無法歸類,小說? 散文? 筆記? 《棋王》發表后,各種雜志要稿很多,又很急,并且要求字數也多,于是兩三篇合為一組拿去發表, 即你看到的<之一>、<之三>等等。當時給出去很多,后來都想不清楚誰拿走了。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若干判斷:第一,阿城小說的諸多文本, 包括他轟動一時的成名作 《棋王》,本是私密之作,原來并未打算發表。 創作心態“自由自在”。 第二,“手抄”轉成“鉛印”有較長的時間差。 作品寫作的時間多在插隊之時,即文革時期或改革開放初期;成名作《棋王》發表的時間為1984 年,《遍地風流》 系列短篇單獨發表和結集出版更在其后,創作與發表的時間差十年左右乃至更長。 文稿一朝得見天日,彼時新時期文壇的主潮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已過月盈。 第三,沒有《上海文學》的那位編輯慧眼識珠,阿城不入主流的作品破土而出,更不知會推遲至何時。 第四,阿城“抽屜文學”的部分佚失——阿城稱“本來這類東西有上百篇的”, 而作家出版社結集阿城小說,1998 年《遍地風流》結集,計59 篇;2000 年《棋王》結集,計10 篇;兩集無重復。 粗算即知:佚失數可觀。
文學史家喜好歸類。 不入文壇主潮的阿城,在多種版本的文學史中, 被歸類至 “尋根派”作家,理由自然是因為他們的“同”:他是以韓少功“尋根宣言”《文學的“根”》為代表的若干篇著名“尋根論”的作者之一,阿城的《文化制約著人類》屢屢被研究者所引證。 他對新時期初期的中國文學“常常只包涵社會學的內容”頗感“悲觀”:“社會學當然是小說應該關照的層面,但社會學不能涵蓋文化, 相反文化卻能涵蓋社會學以及其他”。阿城從政治、經濟的“問題小說”的新套中退卻,也不再滿足于對民俗民風的一般描摹,而是從文化視角對現象世界作審美的整體把握。 他不僅反對“把民族文化判給階級文化,橫掃一遍”的“文革”,也對管窺蠡測的某類中國“主流小說史”疑竇重重,進而頑強地試圖重建“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的關系,《閑話閑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表達了他對中國小說史的種種新論。 這些都是他與尋根群體同氣相求的佐證。 他聲明:“我是支持‘尋根派’的,為什么呢? 因為畢竟是要去找不同的知識構成,補齊文化結構,你看世界一定就不同了。 ”“排列組合多了,就不再是單薄的文化構成了”。然而我們必須承認,阿城與尋根群體是有差異的, 他本人提到過這種 “差異”:“‘尋根’是韓少功的貢獻。 我只是對知識構成和文化結構有興趣。 ”“我的文化構成讓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尋。 韓少功有點像突然發現一個新東西。 原來整個在共和國的單一構成里,突然發現其實是熟視無睹的東西。 ”差異還表現在,另立新旗的群體急于形成有理論、 有實績的潮流,從而獲得文壇認可。1984 年底的“杭州會議”,便是尋根作家和評論家們的一次“文化合謀”。 而阿城始終寵辱不驚地玩著一個人的游戲——“抽屜” 里的東西早已形成——他習慣聽從自己,聽從“免費博物館”的浸染,別無選擇。 他對“尋根文學”有個人的基本判斷:“尋根沒有造成新的知識構成。 ”他本人也“造不成新的文體”。
三、阿城小說的“風度”
2006 年底, 王德威先生以 《想象中國的方法——以小說史研究為中心》 在北大中文系演講,他提出了其個人在小說史研究的論點:“我覺得在19、20 世紀漫長的小說現代化的過程里,早期作家學者的目標是‘祛魅’,無論是魯迅個人或是他所代表的批判寫實主義,都希望把小說作為針砭現實人生的利器,將傳統中陰魂不散的鬼魅祛除。 但是過了一個世紀之后,我們所從事的工作,尤其是在小說界,可能是‘招魂’。 有心的作家希望借小說再次把我們曾經失去或者錯過的各種斑駁的記憶,紛亂的生活體驗,各樣的理念情緒重新思考反省。 中國現代性在啟蒙和革命之外,也許還有些別的?”無論如何,阿城都應算作“招魂”的作家,而值得深入討論的是,他的“別的”,究竟是何種模樣?
評家大多偏愛阿城的“三王”,而對他個人化風格更為突出的《遍地風流》中的幾十個短篇缺乏重視。 阿城這樣解釋他的《遍地風流》中“風流”一詞:“‘風流’中的‘風’,是‘風度’,我此處結合了風俗、風度兩層意思,每個短篇中亦是在捕捉風俗和風度,包括自然景物的風度。 ”“風度是指不自覺的時候,自覺了,就是摹仿出來的,也就不是風度了。 總之,《遍地風流》用直白的話說,就是‘這塊土地上的各種風度’。 ”評論阿城小說,我想“風度”實在是最貼切的詞語。
下文我們探討阿城別一樣的“招魂”的“風度”:
第一,“不焦慮”的風度。
阿城以為:由于西方文化的進入,“五四那些人是有‘焦慮感’的”,“焦慮”的結果是五四以后的小說“文以載道”:“以前說‘文以載道’,這個‘道’是由文章來載的,小說不載。 小說若載道,何至于在古代叫人目為閑書? 古典小說至多有個‘勸’,勸過了,該講什么講什么。 梁啟超將‘小說’當‘文’來用,此例一開,‘道’就一路載下來,小說一直被壓得半蹲著,蹲久了居然也就習慣了。”面對訪談主持人的插言:“我們接觸到的很多東西都是焦慮的人寫出來的創作,爭論也好,問題的提出也好,都是焦慮心態的產物。結果反而淹沒了你說的這種人的聲音。 ”阿城堅稱:“我不焦慮。 ”他還進一步說明:“當你的知識結構擴展改變的時候,問題改變了。 這時你發現,還有東西。 ”于是,他別開生面地從歷史的、文化的、哲學的、宗教的等等方面討論這個“焦慮”。他批評“由于焦慮,我們現在對時間的承受力越來越脆弱,急得就像火燒猴屁股:一萬年太久! 中國這才一百年,到五百年的時候,你再去看。 ”
“不焦慮”的阿城,寫“不焦慮”的小說:他不是從顯性的、單一的政治層面干預生活,而是從歷史的、文化的、人性的層面展示生活;他以民間的價值立場,個體的價值恪守,外道內儒的文化傾向,不入主潮的小說樣貌,對抗人文環境反人道、反科學的時風;他以“歷史過程”拉長了睹物觀世的焦距,以“邊緣化”拓寬了“民族文化”的空間;他別有一種經歷過大風暴之后的從容、淡定、敏銳、深邃。
《棋王》 一出, 不少評家狂評阿城與道家文化,對共和國的同齡人竟然衣缽老莊,頗感好奇和疑惑,也有讀出儒家精神者,那似乎只是附加或至多是互補。 后來,我們讀到阿城如下文字,才有些許醒悟:
我喜歡孔子的入世,入得很清晰,有智慧,含幽默,實實在在不標榜。道家則總有點標榜的味道,從古到今,不斷地有人用道家來標榜自己,因為實在是太方便了。 我曾在《棋王》里寫過一個光頭老者(本文作者注:車輪戰中求平手言和者),滿口道禪,捧起人來玄虛得不得了, 其實是為遮自己的面子。我在生活中碰到不少這種人,還常常要來拍你的肩膀。汪曾祺先生曾寫過篇文章警惕我不要陷在道家里,拳拳之心,大概是被光頭老者蒙蔽了。
細讀起來, 阿城的小說實在都是入世的小說。 他推崇儒家文化所建立的社會基本規則、道德理想和倫理, 譬如 “信用”、“助人”、“尊重隱私”、做人“最起碼的教養”等,把它看作文化傳承中的“常識”,需要格外地看護和恪守。 這些也是他讀雜書所形成的“知識結構”的價值核心,進而成為小說文本的價值核心。 看來“不載道”并非無“道”,只是不可以“腔”載罷了。 阿城討厭小說的“學生腔”、“文藝腔”,甚至還有“尋根腔”。
第二,“人性之真”的風度。
阿城說:“丹青(本文作者注:畫家陳丹青)要歷史之真,我比較要人性之真。”誠哉斯言。阿城小說人物的最有魅力處,即是“人性之真”。 他以邊緣人的視角,看邊緣人的生活形態,書寫人的純粹的或不那么純粹的動物性以及人的豐富的社會性,書寫“文明社會”遭受的種種污染,擁抱鄉土的、蠻荒的、原生形態的生命活力,眷戀歷史縱深處多姿多彩的文化遺存。 阿城在《思鄉與蛋白酶》、《愛情與化學》、《藝術與催眠》、《攻擊與人性》等散文中解讀人的動物性,當然那是科學而非文學,卻能證明他對人的動物性有相當專深的研究。 而文學是需要賦予科學以夢幻、以想象、以浪漫、以復雜、以意義、以多義的,從這個角度說,“阿城的小說”比“阿城的科學”(人類學研究)更有滋味,只是在“冷峻客觀”上,兩者常常相通。
阿城以人類亙古不變的生存形態彰顯“人性之真”。 他既善寫“衣食為本”,也善作“性的文學”。 于前者,一貫好評如潮;對后者,至今關注甚少。 評論夸贊阿城“民以食為天”的文本: 棋王王一生的吃相,知青們的蛇肉大餐,堪與任何中外文學經典相媲美。 更有好事者鼓動寫《吃王》,不知作者是否曾經心動。 評家又普遍認為阿城不善寫女人,不善寫愛情,這是誤讀。 《遍地風流》短篇里,隨處可見“性”的話題,只是寫了性壓抑的時代,性壓抑的男女,性的非常之態,讓人覺得荒謬和尷尬,卻為當代“史傳”平添了并非文人虛構的“傳奇”:插隊太行山的女知青,是在聽粗俗的村婦不堪入耳的“天罵”中獲得了人生的“性啟蒙”,想象并幻想著自己人生的第一次 “天罵”。 (《天罵》)油燈搖曳的夜晚,知青們借著講“同性戀”的故事壯膽,發展著“異性戀”的續篇,萬般無奈間還得鉆回“同性”的被窩。 (《兔子》)一對同班的少男少女,在懵懂交往中情竇初開,多少無法解釋的美麗“春夢”,最終破滅在“文革”中——女孩被打致死,罪名是:勾引腐蝕紅衛兵。 (《春夢》)在部隊養鴨養豬的大兵,復員回鄉找不到老婆,因與人打賭:女知青的裙子里是否穿了褲子,忍不住還想驗證,被判流氓罪,死刑立即執行。 (《打賭》)愛情多么需要氛圍,多么需要情調,多么需要詩歌,多么需要文學的助興,知青們因為青春年少和教化,并不缺少這一切:《秋天》寫秋的美景,秋的悠然,“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何時采菊? 而且悠然?秋天嘛”。知青由此快樂,由此沖動,由此野合,由此還想刻一枚“山氣日夕佳”的閑章。 然而,“悠然”毀滅于現實殘酷——村婦與人“耍流氓”,丈夫弄個狗皮睡在炕下,一個男人每次付給兩分錢;于是知青揭發,吊打了那個女人;年底分紅, 村里每個勞動力的全部所得是六分錢——“山氣日夕佳”的閑章,從此沒有刻完。 (《秋天》)或許——從此, 阿城筆下無正常意義的女人,無抒情想象的浪漫愛情。
阿城善寫母性。 他說:“女子在世俗中特別韌,為什么? 因為女子有母性。 因為要養育,母性極其韌,韌到有俠氣,這種俠氣亦是嫵媚,世俗間的第一等嫵媚。 我亦是偶有頹喪,就到熱鬧處去張望女子。 ”“韌”的母性是災難的避風港,《棋王》中命途多舛的母親,《會餐》中如老獸哺育幼仔的母親們,無不令人動容。 這一定還因為,阿城本人也有一位偉大和敢于擔當的母親。
歷史常常是由“大說”構成的。 阿城對所經歷的歷史重大事件敏感而又記憶深刻,而搬進小說里, 他不惜堂皇地揀拾歷史學家遺落的餅屑,這倒回歸了“小說”發生之時的本相。 讀那些鐫刻下時代印痕的情節、細節,體悟歷史是如何從貼近平民而走向真實,如何從一斑而窺見全豹,如何完成宏大與卑微的鏈接,意義是如何產生或者被解構。 這一刻,“人性”在“小說”里扮演著書寫者賦予的最為重要的角色。
1966 年領袖接見紅衛兵的歷史大事件,阿城小說的透視點卻縮小至:“天安門廣場遺留下近五萬雙被踩落的鞋子, 包括初中一年級學生王樹林明年的新布鞋。 ”小說開篇為“布鞋”作了足夠的鋪敘,那是物質匱乏年代,貧民之家,姥姥千辛萬苦,千針萬線,為外孫備下的第二年必須穿滿大半年的單鞋。 于是,宏大的、偉人的、有“革命意義”的歷史一刻,與微小的、庶民的、初中生切身感受的歷史事件, 產生了對話和張力(《布鞋》)。《小雀》、《縱火》等篇,也篇篇皆有“大說”與“小說”碰撞的力度,錯位的驚悚,纏繞的魅力。 于是,歷史因歷史邏輯而宏大,小說因人性真實而鮮活。
第三,“筆記”體的風度。
“筆記” 體在當代中國小說作家眼中是陌生的、久違了的文體,但在文類革故鼎新的歷史演進中卻源遠流長,枝葉繁茂。 陳平原先生的專著《中國散文小說史》,既定義了散文和小說作為文學的兩大門類,各自的“獨立性”——兩者之間的“差異”,更別開一路地討論了兩者之“合”,兩者某種程度的互補互動。 他對“中國小說”和“中國散文”發展過程中,兩者互為“刺激”、互為“啟迪”,“穿越文類邊界的嘗試”大加贊賞,他說:“在這方面,作為中介的‘筆記’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在我看來,正是借助這座橋梁,超越小說與散文的‘邊界’,才比較容易獲得成功。 ‘筆記’之龐雜,使得其幾乎無所不包。 若作為獨立的文類考察,這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但任何文類都可自由出入,這一開放的空間促成文學類型的雜交以及變異。 對于散文與小說來說,借助筆記進行對話,更是再合適不過的了——這是一個雙方都可介入,都與之淵源甚深的‘中間地帶’。 ”這無疑道出了“筆記”在中國文類演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阿城的肚里林林總總裝了為數可觀的 “筆記”,他向想要了解世俗變化的讀者,推薦“不妨多看野史、筆記”。 僅《魂與魄與鬼及孔子》、《還是鬼與魂與魄,這回加上神》兩篇,他便興趣盎然、饒有趣味地轉述過如下若干清人筆記: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劉熾昌《客窗閑話》、俞樾《右臺仙館筆記》、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袁枚《子不語》、李慶辰《醉茶志怪》,等等。 他還由“筆記”勾連出當代作家汪曾祺:“《閱微草堂筆記》 的細節是非文學性的,老老實實也結結實實。 汪曾祺先生的小說、散文、雜文都有這個特征,所以汪先生的文字幾乎是當代中國文字中僅有的沒有文藝腔的文字。 ”“明清筆記中多是這樣。 這就是一筆財富了。”其實,阿城與汪曾祺本是路徑一致,他才會如此惺惺相惜。
阿城的小說,尤其是結集于《遍地風流》的短篇,彰顯了文化斷層中難得的“筆記”體風貌:隨筆隨記的敘述風格,截取或人或事或景,不求敘述的完整,卻多有志奇志怪的跌宕;皮俗而骨雅,貼近俗世俗景,于樸野中透出文人情致、意趣、哲思;清俊搖曳、極簡極凈的文筆,在當代文壇能比肩者寥寥。
阿城的筆記體小說以俗為美。 他明白:“中國小說古來就是跟著世俗走的,包括現在認為地位最高的《紅樓夢》,也是世俗小說。 中國小說在‘五四’以后被拔得很高,用來改造國民性,性質轉成反世俗,變得太有為。 八十年代末,中國內地小說開始返回世俗。這大概是命運?‘性格即命運’,中國小說的性格是世俗。 ”王德威先生在北大的演講特別強調了阿城《遍地風流》世界里的“風流人物”,是只有屁股眼是白的礦夫,站在紀念堂頂順風撒尿的建筑工人, 穿著肥料袋做褲子的農民, 干校搗糞的學員……特別強調那些不文雅的、殘暴的、慘烈的場面,他說:“這個是中國傳統抒情詩學不會碰到的。 可是我認為阿城是有意為之。 而且他必須要寫到這么粗俗,這么狂野,才能用來作為某一種抒情藝術形式的反省,以及對文類本身的批判,以及接之而來的超越。 ”王先生無疑點明了阿城小說最為重要的一面。 然而另一方面他或許還來不及細講——阿城在不恥于言俗的同時, 骨子里推崇歷代中產階級的趣味、修養。 他有中產階級崇拜癥。 阿城毫不掩飾地表明:“其實后來想起來,我喜歡那個時期,就因為中國有那么多不焦慮的人,他們在看莫奈、看梵高、看康定斯基,看左翼引進來的麥綏萊勒、柯勒惠支,表現主義的格羅茲,還有魯迅喜歡的比亞茲萊。 ”阿城認為,藝術、文化是奢侈的事情,“中國文化的事情是中國農業中產階級的事情”,而“文化產生的那個土壤被清除了。 剩下的,其實叫文化知識”。阿城嘆息文化的“根”被斬斷,他憑吊“根”文化的審美旨趣。
阿城的《棋王》,從最底層的貧民到曾經衣食無憂的中產家庭,筆涉物質層面的生存到精神層面的需求——一面是知青的 “群體記憶”: 關于“吃”和“餓”的故事;另一面則由家世不凡的知青“腳卵”回顧別一樣的傳統:名人云集,高朋滿座,吃蟹,下棋,品酒,作詩。 小說中的“我”會不合時宜地談論杰克·倫敦、巴爾扎克,幼時曾見過的荷蘭畫家倫勃朗的名作《夜巡》,曹操的《短歌行》。會筆涉在河邊畫裸體寫生的無名畫家的人體審美論。 小說在更高的哲學層面,借神秘的“撿爛紙的老頭兒”談“道家陰陽”,“棋道”與“生道”;借未出場的“腳卵”父親,傳亂世生存之學。 這是阿城的另一種嘗試和反省,他沒有從“文革”流行的階級對立的視角走進故事縱深——一副王一生母親撿牙刷把磨制的讓人潸然淚下的 “無字棋”和另一副“腳卵”家祖傳的“明朝烏木棋”成為符號,前者指代人性母性,后者指代生存智慧和文化審美,它們的出場,完成了文化的物質性和精神性的匯合,即是小說篇末所言:“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可囿在其中,終于還不太象人。 ”
讀《遍地風流》,看文明的碎片,邊關景色中蘊含的文人審美理想:小河、草岡,草原青年男女間的打趣挑逗。情歌悠揚,愛情似火。(《洗澡》)峽谷、巨石、藍天、大樹、雄鷹、駿馬、騎手,三五人家,一幢石屋,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仿佛廣袤蒼穹,時間凝固,一派天高皇帝遠的景象。 (《峽谷》)想想是作者隨記于階級斗爭斗得雞飛狗跳的年月,寄予的情感,既在文里,更在文外。
異族風情書寫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首領、馬幫、藏漢,氣貫滇西的怒江,懸于萬丈絕壁間的溜索,“命在天上”的過溜索的體驗,人與自然的和諧,人搏自然的雄壯。 (《溜索》)
阿城小說落筆時選擇刻意近俗而貌似避雅,除對傳統小說與世俗的關系了然于胸之外,還源自他藝術品位很高的父親。 阿城懷念父親的指點:“八十年代我發表小說,我父親從雜志上看到了,批評我在小說里提到巴爾扎克,杰克·倫敦。知道而不顯出,是一種修養。 就好像寫詩,用典,不是好詩。 唐詩不太用典,并不表明他們不知道唐以前的典故。 你看李白、李賀,直出,有自我的元氣。 ”阿城后來發表的《遍地風流》幾十個短篇,“直出”居多,“元氣”十足,避雅而不失雅,俗中藏雅——批評家是高人,小說家才受益良多。
小 結
阿城多少有些“偶然”地登上20 世紀80 年代文壇,他的小說“風度”卻昭示了歷史的必然:文化斷裂帶上, 文人們總會留下歷史深深淺淺的印痕,即便焚書坑儒,即使經歷激進變革,中華文化都將直面難以割斷的血脈。 傳承和變革缺一足便得跛行。 種子播撒于民間,根須伸展于街巷阡陌間,人為斬斷,只能讓顯態文化即刻變臉,隱文或“手抄”于地下,或擱置于“抽屜”,正如棋王王一生所說,“棋譜” 毀了,“好在書已在我腦子里”。 春風又度, 自會再現星星點點的“綠”。 中國當代小說史上,阿城的那些邊緣的、人性的、 久違了的筆記體的作品, 正是古老的“根”綻出的新鮮的“綠”。
[1]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68.
[2]査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M].北京:三聯書店,2006.
[3]阿城.棋王[M]//吳亮,章平,宗仁發.民族文化派小說.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
[4]阿城.文化制約著人類[N].文藝報,1985-07-06.
[5]阿城訪談.文學報,1987-03-19.
[6]阿城.阿城致諾埃爾·迪特萊的信[M]//阿城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7]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M].北京:三聯書店,2010.
[8]阿城.閑話閑說[M]//阿城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9]阿城.魂與魄與鬼及孔子[M]//阿城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10]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4-15.
[11]阿城.威尼斯日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