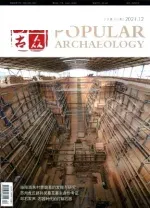良渚文化“人鳥獸”合一玉器蘊意新解
文 圖 /十 工

江蘇昆山趙陵山新石器時代遺址77號墓出土現場

2007年,南京博物院聯合《揚子晚報》,舉辦了“南京博物院鎮院之寶”的甄選活動。在豐富的院藏品中,18件珍寶脫穎而出,若按時代排序的話,名列首位便是出自江蘇昆山趙陵山新石器時代遺址77號墓的那件透雕“人鳥獸”玉飾件。2008年它被選作國寶級展品,參加首都博物館舉辦的迎接奧運之“中國記憶5000年文明瑰寶展”。2012年,它又遠赴英倫,放置于埃塞克斯郡“中國珍寶展”的顯著位置。為什么一件不足6厘米的小玉件,竟然讓大家驚嘆不已?簡潔構圖下蘊含了什么樣的意義,讓美術史與思想史研究者沉醉其中呢?另外,在此之前,對于類似尖狀的弧形器形,在文物學上多以解繩用途的“觿”命名,或籠統地命名為“掛飾”,但是它準確的名稱又該是什么呢?若從良渚先民制造和使用它的角度去剖析,可能會有一些新的發現。本文即是一次小小的嘗試。
構圖及蘊意
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這件玉飾件的基本情況:它僅長5.08、寬2.95、厚0.32~0.48厘米。玉質呈淺綠色,不過大部分已經受沁呈雞骨白色,不透光,表面少量紅褐色沁斑。它整體為弧條型片狀,頂端偏厚,底端較薄,除鏤孔處側邊外,均經過打凹抹邊處理。整體可以分成上、下兩部分,上部為該器的主體圖案區域,兩側紋飾相同,下部為突出的榫頭。主體圖案頂部為一只立眼平視、長吻翹尾的小鳥,它的胸部下垂,做蹲踞的棲息狀;下面匍匐的小獸與鳥腹下部相接,且前、后腳分別立于下方人物頭部;人物頭帶 “羽毛”頭冠,冠頂與小獸相接,顏面內凹、翹鼻,下顎微突出,頸部很短,胸部卻凸起,手臂后舉與獸尾部相接,人物下體作屈膝蹲踞式。除鏤孔的內部,整體玉飾上打磨出平整的玻璃狀光澤,靠近“尖頭”部分有多個打磨粗糙面。
觿:古代用骨或玉制成的解繩結的錐子,也用作佩飾。
玉器之所以受沁,實質上是受自然環境下的風化作用與浸蝕作用所致,通常需百年以上方能受沁。
白沁現象(俗稱鈣化):玉器經長期風化作用,在器表或孔隙內附著一些白色粉末,或生成一層白色松軟的包體。閃玉白化后,比重常常會變輕,硬度也會下降。凡入土時間長的高古玉,或因水土環境、或因玉質較次,造成白化嚴重,而呈雞骨白、象牙白,甚至會完全腐化變質。“人鳥獸”玉飾件即是受白沁后呈雞骨白色。
類似的還有黑沁現象(俗稱黑漆古、水銀沁)、紅沁現象(俗稱血沁,如“棗皮紅”、“灑金沁”)和土沁現象(如“老甘黃”、“松香沁”)。
若經細致觀察:人物羽冠部分的長條狀凹槽一側邊與短側面凹槽相接,另一側面與短側面略顯錯位;人物一側臀部保留短小的切割痕跡;鏤孔內面,保留的制作痕跡不明顯,僅在人物手臂的較長鏤孔處,保留有類似線切割痕跡。這些均說明此件玉飾是由手工并借助簡單的工具琢磨而成。
鳥兒停留在人冠帽尖端的羽翎上,似乎在遙望。鳥是人類伴侶,它們展開翅膀在空中飛翔,展示神奇的魅力,不能不讓人感到神秘和崇敬。良渚先民觀察著鳥兒的一舉一動,獲取有關節令、時辰、天氣等等自然界的變化信息。在浩瀚的天穹中,光芒四射的太陽威力最大,先民們把太陽作為上天世界的主神。自由自在飛翔的鳥兒,與太陽最為接近,人們便認為鳥兒正是太陽的精靈,神鳥是太陽神的化身。
若犬若豕的走獸,頭上尾下的向上攀爬,利用前后肢與冠帽的巧妙相接,將人與鳥、獸關聯起來。而走獸則又是與大地最親近的神靈,他們奔走于曠野、山巒之間,與先民的生活密切相連。其中部分種類被馴養后,或是成為人類的朋友,或是成為為人類提供生活保障的食物來源,與遙不可及的飛鳥相比,它們與人類的關系更實際、也更加密不可分。

鳥局部

獸局部

人局部
人居于最下端,也是構圖的基礎,冠頂為鳥,手托走獸。我們可以從眾多良渚時期的蹲踞狀人物形象中推測,冠帶羽翎的他(她)一定是一位具有崇高地位的人物,他(她)這一番異常于生產或者生活狀態的肢體動作,所表達的應該是某種具有特殊意義的行為,也許我們可以將其看作為一種“儀式”。而這種儀式所要表達的是對太陽崇拜或鳥崇拜,與大地崇敬的交融,形成了自然神與通神人物合并的崇拜模式。
很多學者認為,這件由人、鳥、獸組合構圖的玉器寓意,正體現了“天地人合一”,也可以解釋為良渚時期的顯貴者們借助鳥和獸這些有靈性的伙伴,集祖先、天、地于一體,上天通神,崇敬山川。這預示著良渚先民們逐步脫離原始單一信仰的宗教觀念,邁向系統的神靈崇拜。無怪乎眾多熱衷于玉器、美術史及思想史的學者對它長久不衰地沉醉研究與癡迷探索 。

趙陵山“人鳥獸”玉飾展開想象圖

反山玉琮神人獸面像從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其他墓葬出土物來看,當時的人們似乎對將自然神與通神人物合并有著特殊的執念,借此表達對自然的崇拜。
正名
當我們從這件玉器的構圖大致推想出其所表達的寓意后,接下來,它的用途便成為了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當然,討論一件器物的用途,不能不思考它們原本使用時的狀態,而對于墓葬,就不能不去了解它出土時的狀態以及與周邊伴出物的關系了。
根據趙陵山77號墓的出土情況,墓坑內發掘出長方形的葬具(即棺材),在清理完蓋板后,才顯露出層層疊壓在墓主人身上用以隨葬的石鉞。“人鳥獸”玉飾件則被一件大石鉞掩壓著,鳥與部分的羽翎從這件大石鉞的孔部露出;玉飾有部分壓著另一件石鉞的刃部。所以玉飾件無疑應出于葬具內部,發現時與墓主的相對位置是位于右腿脛骨外(右)側。
巨大的石鉞與“人鳥獸”玉飾同時發現并不是巧合。鉞,在石器時代是一類脫離于實際生產的具有一定權力或者禮儀象征意義的器物。與玉飾同時出土的這件石鉞孔部涂飾著朱砂、表面打磨有玻璃狀光澤,且為良渚文化中目前發現的尺寸最大者,在早期的研究討論里,一般將“人鳥獸”玉飾認為是這件巨大石鉞、甚至具體到為鉞孔內的裝飾品。但實際上,依據最新資料,它被鉞所掩壓,只是部分于鉞孔露出,由此可知道,“人鳥獸”玉飾在發現時與大石鉞的空間關系并不是同一個層面。那么,所謂玉飾原本是立于大石鉞孔部的推論便有可能不成立。
我們再來仔細觀察“人鳥獸”玉飾的細節:上部是嚴謹的、具有深邃含義的構圖,而下部——“人”腳部的穿孔周邊,光潔的拋光戛然而止,余下的是打磨毛糙的棱面狀。按照當時制玉水平,處理這些磨痕不是難事,所以這可能是制玉工匠為考慮其完工后的功用,有意識保留的痕跡。在此,我們當然有理由去認為此處的穿孔并不適合穿繩佩戴,這與先前所提及的“觿”的使用也并不契合;最重要的是,當穿繩佩戴后,所有的上部構圖將會180°的反轉,不符合人類通常的審美方式,并且無法合理地解釋穿孔周邊刻意保留的磨痕。


綜上,考慮到鳥在頂端、人腳穿孔向下的圖像構成,以及穿孔處周邊保留粗糙磨痕的尖狀類似“榫頭”,我們推斷,此類一端帶有榫頭的玉飾件,其使用時安裝復合方式應該與玉錐形器(良渚時期一類尖狀長錐形的玉飾件)和玉端飾(以復合的方式安裝于其他器物的上下端)類似,均由榫頭一端以復合方式插入另一物體卯孔內,并且大多有橫穿過銷孔的銷釘加固。但從造型上看,這類象形的飾件可能存在與錐形器和端飾不同的使用功能,為了區別于后兩者,我們暫命名為“人鳥獸”玉插件。
玉插件在嚴格意義上說同屬于玉端飾,而將前者劃分出來,主要是因為它的使用方式上應僅限于頂端,且從造型來看相對通常裝飾品而言,更具有特殊的意義。以“人鳥獸”玉插件為代表,人體蹲踞的形態或許正表達了通常在高等級玉器上所刻劃的正面神人獸面像的側視;而另一件著名的人形鏤空玉器,發現在與趙陵山遺址相距不遠的張陵山遺址與趙陵山77號墓葬時代相近的一座墓葬當中。將其與“人鳥獸”插件相比,除了沒有見到頂部的蹲鳥以外,攀爬的走獸也沒有具象地表現出來;而在安徽馬鞍山市的煙墩山遺址中,同樣見有類似的人形玉器,形態則更加抽象,可以推測趙陵山所發現的“人鳥獸”玉插件,可能是這些抽象玉制品靈感的來源。
復原與使用
這件“人鳥獸”玉插件的下端雖沒有類似錐形器突出的榫部,但依據近底部近乎尖狀的粗糙部分及圓形的銷孔,能夠推想出其插榫時的形態:
“人鳥獸”玉插件位于復合桿狀物(可能是竹木類制品)的上端,在桿的頂端事先鉆有銎孔(安裝柄或裝飾物的小孔),再將“人鳥獸”玉插件的下端尖部包括毛糙部分插入銎孔當中,可能在銎孔內涂抹有粘黏物,最后利用銷孔橫向將玉插件下端與桿子銷卯嚴密。同一墓中,在發現“人鳥獸”玉插件向北近50厘米處,發現一件制作精美的玉端飾,或許我們可以推測“人鳥獸”玉插件和玉端飾原本就屬于同一件器物。
2011年在上海福泉山吳家場良渚文化墓地中,發現底部加有端飾的弧形象牙“權杖”,考慮到“人鳥獸”玉插件具有弧線形的外部輪廓,所以連接插件與端飾的桿狀物很有可能具有弧形的彎曲,如此一來弧形所造成的傾斜也能將人、鳥放置于移動的不同觀察視角,讓該玉件更加具有靈動性。


余言
在史前考古發掘中,不僅能發現大量能夠證明它們所屬年代的常見器具,而且會發現一些令研究者們匪夷所思的新器物。史前時期沒有文字記錄,我們無法通過當時留下的文字去感知那個年代。對于那些器物功用與命名的探討,需要一絲不茍的田野考古清理技術與敏銳的觀察能力,并利用考古現場層位、痕跡與伴出物的關系,加上研究的經驗來拼湊、還原一個活態的歷史。
具象器物的復原研究僅僅是考古學器物研究的一個方面,小文即是以管中窺豹,聊以引玉。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