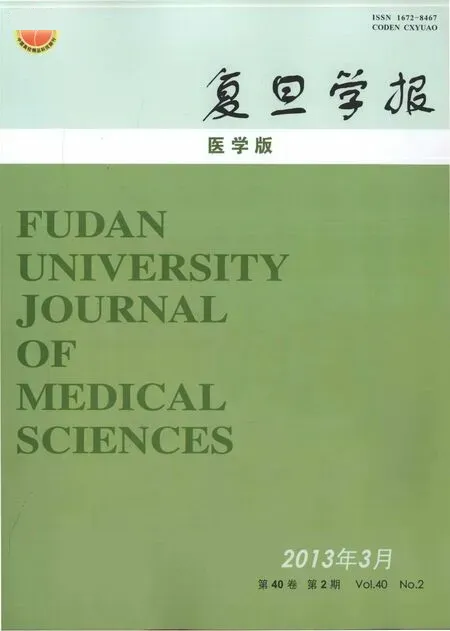白癜風患者應激生活事件及常見應激障礙調查
隗 祎 楊莉莉 劉海蕾 李 明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皮膚科 上海 200032)
白癜風是皮膚科的常見病,病因復雜,發病機制未明,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治療手段。作為一種毀容性的皮膚病,對患者的生活質量造成嚴重影響[1]。臨床實踐證實精神創傷、過度勞累、憂慮緊張等精神神經因素與白癜風的發病及病情加劇有著密切關系[2],且發病后容貌遭到破壞,導致日常生活質量下降,這又可作為新的應激因素進一步影響病情發展,因此慢性精神應激貫穿在從白癜風發病到病情發展的整個過程中[3]。但是目前精神、神經、內分泌因素與白癜風發病的相關研究仍是一個薄弱環節,國內外相關文獻報道還很少。本研究從應激生活事件與白癜風發病關系入手,調查白癜風患者發病前及病情復發前應激生活事件的發生情況,了解其與正常人相比是否存在差異,并對白癜風患者伴發的常見應激障礙(焦慮或抑郁)的發生率及嚴重程度進行評價,以期為今后進一步研究及治療干預提供線索。
資料和方法
臨床資料
研究對象分組 共調查180例,其中病例組60例,為門診確診的白癜風患者,正常對照組120例,為同期門診健康體檢者,經常規檢查(包括血、尿常規,肝腎功能,血糖,血脂,肝炎全套,腫瘤相關抗原等)未見異常者,并除外白癜風家族史和甲狀腺疾患既往史。調查對象均知情同意。剔除無效問卷后,共收到有效問卷173份,其中病例組55例,正常對照組118例。
一般資料 病例組男29例,女26例,平均年齡(40.98±15.87)歲,病程1個月~31年,其中進展期45例,穩定期10例;正常對照組男60例,女58例,平均年齡(40.56±12.59)歲。兩組性別、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方法
應激生活事件調查 采用1986年編制的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共含有48條我國較常見的生活事件,包括三方面的問題:一是家庭生活方面(28條),二是工作學習方面(13條),三是社交及其他方面(7條)。根據研究需要,不僅可以對總生活事件進行統計,也可按以上三個方面進行分類統計。根據事件發生的次數、持續時間、影響程度計算總分(即總評分值),總分越高反映個體承受的精神壓力越大。負性生活事件的分值越高對身心健康的影響越大。本研究中分別對生活事件的數量、總分、評分均值進行統計,生活事件評分均值=生活事件總分/生活事件數量。
焦慮及抑郁評定 焦慮評定采用漢密頓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14項版本,按評分值分為嚴重焦慮、明顯焦慮、有焦慮、可能焦慮和無焦慮5級,等級劃界分為29分、21分、14分、7分,總焦慮例數=嚴重焦慮例數+明顯焦慮例數+有焦慮例數。抑郁評定采用漢密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項版本,按評分值分為嚴重抑郁、輕中度抑郁、可能抑郁和無抑郁4級,等級劃界分為35分、20分、8分,總抑郁例數=嚴重抑郁例數+輕中度抑郁例數。總分能較好地反映病情嚴重程度,即癥狀越重、總分越高。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11.0統計分析軟件,計量資料采用±s表示,兩組獨立樣本比較采用成組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Fisher精確檢驗及Pearson′s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為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
結 果
生活事件發生數量 發病或復發前1年內,總生活事件及總負性生活事件數量、家庭方面總事件及負性事件數量、工作學習方面總事件及負性事件數量,病例組與正常對照組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僅社交和其他方面總事件及負性事件發生數量,病例組低于正常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生活事件評分 工作學習方面總事件及負性事件評分值,病例組高于正常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總生活事件與總負性生活事件評分均值、工作學習方面總事件與負性事件評分均值,病例組均高于正常對照組,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表1)。
表1 生活事件發生情況及評分Tab 1 Occurrence and score of life events (±s)

表1 生活事件發生情況及評分Tab 1 Occurrence and score of life events (±s)
P 0.396 0.744 0.324 0.181 0.001 0.001 0.473 0.670 0.959 0.894 0.099 0.147 0.884 0.396 0.048 0.014 0.001 0.001 0.049 0.038 0.528 0.628 0.633 0.864
焦慮發生情況及評分 病例組嚴重焦慮、明顯焦慮、有焦慮、可能焦慮及無焦慮分別為1例(1.82%)、1 例 (1.82%)、4 例 (7.27%)、22 例(40.00%)及27例(49.09%);正常對照組相應情況分別為0例、0例、1例(0.85%)、19例(16.10%)及98例(83.05%)。兩組各級焦慮發生例數及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11.85,P<0.05)。焦慮評分及總焦慮發生率比較,病例組均高于正常對照組,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表2)。
抑郁發生情況及評分 病例組嚴重抑郁、輕中度抑郁、可能抑郁及無抑郁分別為2例(3.64%)、2例(3.64%)、17例(30.91%)及34例(61.82%);正常對照組相應情況分別為0例、0例、14例(11.86%)及104例(88.14%),兩組各級抑郁發生例數及發生率比較,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F=9.25,P<0.01)。抑郁評分及總抑郁發生率比較,病例組均高于正常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2)。
表2 焦慮和抑郁發生情況與評分Tab 2 Occurrence and scor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

表2 焦慮和抑郁發生情況與評分Tab 2 Occurrence and scor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
Variable Case group(n=55)Control group(n=118)t orχ2 P 0.0010.007 0.0010.015
討 論
白癜風(vitiligo)是一種以局限性或泛發性皮膚色素脫失為臨床特征的特發性疾病,人群發病率約0.5%~1%,男女無明顯差異,一般在兒童期或青年時期即發病[4]。發病后雖然對患者的軀體健康和生理功能影響不大,但直接影響容貌外觀,對患者的生活、工作、學習以及社交造成許多負面影響,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5]。白癜風是典型的身心疾患,疾病的發生發展與精神神經因素密不可分。從胚胎發生學來看,皮膚與神經系統同源于外胚層,神經系統通過其豐富的感覺神經將環境刺激源產生的信號傳遞給中樞,再由中樞調控全身各系統產生應激反應來適應外界環境的變化。心理負擔或精神緊張影響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導致自主神經功能紊亂,可造成皮膚汗腺分泌、微血管舒縮功能障礙、皮膚和毛發的營養功能異常等,從而引起各種皮膚疾病;皮膚應激反應過程中分泌的細胞因子和皮膚自主神經產生的神經遞質和神經肽如果被激活,形成局部的應激反應系統,也可誘發皮膚病的發生。
不同的遺傳素質塑造了不同的身體素質,使具有不同身體素質的機體對相同刺激原的反應也存在著個體差異,精神神經因素也是一種應激原。應激是機體對內外環境中各種不同應激原作出的非特異性防御適應反應,適當的應激可增強機體對外界有害因素的抵御能力,但應激負荷過強或過于持久,也可導致機體生理機能紊亂,產生病理性應激,引發應激損傷或應激障礙,導致疾病的發生[6-7]。其中焦慮和抑郁就是常見的應激損傷所致的心理障礙和情感障礙[8-9]。
目前精神神經功能障礙的評價、精神神經疾患的診斷甚至療效判斷所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仍然是流行病學量表調查。LES有多個版本,被國內外相關專業研究者廣泛采用,既往研究對自評量表的信度、效度分析結果已經證實,事件影響量表與觀察者臨床診斷的應激障礙有良好的一致性[10]。LES屬自評量表,適用于16歲以上的正常人、神經癥、身心疾病、各種軀體疾病求助者以及自知力恢復的重性精神病求助者,主要應用于:(1)身心疾病、神經癥、各種軀體疾病及重性精神疾病的病因學研究;(2)指導心理治療、危機干預,使心理治療和醫療干預更有針對性;(3)甄別高危人群,預防精神疾病和身心疾病,對LES高者加強預防工作;(4指導正常人了解自己的精神負荷、維護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質量。
本研究通過調查白癜風患者應激生活事件發生情況,顯示發病前或復發前1年內白癜風組接受的應激生活事件數量及負性事件數量并不多于正常對照組,但某些類型的應激事件或負性事件的總評分值及評分均值,白癜風組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提示某些類型的應激事件刺激后,白癜風患者承受的精神壓力顯著高于正常人,更容易產生應激損傷,也提示在白癜風患者中,可能存在較高的應激損傷易感性,其即使接受相同數量的應激原刺激,發生的應激后損傷仍然會高于正常人,白癜風發病及復發可能就是應激后損傷在皮膚組織上的一種疾病表現形式。
由于白癜風應激生活事件調查的相關文獻報道還比較少,已有的少數幾個國外的相關研究得出的結論也各不相同,多數的研究結果顯示白癜風患者發病前接受的應激生活事件數量明顯多于對照組。有學者對21例兒童(≤14歲)白癜風患者進行應激生活事件調查,發現白癜風患者中發病前或病情加劇前1年內各種精神因素事件的數量比對照組明顯增加[11];Manolache等[12]對32例成年(≥15歲)白癜風患者進行的相關調查也顯示,在女性患者中應激事件的數量明顯多于對照組。但Picardi等[13]對31例成年白癜風患者(18~60歲)及116例對照者進行的調查卻顯示,與對照組相比,白癜風患者發病前或病情加劇前12個月內應激生活事件的數量并無顯著差異,這與我們本次的調查結果相似。但由于各研究納入病例數及調查對象的人口學特征各有不同,使用的量表也不盡相同,因此今后仍需加強這方面的研究,統一評價標準,得出的結論才更有說服力。Manolache等[11]同時對應激生活事件的種類進行調查,顯示這些精神事件主要來自三方面---家庭問題、個人問題、工作問題,例如家庭成員的死亡、懷孕、失業等;而在兒童精神因素與白癜風關系的研究中,發現精神事件主要來自學校、家庭、疾病以及精神創傷,與成人有所不同。此外,本研究中總生活事件或負性生活事件的評分,差異雖然無統計學意義,但白癜風組評分值有增高趨勢,如擴大樣本量,差異很可能就會出現統計學意義。
本研究中,白癜風患者焦慮和抑郁的評定分別采用HAMA14項和HAMD24項,這是精神科中最經典也是應用最廣泛的量表,用于評定神經癥及其他患者的焦慮癥狀或抑郁癥狀的嚴重程度和特點。結果顯示焦慮及抑郁的評分與發生率,白癜風患者均顯著高于正常人,提示在白癜風患者中伴發的常見應激障礙高于正常人,表明應激障礙與白癜風密切相關,這與目前國內外學者的意見相一致。路永紅等[14]研究白癜風患者焦慮、抑郁情緒與皮損的相關性發現:進展期白癜風患者焦慮、抑郁情緒的評分較穩定期高,皮損片數及皮損總面積增加,白癜風患者焦慮、抑郁情緒的評分增高,皮損在暴露部位的白癜風患者其焦慮、抑郁情緒的評分較非暴露部位者增高。正因為如此,有學者呼吁應該重視白癜風患者的社會心理障礙,將社會心理評價納入白癜風病情活動度評價以及療效評價體系中[15]。
由此可見,在應激生活事件刺激下,白癜風患者呈現異常的應激反應,引發的應激損傷顯著高于正常人,臨床上常見的應激障礙性疾患的發生率也更高,這就提示白癜風患者可能具有較高的應激損傷易感性,并在白癜風發病及病情復發中發揮作用。有學者推測在白癜風患者中是否存在著應激損傷的遺傳易感性[16]或易感基因,且可能在其他疾病影響因素共同存在時才能發揮作用。這些作用機制值得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
[1] Evers AW,Duller P,van de Kerkhof PC,et al.The Impact of chronic skin disease on daily life (ISDL):ageneric and dermatology-specific health instrument[J].Br J Dermatol,2008,158(1):101-108.
[2] Osman AM, Elkordufani Y, Abdullah MA.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vitiligo in adult Sudanese patients[J].Afr J Psychiatry,2009,12(4):284-286.
[3] Christian K,Jim WS,Jennifer DS,et al.Significant immediate and long-term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life and disease coping in patients with vitiligo after group climatotherapy at the Dead Sea[J].Acta Derm Venereol,2011,91(2):152-159.
[4] Willemsen R,Roseeuw D,Vanderlinden J.Alexithymia and dermatology:the state of the art[J].Int J Dermatol,2008,47(9):903-910.
[5] Eleftheriadou V,Whitton ME,Gawkrodger DJ,et al.Future research into the treatment of vitiligo:where should our priorities lie?Results of the vitiligo priority setting partnership[J].Br J Dermatol,2011,164(3):530-536.
[6] Choi DC,Evanson NK,Furay AR,et al.The anteroventral bed nucleus of the stria terminalis differentially regulates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ocortical axis responses to acute and chronic stress[J].Endocrinology,2008,149(2):818-826.
[7] 尚蕾,王擇青.創傷后的應激障礙及其預測因素[J].中國臨床康復,2005,9(16):128.
[8] Zoellner LA,Rothbaum BO,Feeny NC .PTSD not an anxiety disorder?DSM committee proposal turns back the hands of time[J].Depress Anxiety,2011,28(10):853-856.
[9] 陳美英,張仁川.突發災害事件的心理應激與危機干預[J].臨床和實驗醫學雜志,2006,5(12):1960-1961.
[10] Aghaei S,Sodaifi M,Jafari P,et al.DLQI scores in vitiligo: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Persian version[J].BMC Dermatol,2004,4:8.
[11] Manolache L,Benea V.Stress in patientswith alopecia areata and vitiligo[J].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2007,21(7):921-928.
[12] Manolache L,Petrescuseceleanu D,Benea V.Correlation of stressful eventswith onset of vitiligo in children[J].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2009,23(2):187-188.
[13] Picardi A,Pasquini P,Cattaruzza MS,et al.Stressful life events,social support,attachment security and alexithymia in vitiligo.A case-control study [J].Psychother Psychosom,2003,72(3):150-158.
[14] 路永紅,蘇曉杰,向丹黎,等.白癜風患者焦慮、抑郁情緒與皮損的相關性[J].中華皮膚科雜志,2008,41(1):49-50.
[15] Kostopoulou P,Jouary T,Quintard B,et al.Objective vs.subjective factors in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vitiligo:the experience from a French referral centre[J].Br J Dermatol,2009,161(1):128-133.
[16] Raymond EB,Richard AS.Frontier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pathobiology of vitiligo:separating the wheat from the chaff[J].Exp Dermatol,2009,18(7):583-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