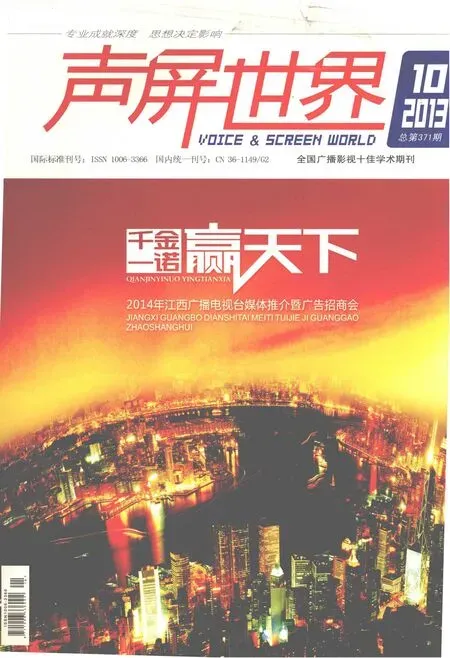紀錄片與地域文化的關聯
□ 閆偉娜 劉 青
紀錄片與地域文化的關聯
□ 閆偉娜 劉 青
紀錄片具有很強的社會認知價值、歷史文獻價值、文化傳承價值和藝術欣賞價值,是一個國家和地區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要一環。“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好比一個家庭沒有相冊”,而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也顯現出與地域文化、經濟和社會之間的緊密關聯,在一定區域,紀錄片通常呈現出比較鮮明的創作特色和共同傾向。作為歷史和時代的見證者,紀錄片無法脫離博大精深的文化傳統,更無法規避在現實生活中沉淀已久的地域文化,尤其作為觀念意識形態呈現的認識模式。
地域文化與紀錄片創作
地域文化,也可以稱為區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區域源遠流長、獨具特色,傳承至今仍發揮作用的文化傳統,“是在人類的聚落中產生和發展的,以世代積淀的集體意識為內核,形成一種網絡狀的文化形態、風俗、民情、宗教、神話、方言,包括自然生態和種族沿革等等,組成一個相互關聯的有機的系統。”①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與環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獨特性。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一方人就會產生具有一方特色的文化。作為歷史的立體檔案與現實的文獻筆記,紀錄片因其記錄內容的迥異,以及創作者和創作對象所處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社會環境的差異,因循承續著不同的品性、觀念和習俗,而呈現出與地域文化相關聯的影像風格。首先,地域性的自然風貌與地理環境,構成了紀錄片創作的重要內容和記錄對象。無論何種藝術形式,恐怕都很難完全將自然生態和環境徹底排斥于創作敘事之外。相反,山川河流、動物植物、天文地理等內容,構成了自然紀錄片最重要的敘述對象與內容。其次,地域文化為紀錄片中的人物性格和價值觀念的形成提供可信的文化基因,并在此基礎上完成一種社會性格或地域性格的凸現,成為一種人文精神的補充。紀錄片《沙與海》中,生活在內蒙與寧夏交界處沙漠邊緣的牧民劉澤遠和生活在遼東半島孤島上的漁民劉丕成的人物性格和價值觀念有較大區別,這些都是地域文化的烙印。第三,地域文化為紀錄片創作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思想動力和文化智慧。藝術創作離不開生活,更離不開地域生活,因為地域生活具有最為鮮活的生命活力。不同地域的生產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形成了特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也使得紀錄片作品具有一種獨特性。最后,地域文化對創作者的創作方式有潛在的制約作用。地域文化所形成的特殊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已經構成了他們藝術創造思維模態的基礎乃至基本的思維方式,并融入其一貫的紀錄片作品之中。盡管這種遺傳性的文化基因的影響程度不盡相同,但或多或少都會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制約作用。
紀錄片影像中地域文化的價值體現
紀錄片作為一種藝術存在,首先是一種影視藝術,是對地域風土人情的聲畫視聽書寫,這是作為媒介價值存在的;其次是一種民族文化,是對地域文化的記錄與傳承,這是作為文化價值存在的;同時還是一種審美話語,是不同地域人民審美意識的綜合反映,這是作為審美價值存在的。
一、作為影視藝術的素材:對地域風土人情的聲畫視聽書寫。紀錄片是特定的文化環境中的產物,通過對環境和人物的記錄、重構和表達,達到表現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現狀的目的。紀錄片創作有三個環節:選題、拍攝和制作,在這三個環節中最核心的就是題材的選擇,選題的巧妙與否直接影響一部紀錄片的成功與否。而無論是歷史文化類紀錄片還是自然生態類紀錄片,抑或是人文社會類紀錄片,地域風土人情都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素材。例如,西南少數民族紀錄片大多以民族風情為主,主要包括獨特的異域奇觀、少數民族的物質活動和少數民族的精神活動。這些都是我國少數民族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淀和發展演變而形成的最能反映少數民族的性格氣質、文化內核、精神品格、心理結構的特征,是少數民族獨特性的基本要素。②從紀錄片創作的角度來說,這些關乎特殊地域生產、生活、物質、精神的方方面面又構成絕好的創作題材。
二、作為一種文化表征:對地域文化的記錄與傳承。地域風土人情為紀錄片提供創作素材的同時,紀錄片的記錄也為地域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提供了一條可靠途徑。一部 《舌尖上的中國》將中華美食文化和東方生活價值觀記錄呈現,在獲得市場認可的同時也傳承了中國地域文化。在記錄與傳承的同時,紀錄片也促使人們深入思考傳統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發展與走向。《遠山的瑤歌》是一部以少數民族風俗文化為主題的紀錄片,它以客觀的視角展現現代主流文化與古老的地域文化的碰撞、滲透以及有機交融的過程。通過紀錄片,我們看到了一個古老地域文化的縮影,感到了老一代對將要消失的文化傳統的依戀與無奈,又通過文化的傳承滲透,使人們看到了希望,促使社會關注地域文化。③
三、作為一種審美話語:對不同地域人民審美意識的綜合反映。處于不同地域文化熏陶下的群體對個體存在、日常生活、自然生態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感悟和理解,這種感悟和理解使人們“詩意”地棲居在地域文化的熱土上,他們的生活狀態和審美認知都遵循這種內在的地域文化心理。紀錄片《藏北人家》講述了藏北牧民措達一家人平靜而又和諧的日常生活。作品呈現出的生活是一種從容與寧靜,飲食起居、祭神舞蹈,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諧自然。影片中人物的精神生活同樣簡單自然。措達不識字,沒有去過外面的世界,但是他認為自己很快樂,他會在放羊時哼唱小曲敲打石頭,他與妻子之前并沒有感情基礎,但二人相互依靠,默契配合,為家庭努力。整個紀錄片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簡單到極致的自然之美、生活之美、人性之美和文化之美。這種智慧、虔誠與知足的生活狀態實際上是藏族人民審美心理的一種折射,是他們審美意識的一種綜合反映。
地域文化視域下的紀錄片影像創新思考
地域文化既是紀錄片風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時,也可能在影像風格成熟后的開拓性發展中形成制約。如何利用地域文化特色發揮紀錄片的地域優勢,如何在發展中不斷超越地域文化對紀錄片發展的制約,是地域文化視域下紀錄片創新發展的關鍵。
首先,“獵奇”有度,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資源。歷經20世紀90年代的輝煌之后,我國的紀錄片創作和播映進入了低靡狀態,很多精品紀錄片欄目因為收視率等原因停播。于是,一些紀錄片的創作者就把目光投向了邊緣人物和題材,一些少數民族的奇風異俗就成了紀錄片的“賣點”和“看點”,如果表現不當,不能用人類學、文化學的視角來關注它,就會使紀錄片陷入過度“獵奇”的誤區。例如,西南摩梭族至今還保存著阿夏走婚制度:男不婚,女不嫁。這種風俗對于現代婚姻制度而言確實是古老而新奇的,如果紀錄片的創作單純關注這一奇風異俗,以滿足觀眾的窺探欲和好奇心為目的,而并沒有引導觀眾深層領悟其文化歷史和內涵,這就是紀錄片創作中的過度“獵奇”,這種做法會扭曲地域文化的本來面貌。要注重其文化內涵的深入挖掘和表現,著力探討表象背后的文化成因和文化傳承,這樣的作品才能具有歷史文化的深度與厚度。
其次,“坐標”意識,打造地域“類型化”紀錄片。紀錄片在表層是一種聲畫體系,在深層則是一種意義系統。這種意義系統,一方面是創作者個人意圖的傳達和一種文化選擇,另一方面是由觀眾的讀解來完成的。而這兩方面要素都與地域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地理的完整性和歷史發展的延續性使得地域文化如同基因一般植入特定地區人們的思想,創作者的選題、攝制和剪輯都深受傳統地域文化的影響,而本土受眾也因紀錄片負載著傳統文化的因子,進而與之形成良好互動。可見地域文化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是十分巨大的。基于此,在題材風格多樣化的前提下,可以鼓勵打造地域“類型化”紀錄片。紀錄片類型化是指在一定程度上紀錄片的量化生產,它為紀錄片的商業化操作提供了可能,并且可以有效解決節目特征模糊和同質化等問題。
第三,“多元”思維,尊重地域文化的同時兼顧文化多樣性。從當前的紀錄片創作來看,紀錄片的發展必須建立在本土資源的基礎上,包括自然風光、人文歷史、政治資源、社會變遷,受眾資源等,它賦予紀錄片不可替代的獨特的核心價值。但是尊重地域文化并不是片面的地方保護,強調地域文化也并不意味著排斥其他地域的文化傳統,而是針對一些紀錄片“同質化”“無文化”的現象提出的。在進行紀錄片創作時,我們不僅要尊重地域文化,挖掘創作富有地方特色的紀錄片,更要觀照不同地域文化的差異性與多樣性,注重文化交流。特別是在對外交流的過程中,要選擇既具有本土性又可為全世界所理解的題材內容,在保持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時兼顧與世界文化的溝通融合,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紀錄片走出國門的同時又能發揚中華文化。
[本文系山東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 “新媒體語境下山東省紀錄片產業發展策略研究”(項目編號:2012RKB0 1133)的階段性成果]
欄目責編:胡江銀
注釋:①田中陽:《論區域文化對當代小說藝術個性形成的影響》,《中國文學研究》,1993(3)。
②胡 釘:《中國少數民族紀錄片研究》,廣西民族大學,2012年版,第34-35頁。
③金震茅:《地域文化在紀錄片中的體現》,《視聽界》,2011(2)。
濟南大學 山東輕工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