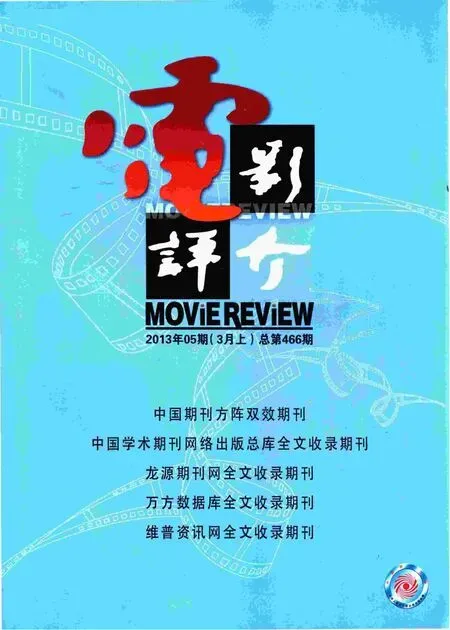創新與保守——評新版《安娜·卡列尼娜》
一、創新:舞臺劇轉場
本片在拍攝手法上給觀者帶來一種置身于舞臺劇的絢麗幻覺之中,美工、布景、音樂、服飾均帶有舞臺劇略顯夸張的形式美感。比如開篇用舞蹈式的動作來表現安娜閱讀哥哥的來信這種很生活化的動作,意在表達一種沙俄時代貴族詩意般的優雅。安娜的哥哥在辦公時一個很普通的蓋章動作都被演員形體的夸張動作表現的充滿戲劇感,這種表現手法給觀眾帶來的是新穎的視聽感受。然而本片最值得注意的是舞臺劇式的轉場,這種劇目的形式加快了影片情節的推進速度,將一部700多頁的長篇小說壓縮為僅有130分鐘的影片之中。前一幕是風雪交加的火車站,下一幕就到了廣博的西伯利亞草原,這種拍攝手法節省了影片的經費,省略了冗長的過渡情節,將影片剪切成一幕幕的舞臺劇片段,正如導演喬懷特認為的那樣,譬如乘馬車去戲院這樣的情節對表現影片內容和主題毫無意義,但是卻花費不少的經費。同時舞臺劇轉場也使得影片在過渡上顯得亦真亦幻,營造出一種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夢幻感。影片在聲音的細節處理上也表現出舞臺劇的精致美感,片頭火車站的竊竊私語似乎在暗示安娜悲劇愛情中遭遇的社會輿論壓力,為故事的開篇就蒙上壓抑的陰影。安娜在與沃倫斯基的戀情暴露后參加上流社會的舞會,舞會中的音樂聲被貴婦人手中的折扇快速的扇風聲取代,烘托出一種心理上的緊張感。
然而舞臺劇形式的運用也是一把雙刃劍,雖然舞臺劇與電影的“混合搭配”給觀眾產生新奇的形式美感,帶有強烈的實驗性。但是《安娜·卡列尼娜》作為一部現實主義巨作,情節內容和人物才是關鍵。將這種方式運用到歷史感沉重的現實主義小說上,容易讓觀眾產生疏離感,無法投入到復雜而深刻的人物情感世界,淡化了思考的余地。我們只能將這種手法看做是形式超越內容的創新,是一種向傳統敘事形式的強烈挑戰。
二、人物塑造:“英式”的俄國貴族
本片在人物塑造上帶有強烈的英倫風范,無論是演員的表演風格還是導演對原著思想的解讀都在一定程度上帶有英國式的保守和矯飾。在人物塑造上,沃倫斯基傾斜十五度的帽檐和貴族式的八字髭讓人感覺到導演急于再現和還原19世紀俄國貴族的華麗衣飾,而在人物性格塑造上明顯著力不足。卡列寧在本片中被塑造成典型的英國紳士,面對妻子的出軌,隱忍和克制的情緒伴著骨節間吱吱作響聲為觀眾帶來的是英國人表達情感時的壓抑和適可而止。對比在傳統的文學教材和評論中,卡列寧被認為是俄國專制制度的衛道士,激進的女權主義甚至將其看做是壓迫女性自由權力的儈子手。但是從列夫托爾斯泰的原著來看,作者本人對卡列寧也是復雜而非單向批判的,我們很難用好人壞人這種簡單的標度來評判他筆下復雜的人物形象。毫無疑問,卡列寧的性格里是存在虛偽的一面的,這體現在面對安娜出軌時,他認為“不能因為一個下賤的女人犯了罪的緣故使自己不幸”,迫于身份和保守社會環境的壓力,不敢與安娜離婚。但在安娜產熱即將瀕死時,面對昏迷中依舊呼喊自己的妻子,卡列寧希望她早些死去的想法被心中的善意融化了,原諒了沃倫斯基和安娜的背叛。列夫托爾斯泰希望展現的是人性的復雜和多變,如果說傳統的解讀方式將卡列寧惡向放大,那么新版的安娜卡列尼娜在這個關鍵人物的性格塑造上則是主觀性的幻想,將卡列寧塑造為寬容隱忍,篤信宗教,解救道德墮落妻子的圣人,這種對原著的改變是英國式的“誤讀”和創作班底的主觀再創造。
三、保守:主題思想局限
《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用這樣的方式來描述人類的愛情:“比喻是危險的,愛情源自于一個比喻。”這是因為比喻是感性的開始,理性的滅亡。愛情作為人類情感的表現方式,長期以來都是文藝創作的重要主題。我們可以將安娜的愛情看作是“為愛情而愛情”,這種基于人類靈魂深處的激情和超越階級利益關系的情感能否用對錯這種簡單的判斷標準來衡量是值得人們思考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依托于愛情的故事,對其解讀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然而影片既沒有從時代背景和人物性格上做出深刻的探討也沒有從人性的變化著眼,而把思想重點落在道德的反省和教化之上。《安娜·卡列尼娜》寫于1873年,4年之后小說首版發行,19世紀60年代俄國的社會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裂變,自1861年亞力山大二世廢除了農奴制度,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資產階級倡導的自由思想開始侵襲古老而保守的莊園經濟,《安娜·卡列尼娜》正是寫于這樣一個復雜而變革巨大的時代背景之下,作者復雜的世界觀演化出復雜深刻的人物性格。傳統的階級解讀方式將安娜看作是深受舊制度壓迫的女性,這種社會學的解讀方式也不失是一種看法。然而列夫托爾斯泰似乎是在通過婚姻和愛情故事尋求對人性更深刻的解讀。在影片中,安娜被簡單的塑造成追求激情,背叛婚姻的可悲女人,其價值意義只在于警示列文傳統選擇的正確性和哥哥布朗斯基公爵雨夜下對不忠的沉思和靜默。安娜性格中的反叛和抗爭被削弱,而被導演主觀性的詮釋為一個庸常的道德反例。一部電影的立意與導演和劇組制作團隊的意識是無法分離的,喬懷特和他的英倫班底用英國式的保守主義詮釋了俄羅斯人骨子里的熱血和激情。新版的《安娜·卡列尼娜》并沒有再現出這位文學巨匠復雜的思想世界。
影片結尾處,在和煦的陽光下圣人一般的卡列寧帶著慈愛的微笑看著安娜的孩子在花海中嬉戲,畫面在意境色調上大有印象派的美感,再次表現了導演對中產階級保守家庭觀念的憧憬和贊美,我們并不能說這種價值觀是錯誤的,只是用它來解讀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未免顯得有點單薄和無味。
[1]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海譯文出版社[M].草嬰.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