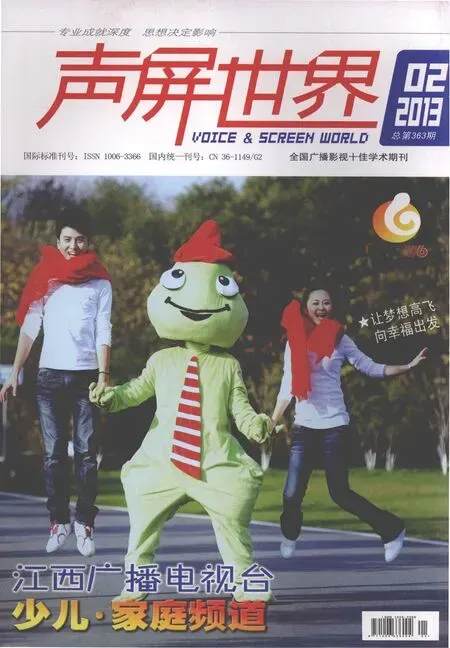影視是解讀文學后的集體創造
□禾 刀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改編自劉震云的小說作品,李安導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改編自加拿大作家揚·馬特爾的同名小說,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也曾經為中國電影奉獻過優秀的文學劇本……這段時間的幾個重大文化事件,似乎都在闡明文學對于影視的重要性。文學真就是影視作品的靈魂嗎?
老實說,這個問題的答案很難一概而論。優秀作品改編成優秀影視作品的有之,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四大名著電視劇。不成功的例子更是枚不勝數,比如近年來被改編成電視劇的四大名著頻遭觀眾 “吐槽”。若要深究文學與影視間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怎么看都像是雞生蛋,蛋孵雞的關系。二者鼎力互助,往往能產生強大合力。記得英國導演史蒂芬·戴德利就曾坦言:“在電影方面我會和寫劇本的人走得非常近,有很多接觸。”也記得馮小剛曾談到《集結號》時自曝,原有意用一個藝術性的結尾,即幸存的谷子地歷經千辛萬苦最終沒能找到真相。但此舉遭到編劇的極力反對,認為觀眾喜歡看一個大團圓的結局,而不愿花錢背上一個包袱。這也許還可以成為《一九四二》叫好但不叫座的原因。
一百多年前,世界上第一部電影的出現,引得公眾無比震驚。電影最終脫胎新奇玩藝,被挑剔的藝術陣營所接納,是因為這種表達方法,成功開創了連貫性的光影藝術表現手段,突出了肢體語言的表達底蘊,特別是有效結合環境等諸多要素。也所以,越是有個性的電影導演,越會挑剔電影色調,像張藝謀的《紅高粱》執著于一種極致發泄的鮮紅,陳凱歌《霸王別姬》的灰暗傳遞出一種由視覺扭曲而抵至心靈深處的痛感,王家衛的《藍霉之夜》則在幽暗中透出一種朦朧的溫馨……很顯然,無論是光影的把握,還是現場肢體語言的表達,這往往是劇本或者文學不足以展現的內容。事實上,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要變成優秀的影視作品,期間至少需要經歷兩次高水準地再創造,一次是將文學作品改編成優秀的劇本,另一次是導演將優秀劇本成功 “翻譯”成高質量的光影藝術作品。從這層意義上講,一部優秀影視作品是文學作者、劇本改編者、導演包括演員在內所有人的共同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