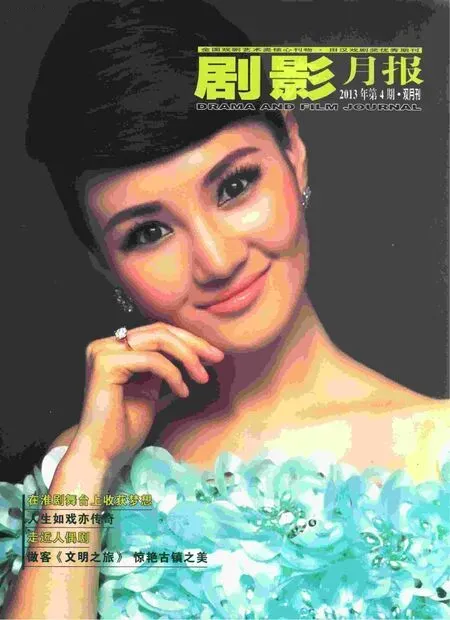猶看春閨夢里人——舞蹈《春閨夢》淺析
■陳東
花旦,是中國戲曲旦行中的一支,扮演的多為天真爛漫,性格開朗的妙齡女子。而舞蹈《春閨夢》就是提取了如今我們所見的戲曲人物中的角色——花旦中的 “閨門旦”來創作,將戲曲中的身、法、手、眼及下身的走步與流動結合于舞蹈的本體中,成為了舞蹈界的一個新的點睛之作。一身青衣,頭飾珠翠并加上一根長長的辮子,背立而向,定點的造型之下,只可從單薄的背影中透過其側臉可看出這是一個嬌小的女子。隨著戲曲音樂的響起,蘭花指的纖長俏麗配以手臂動作的柔潤伶俐,女子轉身而退,細碎的花梆步以一個S形,迂回于舞臺之中,如同躍然紙上的書法一樣游刃有余。拂面撩窗的探頭,雙手小心翼翼地在胸前鼓掌,腳下步伐的小小抬起落下,無一不能看出這是一個活潑開朗而又天真可愛的少女。戛然而止的音樂后一個旦角出場的咿呀之音,定點而立,細碎的小晃頭加上甜潤的微笑,頓時讓人聯想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詩句,旦角的形象一下樹立起來。舒緩輕快的曲調插入,女孩向前探身而行,左右的張望,雙手在胸前不斷地揉捏,單腳在腿上來回的摩擦,看出了她心中的焦躁和不安,想去上前看個究竟,但卻又止步于繁縟禮節的束縛只能在原地徘徊之中。隨后的嘟嘴,跺腳轉身,一個少女的撒嬌之態通過一個極其簡單易見的動作展現出來。不斷地向自己的好奇之處去試探,以退為進,探頭轉身的張望,雙眼瞪大眼中充滿著好奇,使一個從不出門對外面世界充滿好奇的少女形象通過眼神、探頭、表情及來回徘徊的步伐,四點相融合,清晰流露。雙手掩面遮擋,頭從手后悄悄地探出,頷首收回,手捂嘴而扭頭;背對而立,雙手在身后來回的絞動。讓我們看到了少女的懷春姿態,對愛情的向往,含羞時的不好意思,猶豫不決的徘徊。
動作雖細碎,但卻豐富且耐人尋味。整個舞蹈調度雖沒有那么豐富,但卻清晰可見,很明確。剛開始時一連串S形的花梆步,緊接定點造型;其次動作的設置一直在朝向一個方向,一條斜線的前后調度迂回,表現女孩被那邊所吸引;進入快板音樂后,同樣也將演員設置于舞臺的斜角區域,斜線的迂回和橫線的延展并且反復出現在舞臺前方斜角定點舞蹈的設置,可見編導的匠心獨運之處。雖然只有簡單的調度,但卻能讓觀眾從這巧妙的舞臺調度的流動中看到編導所要傳遞出的蘊含之義,為整個舞蹈錦上添花。再者,配以編導巧妙的結構安排,使舞蹈又升華一步。第一段,為少女懷著對世界的無限憧憬邁出家門,對外面世界的處處驚奇和好奇;第二段,是少女的思春之態,在遇見心上人時的嬌媚;第三段,強化人物的形象特征,及內心的各種緊張與焦躁,并在最高潮之處選擇戛然而止的收尾。步步扣題,層層嵌套,在最高點的時刻選擇收尾,獨特而又新奇,并且能給觀者留下一種意猶未盡之感,在結束后還能夠讓人沉醉其中。
在對旦角這一形象上抓住自身特點,留下經典的元素:晃頭。與古典舞結合一體,對“閨閣旦”這一形象的塑造,體現了少女的天真爛漫與活潑開朗。同為取材戲曲的旦角,與早期作品《俏花旦》有異曲同工之巧,也有大相徑庭之妙。《俏花旦》選取的是戲曲之中花旦的形象,為青年或中年女性的形象,性格活潑或潑辣放蕩,常常帶點喜劇色彩。同時花旦也是一道清新亮麗的風景,旦角們常常穿著艷麗的戲服,畫上濃烈的油彩,頭戴華貴的頭飾,顧盼神飛,在舉手投足間散發出無限活力。 融會川劇的音樂風格,用舞蹈的現代創編手法以及舞蹈的古典身段等肢體語言,在道具的設置上,更是獨具匠心。在花旦的頭頂上別上了一個野雞翎子,隨著花旦們的細碎走步和戲曲晃頭的動作,野雞翎子不斷地顫動形成一個空中的波紋,給人一種空間的審美之感。同時這個道具也展現出了花旦角色的乖巧伶俐,幽默風趣。一個是運用特殊的道具加上晃頭展現成年女性的嬌媚乖巧,一個是一身青衣融合晃頭體現少女的可愛活潑;以群舞和獨舞兩個不同的形式表現,不論是花旦還是閨門旦都由編導的獨特創思和編排手法巧妙地各自展現了自己的獨特之風,令觀者眼前一亮,也成為了舞蹈界新的亮麗風景。
舞蹈《春閨夢》雖取名與戲曲中的《春閨夢》一樣,但風格卻完全不一樣。“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京劇中尤為出名的《春閨夢》是根據唐代詩人杜甫《新婚別》及陳陶《隴西行》中的詩句而改編的。在故事中:“壯士王恢新婚不滿數月,被強征入伍,陣前中箭而死。妻子張氏,終日在家佇盼,不覺積思成夢。夢見王恢解甲歸來,張氏又是歡忻,又是哀怨。倏忽間戰鼓驚天,亂兵雜沓,盡都是一些血肉骷髏,嚇得張氏驀地驚醒,才知都是夢境。”整個戲曲的基調都處于悲涼、凄慘的氛圍中,對亡夫的死難以接受、逃避血淋淋的事實真相,并同時對其懷有終日的思念之情,最終抑郁寡歡無疾而終。而與其完全不一樣的古典舞的《春閨夢》,氛圍卻截然相反。古典舞中的少女正值青春年華,她可以肆意的笑;可以倔強的哭;可以賭氣撒嬌;可以年少輕狂;可以我行我素;并沒有戲曲之中的少年傷感,懷春遺夢,所留下的傷感和留戀。全新的釋義:猶看春閨夢里人。多了分青春活力的朝氣,少了些悲傷懷春的難過和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