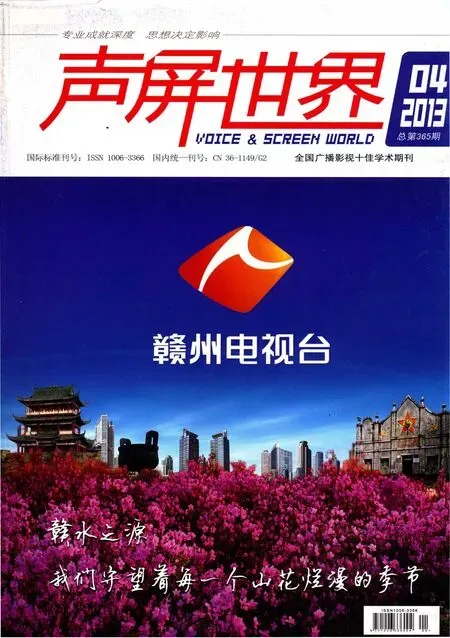醫療題材電視劇的審美缺失與期待
□黃媛媛
醫療衛生事業被稱作國家的第二國防。書寫這個行業,需要在醫學話語、政治話語、藝術話語、倫理話語等眾多話語體系的交錯融匯中,繪制出一個復雜的“話語光譜”。醫療題材電視劇置身其中,沒有釋放出相應的光彩和能量,甚至于在中國電視劇的恢弘成就中黯然失語。本文評議它的種種失范之處,期冀它能以一個成熟的姿態面對這份凝重的書寫,并找到自己的獨特波長。
生命拯救母題的豐富演繹與商業捆綁
醫療活動面對的是生命的脆弱,醫療過程中遍布著生與死的命運擺渡。因此評審醫療題材電視劇,我們要從醫療片段里找出這種文化表述被運用的動機,找出這段生命救治歷程中有靈魂的勾勒。遺憾的是,一部分創作者在凝視生命難以承受之重時,總有部分劇集步履輕飄,語義曖昧。
在社會的職業化和保障體系高度發展的美國,醫療劇是其電視劇品類中一個成熟的類型。上世紀90年代初,由《急診室的故事》建立起來的“‘Professional(專業)+Personal(人性)’的‘P+P’模式,成為美國醫療劇最重要的兩大特點。”①在“專業性”一端,多數美劇征用病人的生死節點,意在以此創造的戲劇波峰中用精湛醫術的蒞臨化險為夷,進而回應美國強大的技術基礎和虔誠的科技崇拜。如在美劇《豪斯醫生》中,怪醫豪斯憑借超凡的推理能力將病癥診治轉化為偵探劇框架內的埋線、解扣過程,在劇中生命臨界點只充當了美國式英雄行動開啟的觸發器。在“人性化”一端,美式醫療劇忠實履行了西方哲學精神中的人性啟蒙和倫理探尋,每次生死存亡的內核都包含著人倫劫難。然而,美劇的表達慣性是每一集完成一個故事,那么生命遭遇的陡峭因其出現頻率的增加而導致了含金量貶值,生命不再是一個艱辛的體驗過程,而被斷層為一個個充滿奇遇的片段。
在不同的土壤中孕育、生長,我國醫療劇雖然沒有過多地用奇觀來裝點自己,但也因在戲劇尺度上拿捏不準而難于打撈關于生命的厚重的意義。部分醫療劇一方面明確了創作上的現實性旨歸,竭力鋪展著逼真的醫療現場,另一方面又缺乏用平實的醫療過程啟示觀眾的創作自信。在《柳葉刀》中,顧明道醫生查明醫院貪腐黑幕的過程一直攀附在一宗離奇的命案之上。于是,彌漫在生命之上的案情進展成為故事引擎,經歷層層迷霧,與顧明道處于競爭關系的好友李肖一醫生排除嫌疑,徇私枉法的院長最終現形。雖然這是一部有風格、有節奏的電視劇,但是這種案情綁架病情,病情推動案情的展示路徑,稀釋了面對生命的真誠。
另一種逾越病情的癥候表現為難以掙脫來自收視的“影響力焦慮”,將醫療領域軟化為私密的個人生活,盤旋在婚姻、情感的狹小空間中,靠咀嚼、反芻情感的小悲歡賺取生活情味。港劇《妙手仁心》系列沉溺在三角戀、四角戀、五角戀的滔滔喋喋中,擊潰了醫療活動的精神崇高性。電視劇《心術》將醫院分解為勾兌愛情和執行醫療兩個空間。愛情線憑借男醫生和女護士曲折的、完整的戀情升溫過程,力壓醫療線上片段性的、零散的事件組合。后半部分醫療線更是嚴重褪色,情感線愈演愈濃,最終承受著人體病痛和體制病癥的體魄被整形為含情脈脈的身姿。這種庸俗化的編創路數讓人不得不懷疑,離開了愛情的華麗拐杖醫療劇還能不能獨立行走?
醫生形象的道德使命感與現代性匱乏
道德之思是醫療劇中不可回避的話題,又在醫生這個“救助者”形象的原型屬性下進一步發酵,成為醫生的最終歸屬。早在1985年亮相的醫療劇《希波克拉底誓言》就將批判的指針指向了道德層面。該劇深刻揭示了名利對醫德的傾軋和腐蝕,進而在當時的社會寫作愿景中“表達對人類前景的焦躁預測”。②之后的近30年中,道德化的醫生一直是醫療劇的精神著陸點。讓觀眾在杰作中遇見美麗的心靈,是編導者的創作理想。但若是青睞過度,將道德模式化、塑像化甚至神化,則會導致對道德的消磨。
在引發日本收視狂潮的《白色巨塔》中,醫術精妙的財前為獲得并保住教授的聲譽,變成了病人的冷面“殺手”,最終自己也成為癌癥患者,精神和身體都走向了醫生的悖反。該劇人物傾向上顯露出明顯的二元對立思維,財前完全被名利驅使,里見醫生絕對善良,東教授眼中只有嫉妒。這些單維度的人物性格使堅硬的倫理骨骼失去了溫熱的血肉,批判變得機械。
在塑造道德圣賢時,創作者習慣于一種情緒化的寫作方式,將高尚的道德、堅定的信念以及為全人類提供安頓之所的偉大信仰,氣貫長虹地注入醫生的神經系統中,醫生被放大為救世主,跳脫了人性棲居的地面。電視劇《感動生命》中就有這樣一些失當的設置:實習醫生任丘的發小急需手術費,善良的關珊醫生為了幫助他們就把自己的車以30萬的價格賣掉,籌得了費用;鞏凡醫生的校友登山時受重傷住進醫院,鞏凡懷疑他們可能有意犧牲了另一個隨行者,便到事發現場勘察找到了他們的犯罪證據;鞏凡不但要醫好小病號陳佳子身體的病,還要醫好她心里的傷,她多次探訪陳佳子離異的父母,甚至不顧佳子的父親已有了新感情,成功說服了兩人為了孩子復婚。這些行為雖然意在將醫道升華為人道,但已經明顯逾越了醫生的職業經緯。道德人格的有效書寫應該是厚而不偽、險而不妖的,“一旦過于強調介入,而忽略了如何介入,就面臨著介入性滯漲帶來的藝術本身的衰變。”③
如果說道德倫理是古而有之的,那么現代性就應該是指向當下的。相比技術和器械的現代化成分,醫療劇中醫生形象的現代性是明顯延滯的。例如,電視劇《感動生命》中任丘醫生的發小狗剩為給任丘娘湊錢治病偷了工地的材料,并在偷盜過程中受傷,不但關珊醫生賣車幫他們湊齊了手術費,而且因為狗剩在關珊父親公司打工這層關系,公司對他不予追究,且由關珊出面給他在公司重新安排了工作。醫生實施善行卻模糊了是非標準,并且默認的是腐朽的熟人文化,這完全拉低了現代社會中醫生的精英人格。
對醫患、醫改等深層矛盾的熱情展示與淺層回應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醫療事業在現代化進程中經歷著技術革新,更暴露出前所未有的亂象。各種醫患矛盾借助媒體、網絡迅速蔓延,又被不斷添加、化合了各種社會積怨,使追求健康這項人的基本權利變得無比艱辛。更加痛心的是,千瘡百孔的現實問題終究沒有治服影視創作的從容,醫療劇雖然意識到這是個沉重的問題,多數劇集卻仍用浮想聯翩的方式抵消對醫療現實的考量,難以形成對醫療困境真心實意的敲打和救贖。
部分電視劇在醫療困境的外圍抒發著田園牧歌式的暢想,劇中人只是扮上了醫生的妝容,占用了醫生的活動場所,以醫患矛盾為由頭自語著恩怨情仇的故事。電視劇《生死依托》將目光對準問題最嚴重、最復雜的農村醫療改革進程,卻將改革承受的磨難歸結為小農意識作祟,即沒落的價值觀阻礙了新醫改的破冰之旅。并且,農村醫改這一敘事支脈一直附屬在被知青父親遺棄、醫學院畢業后回到農村的山丹,與身為市醫院院長的王天明父女相認的線索上。可以說,這類故事堆砌的是醫療現場的 “偽真實”,其背后潛隱著的是創作者現實意識的貧瘠。
部分作品在醫療矛盾的表層做著浮光掠影式的停留,對行業創傷只熱衷于表述、渲染、注釋,而淡于展開意義追問。電視劇《心術》探討了一些問題:如醫生應該立即給重傷者手術還是等待家屬的簽字,醫生是否該為手術中的意外負責等等。但是劇中對矛盾的辨析要么停留在醫生為病人捐款建立的美麗桃花源、迷人烏托邦中,要么僅在會議講話中作講演式的主題拔高,要么將沖突化解在沒事找樂的主體調適中。更多的時候,醫患關系只在醫生的閑談中展開,討論得出的精神格言沒有納入敘事鏈條中,更不會成為人物自我認識的關節點,最終這些語言的漣漪只能被認定為創作的未完成形態。這其中的深層原因是創作者對醫患矛盾缺乏最本質的認識、痛徹心骨的反思,草率地決定了電視劇的藝術立場。
極少數作品直擊醫療行業的生存狀態,曝露腐朽的肌體,追索病癥的源頭,讓我們在群體暗淡的醫療劇中看到一份敢于面對當下的膽識。這份欣喜來自《醫者仁心》。醫院不再是一個“生死場”般自閉的空間,創作者成功地將其中病痛、人心、社會內外夾攻的壓力轉化為藝術的形式。劇中通過母親為死去兒子申訴的情節支流回答了“如果患者在救治中失去生命,醫生是否一定有罪”的質問,讓觀眾承認生命的有限性,正視醫學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指出“因為醫患失和,輿論一邊倒,面對壓力,醫生這個群體只能保持沉默,長久的沉默形成冷暴力”,④診療醫患矛盾的同時,也在反思整個社會的誠信與溝通。雖然該劇也存在臺詞略顯臃腫、影像語言拘謹的不足,但它依然能夠被帶進更寬闊的坐標系,在文化價值體系、經濟政治結構的變動中行進,用個體的艱辛蛻變呼喚中國的制度文明進程。
從這一抹光亮看開去,醫療劇雖然還有些孱弱,但我們依然希望它能用藝術的方式進入到這個科學與人學的行業中,置入社會又穿透社會,用信仰召喚信仰,用品格呼喚品格,在這個聞醫色變的時代,還醫學以尊嚴,為社會亮一盞燈。我們期待著!
注釋:①呂曉志,吳文超:《醫療劇的一朵奇葩:〈實習醫生格蕾〉的藝術魅力》,《中國電視》,2010(9)。
②王忠明:《病人類——評電視劇〈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國電視》,1987(4)。
③黃宗賢:《藝術話語重構:跨越流俗與“前衛”的合謀》,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 riter.com.cn/bk/2010-12-27/49588.htm l
④徐 萌:《始有真心,方有仁心——電視劇〈醫者仁心〉創作談》,《當代電視》,2011(2)。